金中都“永安”考
刘浦江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
2008
年第
1
期,收入《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
2008
年,第
275
—
287
页。由刘浦江教授弟子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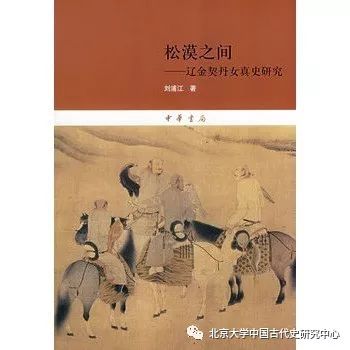
【提
要】
《金史·地理志》在叙述中都大兴府沿革时,有“(辽)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一说,施国祁认为这是“刊本颠窜”所致,并以此为线索,得出海陵王贞元元年改称析津府为永安府,次年更名大兴府的结论。然而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在《迁都燕京改元诏》中已有“仍改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的说法,说明《金史·地理志》的诡异记载绝非像错简那么简单。事实上,“永安”一名是海陵天德三年所改的燕京新地名,所谓“永安析津府”即“燕京析津府”之意,元朝史官因不知“永安”一名的来历,于是便想当然地误以为“永安析津府”为辽开泰元年所改。施国祁受此误导,从而臆想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永安府”。
【关键词】
金中都
永安
燕京
析津府
大兴府
北京史
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初,曾改燕京析津府为永安府,这是不见于历史记载,经过清代学者施国祁精心考证而获得的一个重要发现。自《金史》中华书局点校本采纳此说后,这一结论已被辽金史、历史地理和北京史研究者视为学术定论。很久以来,笔者就对此说法抱有疑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个问题其实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所谓“永安府”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施国祁的错误结论后面,还隐藏着元朝史官对金代文献的误读,可以说是他们联手铸成了这起“冤假错案”。
一、施国祁的一个重要发现
金海陵王贞元元年(
1153
)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并改析津府为大兴府,此事在《金史》里有多处记载。《海陵纪》贞元元年三月乙卯条曰:“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张浩传》亦云:“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记述大兴府沿革时说:“晋幽州,辽会同元年升为南京,府曰幽都,仍号卢龙军,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贞元元年更今名。”同条大兴县下有小注云:“辽名析津,贞元二年更今名。”
《金史》的上述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惟《地理志》“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句似乎有点费解,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施国祁,他在《金史详校》中对此做了非常详尽的考证:
案志文颠窜疏漏不可读。“析津”文上“永安”二字,初疑衍文,考诸他书,得数事焉,知为海陵所立府名。元好问《续夷坚志》云:“海陵天德初(施注:当作贞元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曰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汶阳,河南永安县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又元耶律楚材《庚午元历·步晷漏篇》云:“冬至永安晷漏。”又《世宗纪》,大定十三年语宰臣曰:“海陵迁都永安。”是贞元首改永安,确有明据。缘海陵此名改止年许,而史家于本纪贞元元年漏去此事,直书“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二年遂无复改之文。幸此志刊本颠窜之中尚有未尽抹去之字,稍可援据,乃悟志文贞元元年更名者“永安”也,大兴县注中贞元二年更名者“大兴”也。
施国祁的结论是,《地理志》有关大兴府沿革的那段文字系刊本舛乱所致,当改作:“辽为析津府。……海陵贞元元年,改曰永安府,二年更今名。”
[1]
施氏所引元好问文见于《续夷坚志》卷三“永安钱”条,
[2]
这是施国祁认定贞元元年析津府曾一度改名永安府的关键证据。元好问的记载可以得到文献及考古材料的印证。《金史·地理志》山东西路东平府汶上县条注云:“本名中都,贞元元年更为汶阳,泰和八年更今名。”又南京路河南府芝田县条注云:“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考《元一统志》所记金中都坊名,其中有“常宁坊”,
[3]
即永安坊之更名者。根据元好问的说法,当时改名永安的起因,是因为营建中都时曾发现“永安一千”的古钱币,但他又说“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钱也”。钱币学界一般认为,永安钱是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幽州时期所铸造的钱币,面值有“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四种,币材以铁质居多,铜质则不多见。
[4]
永安钱在北京时有出土,如
1975
年
2
月在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北线阁
85
号院内施工中,曾出土一批永安铁钱,计有“永安一百”、“永安一千”两种。
[5]
以上文献和考古材料皆与《续夷坚志》的记载若合符契,可见元好问确是言之有据的。
此外,施国祁在《金史》中也找到了一条称燕京为永安的证据,《世宗纪》的那条史料见于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他认为这是贞元元年改称永安府的明确证据。又施国祁所引耶律楚材《庚午元历》,见于《元史·历志》:“冬至永安晷影常数:一丈二尺八寸三分;夏至永安晷影常数:一尺五寸六分。”
[6]
《庚午元历》作于
1222
年,是在金《大明历》的基础上重修而成的。
[7]
核以《金史·历志》所载《大明历》,也有上面所引的那两句话,惟“永安”作“地中”。
[8]
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有关地中位置的说法很多,其中以浑天派的阳城地中说和洛邑地中说影响最大,但后来的晷影测量通常以都城所在地为准,不过是借用“地中”的概念而已。
[9]
《大明历》修成于金世宗大定年间,因此它所称的“地中”就是中都;《庚午元历》的冬至、夏至晷影常数均照抄《大明历》,但因成书于蒙古国,不宜再称原金中都为“地中”,故而改称永安,可见耶律楚材笔下的“永安”确是指燕京无疑。
施国祁的考证论据非常充分,似乎无懈可击,被视为校勘学之他校法的一个范例。
[10]
张政烺先生点校《金史》时全盘采纳了《金史详校》的上述考证意见,
[11]
因此自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出版之后,这一结论遂被辽金史、历史地理和北京史研究者奉为学术定论。
[12]
后来,齐心先生又从金代石刻资料中找到几条称中都为永安的证据,为上述结论进一步提供了地下出土文献的支持。
1978
年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娘娘府出土的金《蒲察胡沙墓志铭》,末署“泰和二年三月十五日,孙塔失不立石,永安张伯玉、杨建功刻”。
[13]
1956
年在北京西郊百万庄二里沟出土的金泰和七年(
1207
)《张汝猷墓志》,末署“永安宫济刻”。
[14]
立于明昌六年(
1195
)的《时立爱神道碑》,碑文最后也有“永安宫济摹石”的字样。
[15]
《时立爱神道碑》发现于河北省新城县(现为高碑店市新城镇),金属涿州,距中都不远,此“永安宫济”与《张汝猷墓志》的刻工当为同一人。
[16]
齐心先生根据这些石刻资料得出结论说:“以上志碑刻于金章宗时,距海陵王贞元元年已有四、五十年了,仍自称‘永安’某某刻、摹等,……说明中都称‘永安’在人们头脑中印象颇深,相沿成习。”
[17]
另外,还有学者试图以金代官印论证贞元元年曾改析津县为永安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方“行永安县之印”,系中国人民大学范叶萍捐赠,出土时间、地点均不详。
[18]
景爱先生认为,此永安县即中都永安府之倚郭县,此印证明,在贞元元年改析津府为永安府时,同时亦改析津县为永安县;次年改永安府为大兴府时,同时亦改永安县为大兴县。
[19]
这一结论未免过于唐突。既然此印出土时间、地点均不详,印背又无字款,仅凭印文怎么知道它是金印?又如何能够断定此印之永安县就是中都永安府下之倚郭县?前面说过,《金史·地理志》南京路河南府芝田县下有注云:“宋名永安,贞元元年更。”此永安县在《元丰九域志》卷一西京河南府、《舆地广记》卷五河南府下均有记载。即便贞元元年曾改析津县为永安县,但因存在时间很短,发现官印的概率想必是很低的,所以这方“行永安县之印”更有可能是北宋或金朝前期的河南府永安县印。
二、揭橥“永安析津府”之真相
至此,施国祁对《金史·地理志》的这一重要订正似乎已成定谳。但我在宋代文献中发现的一条金朝史料,使我对施国祁的结论产生了新的疑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绍兴二十三年三月末曰:“是春,金主亮徙都燕京,下诏改元贞元,……改燕京析津府为大兴府。”小注引海陵王诏曰:
今来是都,寰宇同庆,因此斟酌,特有处分。除不肆赦外,可改天德五年为贞元元年。燕本列国之名,今为京师,不当以为称号,燕京可为中都,仍改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
[20]
李心传小注对此段正文的史料来源有所交代:“以《两国编年》金人诛萧裕诏、张棣《金国志》参考修入。熊克《小历》,亮徙燕在二十二年冬,今从《编年》。……诏书具于后。”云云。此条注文语意不甚明确,但大致可以看出,注中所引海陵王诏应是出自《两国编年》。
[21]
《两国编年》一书未见著录,仅见于《旧闻证误》和《系年要录》引用,内容多系辽末金初事,最晚至海陵朝。《系年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正月乙卯条,记金熙宗改元天眷、立皇后、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诸事,小注云:“以《两国编年》、《松漠记闻》参修。”而在“改元天眷”句下又有注云:“杨氏《编年》:绍兴七年,金主吴乞买死,二太子之子亶袭位,改元天眷,误也。今不取。”由此可知,《两国编年》大概出自一位杨姓作者之手,估计此人当是高宗末年或孝宗时期由金入宋的归正人。
尽管上面所引海陵王诏的出处尚不十分清楚,但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最有意思的是,此诏有“仍改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的说法,正好可与《金史·地理志》“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一语相印证,说明《地理志》的这句话既不存在衍文的问题,也不能像施国祁那样用“刊本颠窜”来解释。
[22]
对于“永安析津府”的说法,我们必须另外寻求答案。
先看《辽史》的记载。《辽史·圣宗纪》开泰元年(
1012
)十一月甲午朔,“改元开泰。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地理志》南京析津府条说:“太宗升为南京,又曰燕京。……府曰幽都,军号卢龙,开泰元年落军额。”
[23]
同条又云:“析津县:本晋蓟县,改蓟北县,开泰元年更今名。以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故名。”翻遍《辽史》,找不到南京析津府与“永安”一名有关联的任何记载。
但是,我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发现了一条似乎很有参考价值的线索。该书卷十一“顺天府”下述其沿革:“石晋初,归于契丹,改为南京幽都府,又改为燕京析津府。宋宣和四年得其地,改为燕山府。金仍曰燕京析津府,废主亮改曰中都大兴府。”在“又改为燕京析津府”句下,有顾祖禹的一条小注:“《辽志》:初亦曰卢龙军,开泰元年改为永安军。”
[24]
惟此注所引《辽志》之文,遍查未得。所谓“辽志”者,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辽史·地理志》的简称,一是指《契丹国志》的一种节本。
[25]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屡屡引用《辽志》,一般多指前者,况且《契丹国志》是一部很常见的书,顾祖禹不可能舍全本不用而引用节本,所以我想这里的《辽志》理应是指《辽史·地理志》而言。
那么,今本《辽史》中为何没有这段引文呢?一种可能是顾祖禹看到的《辽史》是一个今天已经失传的善本。《辽史》的至正初刻本今已湮没无存,
1931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残本拼凑而成,其中多有脱误,甚至有整页佚去者。
[26]
但有证据表明,至少在明朝后期,至正初刻本可能尚存于世。明嘉靖、万历间人陈士元,著有《诸史夷语解义》两卷,卷下《辽史》部分所录诸条,虽大都抄自《辽史·国语解》,却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如《国语解》“属珊”条:“应天皇后从太祖征讨,所俘人户有技艺者置之帐下,名属珊,盖比珊瑚之宝。”诸本均阙“有技艺者置”五字,惟《解义》不阙;又“龙锡金佩”条:“太祖从兄铎骨札以本帐下蛇鸣,命知蛇语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谓穴旁有金,铎骨札掘之,乃得金,以为带,名‘龙锡金’。”诸本均阙“有金铎骨札掘之乃”八字,惟《解义》不阙。
[27]
由此看来,陈士元所见《辽史》很可能是至正五年的初刻本。顾祖禹为明末清初人,或许还能看到这个本子。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读史方舆纪要》的引文出处有误,也就是说,引自它书的文字被作者误记为《辽史·地理志》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读史方舆纪要》的这段引文一定有根有据,绝不会是顾祖禹凭空杜撰出来的。
若是我们相信“开泰元年改为永安军”的记载,便可对南京析津府在辽朝的沿革情况做出如下修正:太宗升幽州为南京,府曰幽都,军号卢龙;圣宗开泰元年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并改卢龙军为永安军。也就是说,《辽史·地理志》“开泰元年落军额”的记载有误,不是“落军额”,而是改节镇军名。
不过,如果要用这条史料来解释《金史·地理志》“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的记载,仍嫌说服力不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永安(军)析津府”一名显然不符合古人的习惯说法。我们知道,带有节度军号的州府,如果连称的话,通常是州府名称在前,军号在后,如称幽州卢龙军、云中大同军、京兆永兴军等等,而似乎没有见过卢龙幽州(幽都府)、大同云中府、永兴京兆府之类的说法。
即便开泰元年改卢龙军为永安军一事属实,我也并不认为“永安析津府”的说法由此而来。因为在我看来,“永安析津府”一语中的“永安”,既不是指军号,也不是指府名;析津府或许曾以“永安”为军号,但从来没有以“永安”为府名。对于施国祁之说,还需要重新加以检讨。
施国祁认为,海陵王贞元元年改称析津府为永安府,次年更名大兴府。对他提出的这一假说,我有几点疑问:
第一,上述结论与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元诏》不符。前面说过,在海陵王贞元元年的诏书中,已有“仍改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的说法。首先,这里的“永安”肯定不会是府名;其次,这也说明“永安”一名并不始于贞元元年,当然更不可能有贞元二年改永安府为大兴府的事情了。
第二,施国祁的结论无法使金代石刻材料中的“永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齐心先生从金代石刻中找到的几条称中都为永安的证据,都出自章宗时期的墓志或神道碑。试想,如果永安府一名仅仅用过一年就废掉了,半个世纪后的中都工匠怎么会对这个连历史学家都弄不清楚的名称如此熟悉,并且还津津乐道地自称“永安某某”呢?齐心先生认为,上述石刻材料说明中都曾称永安府一事“在人们头脑中印象颇深,相沿成习”,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第三,施国祁之说也同样无法解释耶律楚材和元好问笔下的“永安”。上文谈到,《庚午元历》所记金中都晷影常数均称为“永安晷影常数”。其实,耶律楚材诗文中常常使用“永安”一名来指称燕京,如《寄妹夫人》诗云:“三十年前旅永安,凤箫楼上倚阑干。”
[28]
《辨邪论序》曰:“予旅食西域且十年矣,中原动静,寂然无闻。迩有永安二三友以北京讲主所著《糠孽教民十无益论》见寄,且嘱予为序。”
[29]
耶律楚材于
1218
年应成吉思汗征召前往蒙古汗庭,据他自述其行程路线:“予始发永安,过居庸,历武川,出云中之右,抵天山之北。”
[30]
又元好问《中州集》卷七有张著小传:“著,字仲扬,永安人。泰和五年以诗名召见,应制称旨,特恩授监御府书画。”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张著跋,自称“燕山张著”,
[31]
可见《中州集》所说的“永安”亦是指燕京而言。若是照施国祁的说法去理解,我们不禁会对耶律楚材和元好问频频使用永安一名感到奇怪,他们为何不用众所周知的燕京或大兴府名,却偏偏要用仅仅存在过一年、早该被人遗忘了的永安府名呢?
其实,并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永安”曾经作为金中都的府名而存在,施国祁谓析津府曾一度改名永安府,不过是对元好问的误解罢了。《续夷坚志》卷三“永安钱”条是这么说的:“海陵天德初,卜宅于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曰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海陵王营建燕京始于天德三年(
1151
),
[32]
这里说得很清楚,改名永安是在“始营造时”,也就是天德三年的事情,并且所改的是燕京的“地名”而非“府名”;元好问同时又指出,海陵迁都燕京之时,“建号中都,易析津府曰大兴”。这里说的原本是两件事,一是天德三年改燕京地名为永安,一是贞元元年易析津府名为大兴,施国祁将它们混为一谈了。
宋元文献中还有两条有关“永安”的史料,也同样可以说明永安是地名而非府名。《大金国志》卷三三“地理”条:“(完颜)亮始徙燕,遂以……燕山为中都,号大兴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大金国志》乃元人所作伪书,虽然这段史料来源不明,
[33]
但无非是出自宋代文献。另一条有关永安的史料见于元人所作《圣朝混一方舆胜览》,该书卷上记述大兴府沿革曰:
辽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后改幽都为析津府,后又更号燕京。金初因之。后废帝筑燕京,其制度一如汴梁,徙居之。改燕京之名曰永安,以析津府为大兴府。
[34]
此书各种版本均无署名,惟明高儒《百川书志》卷五著录作者为刘应李。按是书出自《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而《翰墨全书》的祖本即为刘氏所编,故高儒的著录想必是有根据的。
[35]
刘应李,宋咸淳十年(
1274
)进士,授建阳主簿,入元不仕。
[36]
《圣朝混一方舆胜览》是现存惟一一部完整的元代地理总志,系由编者杂抄各种方志而成,其中就包括《大元大一统志》,上面这段引文,或许就出自《元一统志》。
以上两书的记载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永安”一名之所指,《大金国志》明确指出“其地名曰永安”,《圣朝混一方舆胜览》说得更为明白:“改燕京之名曰永安,以析津府为大兴府。”这与元好问的说法是完全吻合的。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永安”一名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在辽太宗会同元年(
938
)升燕京为南京后,民间仍长期沿用燕京之名。海陵王天德三年营建燕京时,因永安钱的出土,遂改燕京地名为永安,故贞元元年《迁都燕京改元诏》称“仍改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这里说的“永安析津府”其实与“燕京析津府”是一个意思,为地名
+
府名的结构,本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只是当“永安”一名不再为人所知以后,后人才会对“永安析津府”的说法感到困惑,但这对金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在贞元元年改析津府为大兴府之后,中都的地名仍为永安,世宗谓“自海陵迁都永安”云云,章宗时代的中都工匠以“永安某某”自称,甚至直到耶律楚材、元好问还习惯于以永安指称燕京,说明直到金朝中后期,“永安”一名仍为人们所习用。
那么,《金史·地理志》“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的记载又当作何解释呢?我认为,这是元朝史官误解金朝文献的结果。《金史·地理志》的这条史料应该源自《海陵庶人实录》或金朝国史之《海陵本纪》,
[37]
原文当作“贞元元年改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这未免有点难为元朝史官了,因为“永安”一名既非正式的州府名称,作为地名来说又远不如燕京著名,自金朝亡国以后,此名即湮没不闻,《金史》之修纂已在元朝末年,此时的元朝史官想必对永安一名已经很陌生了。见了“贞元元年改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的记载,便想当然地以为这个“永安析津府”必是开泰元年所改,于是在叙述大兴府沿革时就按这样的理解写作“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贞元元年更今名”。元朝史官这一想当然的说法,给后人带来了莫大的困惑。
在得出本文的结论之后,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解释。
其一,《金史·地理志》大兴县下小注云:“辽名析津,贞元二年更今名。”这条史料被施国祁视为贞元元年改析津府为永安府、次年才改称大兴府的重要证据,并由此得出“志文贞元元年更名者‘永安’也,大兴县注中贞元二年更名者‘大兴’也”的结论,因为大兴县是大兴府的倚郭县,改县名必与改府名同时。但我认为这条小注中的“贞元二年”当为“贞元元年”之误。首先,贞元元年改析津府为大兴府一事,在《金史》里有多处记载,惟独这条小注与其它记载不符,可信程度不高;其次,据《元一统志》说,析津县于“金天德五年改为大兴县”,
[38]
天德五年就是贞元元年;再次,《金史·地理志》小注中的错讹是很常见的,就在大兴县下面一行宛平县的小注中,百衲本也把“辽开泰元年更今名”句误为开泰二年了,中华书局点校本系据《辽史·地理志》改正。
其二,据《续夷坚志》说,因改燕京地名为永安,并升为中都,遂“改东平中都县曰汶阳,河南永安县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核以《金史·地理志》,东平中都县更名汶阳,河南永安县更名芝田,都是贞元元年的事情。如果说燕京更名永安是在天德三年的话,为何河南永安县之改名却是在两年以后的贞元元年?这个问题似乎不难理解。天德三年虽已改燕京地名为永安,但当时燕京正在建设之中,尚未成为都城,所以还没有对有关的地名进行统一规划。及至贞元元年正式迁都燕京,升为中都,并仍称永安,才将与中都、永安重名的东平府中都县和河南府永安县一并改用新名,中都永安坊更名长宁坊,也应与此同时。
[1]
施国祁:《金史详校》卷三上,光绪六年会稽章氏刻本,叶
46b
—
47b
。这条考证文字亦见于施氏《金源劄记》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28
—
29
页),仅个别字句有所出入。
[2]
常振国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69
页。
[3]
见《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坊郭乡镇”,赵万里校辑,北京:中华书局,
1966
年,上册,第
6
页。施国祁《金源劄记》卷上谓《元一统志》所记“四隅六十二坊,为金源中都各坊之名”。
[4]
参见《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唐五代十国编)》,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第
515
—
521
页。
[5]
张先得:《宣武区出土的永安铁钱述论》,《首都博物馆丛刊》第
11
辑,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7
年。
[6]
《元史》卷五六《历志五》“庚午元历上·步晷漏术”,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5
册,
1284
页。
[7]
参见《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进〈西征庚午元历〉表》,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185
—
186
页。
[8]
《金史》卷二一《历志上》“步晷漏第四”,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2
册,
460
页。
[9]
参见关增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
19
卷第
3
期,
2000
年,第
251
—
263
页。
[10]
参见崔文印:《古代史书的整理与审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古籍编辑工作漫谈》,济南:齐鲁书社,
2003
年,第
115
—
116
页。
[11]
见《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
52
条校勘记,第
2
册,
584
—
585
页。除了耶律楚材《庚午元历》一条史料外,施国祁举出的其它证据均被采纳,除此之外并未提供新的论据。
[12]
参见张修桂、赖青寿编著:《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162
—
163
页;王颋:《完颜金行政地理》,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第
84
—
85
页;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4
年,第
138
—
139
页。
[13]
齐心:《北京出土的金代女真贵族蒲察胡沙墓志铭考释》,《北京史论文集》,北京史研究会编印,
1980
年,第
102
页。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