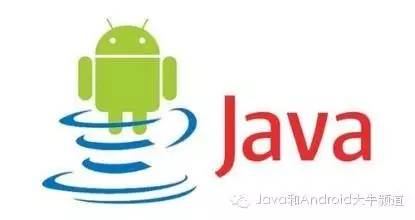01
没有忠诚,社会无法存在
人类几类基本行为模式,无论在本质上或社会学意义上有多大不同,忠诚(faithfulness)都是其中的一种。
无论在对上、对下还是对同级的关系之间;无论是在群体对第三方的敌意中还是善意中;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国家里;无论在个人对亲友的关爱中还是在个人对职业群体的友爱中,忠诚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了。
如果没有我们所说的忠诚现象,社会就一刻也不能存在。维系社会的要素——社会成员的自利、建议、强制、理想、习性、责任感、爱、习惯——若失去了忠诚的补充,亦不能使社会免于分崩离析。
然而,忠诚的程度与重要性又难于在具体事例中确定,因为其实际影响往往通过其他替代情感而发挥,而这些情感又几乎不会完全消失。忠诚与其他情感交织融合的复杂情形,使其难于定量分析。
02
忠诚是一种精神的惯性
事实上,诸如“忠诚的爱”这样的词语,是具有一定误导性的。
如果爱能持久地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中,为什么它还需要忠诚?如果各方不是在一开始就为忠诚所维系,而主要由真实的爱的心理学倾向所联结,那么为什么要在十年以后加上忠诚来做这种关系的守卫呢。
如果从语言用法上只是简单地把“忠诚的爱”理解为“不朽的爱”,当然是没有任何异议的。语言并不是我们此刻所要关注的要义,
重要的是某种特殊的心理和社会学状态的存在,该状态保证了一种关系在失去那些产生它的力量之后还能维系,并产生出了和最初那些力量所具有的相似的聚合力;这种状态我们不能不把它归为忠诚。
忠诚或许可以称为“精神的惯性”。它使得精神在出发的道路上前行而不偏离轨道,即使在那些使之走上这条道路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时亦能如此。
以下事实最具社会学重要性:无数种关系维护着它们的社会结构不变,即使在最初产生这些结构的情感或实践动机已经终止以后亦能如此。“破坏比建设容易得多”这种观点无论有多么确定无疑,用在具体的人类关系上也远非那么必然。
当然,某种关系的产生是需要一些特定的积极和消极条件的,甚至缺一不可。但这种关系一旦产生,往往并不会因为那些关系产生初期的必需条件的消失而受到破坏。譬如,
一开始建立在体态美基础上的性关系,在这种美开始衰减变丑时也能很好地保持下来。
过去认为各种事物只能在产生它们的条件具备时才能维持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自明之理,这绝不是一条关于一般社会交往的普适原则。社会学上的联结无论产生于什么条件之下,都会使之产生一种独立于初始建立关系动机之外的自我保存以及维持运作的形式。
如果没有这种现实社会交往的自我维持惯性,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就会完全崩溃,或是变为一种难以想象的景象。
03
忠诚是一种心理积蓄
社会单位的维持从心理上讲是由许多因素支撑的:智识的与实践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忠诚是其中的感情因素;更准确地说,忠诚以感觉的形式体现出来,投射在感觉层面上。
忠诚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心理蓄积,一种储存了各种各样的兴趣、感情、相互约束的动机等的全面或整体模式。无论各种关系最初的起源多么千变万化,在忠诚的形式中,这些原初的心理状态都达至了一种相似性,这很自然地推进了忠诚的自我维持。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并不关注所谓的“忠诚的爱”、“忠心的依恋”等等,它们指的是已定义情感的某种模式或世俗的量:
我认为忠诚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它直接指向关系的维持而独立于任何维持关系内容的特殊感情或意志因素。
不管这一个体的心理状态具体的存在形式之间可有多大的差异,它都是使社会可能的前提条件之一,这种状态不可能跌至零值。也就是说,
我们无法想象,存在着一种完全没有忠诚的人——对这种人而言,要将产生各种关系的情感转变为维持关系的情感是绝无可能的。
04
忠诚内生于关系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忠诚的过程是回溯的。导致关系产生的心理动机让忠诚的特殊情感去维持这种关系的发展,或是将它们自身转化为这种情感。虽说一种关系可能由多种外部原因引发,但忠诚感却是内生于关系中的,并进而激发出了更加深刻与丰富的情感状态:使关系合法化。
在论及婚姻时,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一种基于传统或是其他外在因素的古老箴言——先结婚,后恋爱——事实上这句话有时十分贴切。一旦关系的维持找到了它心理上的对应关联——忠诚,跟随而来的便是与这种关系相应的感情、情感、兴趣和内在凝聚力。正如我们可“逻辑的”想象到那样,这一切都是出现在这种关系产生之后,而不是呈现于关系产生之初。
但是,这一进程离开了忠诚的中介作用是难以为继的,它的影响直接指向关系的维持。
这些心理状态在背叛现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人会对他新的政党、宗教信仰或是其他派别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忠诚。这种忠诚意识及其坚定程度远远超过那些原本就一直在这个派别中的成员。
在16、17世纪的土耳其,土生的土耳其人往往难以在政府中谋得高位,这些职位上的在职者通常是原本身为基督徒的土耳其近卫步兵,他们要么主动皈依伊斯兰教,要么从小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像土耳其人那样养大。他们是最为忠诚与积极的国民。
这种特殊的背叛性忠诚在我看来是与这样一种事实密不可分的,即在某种环境下,一个人建立的新关系比他之前一直生活于其中而不脱离的关系对他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力。
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到,
忠诚是关系的自主性生命在情感上的反应,它使得我们在面对最初产生关系的那些动机或将消失之际仍能泰然自若。这些动机存在的时间越长,关系自身的纯粹形式所具有的力量独自承受的严峻考验越少,忠诚的效果就越积极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