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线收听
本节目,请点击文章底部左下角
↓↓↓
阅读原文
2017
年4月末,我国自主研发、制造,并已于2013年退役的我国首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在青岛海军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自冷战开始迄今,核潜艇以它巨大的战略价值成为大国俱乐部的准入证,而战略核潜艇更成为大国权杖上最夺目的一颗宝石。
1970
年末,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也成为
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主研制、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从1958年立项至今近60年来,为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和发展,
彭士禄
和黄旭华
等人,
带领着技术团队隐姓埋名、默默奉献,被媒体称作“赫赫无名”的人。
那么,在那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年代,中国为什么要研制耗费巨繁的核潜艇?中国核潜艇的研制怎么会是从一个玩具开始的?核潜艇的“心脏”是如何在一个深山峡谷中试验成功的?负责“核心脏”研制的
彭士禄怎么得了一个“彭拍板”的绰号?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
黄旭华,他的父亲为何至死都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赫赫无名”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们(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由彭士禄负责的“核心脏”研制工作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那就是要造出核潜艇的动力密封主泵,这对当时国内的制造水平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果然,他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图纸做出主泵样机,经过检验投产,生产出正品后,问题也产生了。全密封水泵需要有个外壳包护起来,这个外壳的焊接工艺水平,如果按图纸和技术说明书,是达不到其指标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计算机控制系统,壳壁周围受力受温指标的计算很难做到极其精确,同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高超的浇注技术。
泵壳做出来后,外表发现有瑕疵,军代表不让出厂,只好请彭士禄从北京赶来定夺。彭士禄连夜赶到了沈阳的这家厂,主持一个技术会议。现场放着一台样机——核潜艇动力系统的一个主泵样机。他一面抚摸着这台新造的机器,一面询问着身边的工程师和军代表。
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他身上。“彭总,你决定吧,这东西是出厂还是不出厂,你发个话。”
“
你们都发表意见,最后我来负责任!”彭士禄风尘仆仆、一进会场就这样说。反对放行的一方认为:主泵属于高压水泵,不但要承受很大的气压,而且要承受高温,技术参数一丝一毫不能含糊。厂方表示有难处,已经发挥出了最高水平,非不愿也,是力不从心。
彭士禄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由于核潜艇工程是高密级工程,附着了过严过多的政治色彩,又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峰阶段,大家做事都小心翼翼,生怕被扣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因此,一些人在指标参数面前,表现出多余的刻板态度。
彭士禄却是“胆大包天”。他说:“别怕,如果有人因为技术问题被打成反革命我陪绑!”技术人员终于说话:“技术指标是定得高了,主要是怕出问题担不起责任。因此,保险系数加码又加码。”
军代表也松了口:其实这点瑕疵,外国产品恐怕也免不了。主要是怕人家扣帽子,打棍子。
于是,彭士禄下了令,已经是1969年的夏天,重造一个密封主泵时间不允许,最好的办法是将主泵外壳的裂纹铲除、补焊、打磨,然后出厂!
有人问:“谁签字出厂?”彭士禄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来签!出了问题我负责!”就这样,彭士禄把一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造出来的密封主泵救活了。

像这样大胆拍板的事例,在彭士禄为核潜艇的建造中是举不胜举的。他因此得了“彭拍板”的雅号。
为了安全,有人在蒸汽发生器上加了个“安全阀”,试车时发现总在漏气,彭士禄知道后,拍板割掉,因为在设计计算中,最高温度也不会使二回路的压力超过设计压力。
为了安全,陆上模式堆控制棒曾经搞了9个自动停堆信号,结果试车时常常停车。彭士禄说,过分追求安全反而不安全。他断然拍板去掉了几个装置。
彭士禄拍板也有拍错的时候。他说:“核潜艇在码头试验时,反应堆的循环泵密封出现泄漏,我拍板决定改为新的密封结构形式,结果由于认识不够,失败了,以后又回到原来的结构上,稍加修改解决了问题。我的原则是,拍错了立即改过来,将损失减到最小。但在技术问题上,既然由我负责,那就不能大事小事都推给上面。如果那样,要我这个技术负责人干什么?所以,在技术问题上总是大胆地拍板,不能因为害怕拍板就缩手缩脚,那样会影响整个工程的建设速度和质量。”
在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长达六年的研制试验过程中,作为总设计师的彭士禄不知拍过多少次板,也不知承担过多少次风险。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终于在艰难中走完了它最后的准备阶段。
1970
年7月18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准下,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将于18时开始升温升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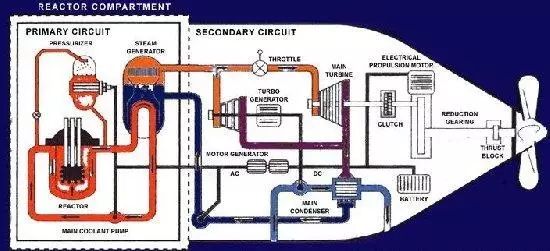
离1970年7月18日18时越来越近了,试验即将开始。
此时,基地接到上级通报,核燃料元件已经运到了附近的火车站,要求立即取货,运回核动力陆上模式堆现场。司机们听说是去运这种东西都不大乐意去,因为担心有放射性。彭士禄听说后,立马赶到车队,对司机们说:“哪有什么放射性?走!我跟你们去,我押车!”司机们半信半疑,以为总设计师不过是说说而已。但话音未落,彭士禄已跳上了一辆大卡车。
到了车站,把装核燃料元件的绿色箱子一个个卸到卡车上。有的司机还是迟迟疑疑不敢开车。彭士禄又是毫不犹豫地一个箭步翻越车厢栏板,跨进打头的那辆卡车,一屁股就坐到那几个码起的绿色箱子上,命令道:“开车!”司机们见状当场表态:“彭总都敢,我们没说的。开车,走!”
又有一次,因为设备之间出现了尺寸上的差异,燃料元件无法装入。彭士禄二话没说,把检修队组织起来“轮番冲锋”,自己带头七天七夜不睡觉,不离开安装大厅一步,直到最后一个元件安装入堆。此时,已是1970年6月28日深夜两点,也是我国核动力装置首次冷态临界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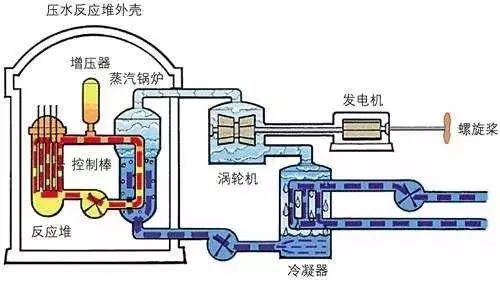
然而,就在启堆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彭士禄突然接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的电话,要他赶回去讲清楚两个问题,因为军管会无法向人们解释清楚。一是有的人谈堆色变,怀疑反应堆若提升功率失败,有可能引起像原子弹那样的爆炸。二是两个工程师通过计算,认为这次即将开始的模式堆启堆,不可能达到满功率,只能达到70%。王汉亭一听急了,在那种年代,人们对反应堆知识少得可怜。怎么向人们解释神秘的反应堆启堆,这是一个深奥的命题。无奈之下,他只好叫彭士禄来向大家解释。
怎么说大家才能明白呢?忽然,彭士禄的眼睛一亮,刹那间他被突发的灵感“点燃”了。他向人们说道:“核潜艇用反应堆装的铀是低浓度的铀,好比啤酒,而原子弹装的铀是高浓度的铀,好比酒精。酒精能点燃而啤酒不会燃烧。所以,我们这个反应堆是不会像原子弹那样发生爆炸的。它的危险只在于泄漏造成放射性污染,而对这点,我们是采取了多层防护措施,是有充分保障的。这些,参试人员都知道,务请放心。”正是这个贴切的比喻,消除了多数人的疑虑。

启堆终于开始了。“开堆!”一声令下,电闸送上了神力。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反应堆的功率一点一滴地缓慢提升……主蒸汽轮机的马力逐步增大。
试验大厅静谧极了,静得出奇。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变得紧张沉重,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在死一般的沉寂中,人们瞪大明亮的眼睛,盯着中心控制台那一排排仪表、键钮。红红绿绿的信号灯明灭闪烁,此起彼伏,好像波浪般地展开七彩的霓屏。一个个指针在仪表上颤动着或转动着,那些数字都像是有了生命,像磷火一样熠熠闪闪。
墙上的电子指钟一下一下地转着弧线跃动。操作员全神贯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紧张地记录一个又一个跳动出现的试验参数。
就在同一时刻,在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里,灯光彻夜亮着。周恩来总理从18日18时开始,通宵达旦地关注着核反应堆的启动情况,一连十几个小时,每隔一会儿就打电话询问远在千里之外的试验情况。试验现场的信息通过国防科委及时报告给他,凡是关键之处都要由总理亲自批准,方可进行。
“
彭总,有情况,脉冲管发现漏水!”“立即停堆检修!”彭士禄答。安全棒落下去了。当发现测量仪表脉冲管漏水,停堆检修的情况和第二次升温升压的时间向总理报告后,周总理再次明确指示:“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越是必须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参数。”
参试人员很快修复了仪表脉冲管。经过仔细检查,几天后又开始启堆提升功率试验。

8
月26日,核动力装置开始由自身的发电机供电,这是我国首次用核能发电,其情景是壮美的。“啊,真正看到原子能发电了!”不少人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
“
报告,彭总,出现停堆信号。”彭士禄皱起了眉头,为什么没有让它停,它却要停呢?若控制失灵就不妙了。他的大脑一转,哦,停堆信号太多了,安全警戒点太多了。对,太安全了反而不安全,控制太严太多了,反而达不到控制的目的。所谓“物极必反”是也。彭士禄与指挥长碰头商议后,果断采取一个大胆的措施,切掉几个不关大局的信号!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措施使反应堆更安全,运行更可靠了。
历经许多阶段,数以百次各种运行试验,结果表明,核动力装置的总体设计是成功的,各种设备的布局和安装是合理的,运行是安全可靠的,它们一一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降临了。8月30日18时30分,指挥长何谦满含热泪站到试验大厅高台上宣布:“反应堆主机达到满功率指标!”
大厅内外顿时欢声一片,泪湿衣衫。
中国第一个潜艇用核动力反应堆如同饱经忧患的胎儿分娩成功,平安出世了。
1970
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成为继美、苏、英、法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朱德总司令登上指挥舰专程检阅了“长征一号”,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元帅庄重地抬起右手,向那条钢铁巨龙、也是向制造这条钢铁巨龙的科学家们敬礼。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虽然成功下水,但并不代表功德圆满,可以高枕无忧了。核潜艇的深潜能力是重要的性能指标。核潜艇艇体强度、密封性如果稍微有一点问题,外部水压造成的进水速度、强度就会像子弹一样具备强大的杀伤力。”世界上曾有十多艘核潜艇在进行试验或航行时沉没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作深潜试验,下潜还不到200米,潜艇上129人就全部葬身海底。
1988
年年初,我国核潜艇进行最后的深潜试验。这是举世公认的危险试验,已经62岁的
核潜艇总设计师
黄旭华亲自下潜,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作深潜试验的第一人。黄旭华回忆,当年有人强调“任务光荣”,越讲光荣,艇员的思想就越乱,有的人甚至给家里写了遗书。“有人下艇之前唱了一首《血染的风采》。黄旭华却说:‘今天要下潜,不希望大家唱这首歌,而要唱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
当潜艇下潜到设计要求深度时,艇上鸦雀无声……100米、200米、250米、300米,巨大的水压使艇身多处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当核潜艇重新平安上升到水下100米左右的深度时,气氛一下子变了,艇员们激动得相互拥抱。黄旭华诗兴大发,当场赋诗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进行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国家。至此,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走完了它的全过程,人民海军也由此成为一支战略性军种。

根据保密规定,最初接到参研核潜艇的命令后,黄旭华曾写信简单告诉老家的母亲,自己要到北京工作,但具体干什么,他只字未提。从1958~1986年,他没有回过一次广东海丰老家探望双亲。即便跟妻子女儿,他也是聚少离多。
女儿出生后,很少见到父亲。有一次,黄旭华从外地回家,女儿说了一句让他哭笑不得的话:“爸爸,你到家里出差了?”黄旭华是客家人,妻子拿这个跟他开玩笑:“你是真正的‘客家人’,你到家里来是做客的。”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的消息传遍世界的时候,远在汕尾老家的母亲丝毫不知晓这一震惊世界的壮举是“人间蒸发了”的儿子领头创造的。30年中,家里人和黄旭华之间的联系,仅仅只是一个海军的信箱。他不能回家,只能每月从工资里拿出10元、20元钱寄回去。即使是20世纪70年代父亲因病去世,黄旭华也未能回家奔丧,父亲只知道儿子在北京工作,但具体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一概不知。
陆游有一句诗,“家祭无忘告乃翁”。1995年,黄旭华“消失”30多年后首次公开身份。黄旭华的身份公开后,他把媒体的报道寄给母亲,母亲看了很激动,特地把黄旭华的兄弟姐妹聚到一块。母亲讲的一句话,至今让黄旭华铭记于心,他是家里的老三,母亲说:‘三哥的事情,大家要谅解。’”
1998
年,身为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的黄旭华回到了家乡。90多岁的老母亲此时见到的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儿子。在给父亲扫墓的时候,黄旭华泪水的闸门一下子打开,说:“爸爸,我来看你了,我相信你也像妈妈一样地谅解我。”
谈及往事,黄旭华说:“为祖国的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我无怨无悔。”中外人士交口赞誉黄旭华为“中国的李科维尔(世界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却一再否认:“中国的核潜艇是一项群体事业。我不是‘核潜艇之父’,我只是其中一员,我不过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
《时代报告》夏风 《中外书摘》杨新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