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间五味,那些世情烟火,正是支撑我们忍受这个充满了荒谬,空虚,孤独的世界的力量和缘由。
▼ 本文由豆瓣用户@夏安 授权发布 ▼
一直不太喜欢看名人之后拿先考先妣作文章的书。第一除了血缘,很多为名人做传的作者和名人没有太深厚的关系,他们是至亲,但是不是知己。比如周海婴写的鲁迅,厚厚的一本书,还不如萧红的一篇小文生动亲切。倒是他在书里“顺带”写到的许广平,看得出很多母子情深。第二很多人写这些的目的不过是夸耀家世,借以自重。比如洪晃和她亲爱的大红门,说来说去,就是广大人民还没见过猪跑路的时候他们家已经把猪肉吃腻了。作为几代贫农的后人,猪肉我从来就没吃腻过,对于这样赤裸裸的显摆我一向是捂着眼睛装作看不见的。
可是好几年前看到网上有人录入的一段《老头汪曾祺》的节选,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在网上找了好几次没有找到完整的电子版,朋友带孩子过来过暑假,问我要带什么,我赶紧屁颠屁颠地跑到网上把这本书给订了。带过来一看,好不惭愧 -- 居然这么厚一本,朋友拖着孩子飞越重洋还要给我带砖头那么厚的书,我真是太任性了。
除了这点惭愧,这本书看下来真觉得物超所值。
看名人传记多少有点偷窥名人私生活,吃了鸡蛋还要看鸡跳舞的意思,可是《老头汪曾祺》在这方面真没多少新鲜爆料。我看汪曾祺的书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吧,投缘,反反复复地看。他一贯是生活写作不分家,连小说都是写实虚构对半开,所以对于作品以外的他,我虽然不敢说了如指掌,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了解。
全书是他的三个子女分别写的关于老头的回忆。汪曾祺说过他的子女都不是写作的料,但是这些回忆却出奇的好看。我想大概是汪曾祺跟他的孩子真的是亲情浓厚。他是那个时代中国男人里的稀有品种,父当马骑,却不望子成龙。他有童心有童趣,喜欢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多年父子成兄弟”的传统,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再传到他的孩子那里。真情流露,弥漫在所有关于生活细节的文字里,不需要多少技巧都很好看。
插页是老头的画。他对自己的画是很自负的,说自己本来该是个美工,误入风尘写小说。我不懂画,请教内行,跟我说你喜欢他的文章,看文章就好了。画嘛,只能说一个作家能画成这样还算不错。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画得好,有灵气。喜欢一个人会变得有点盲目,真是没办法。
还有一篇老头写的李贺,汪朗全文引用,我觉得很好看。这篇小文背后有件轶事,是老头在西南联大期间替别人写的作业,据说闻一多一看就知道是汪曾祺写的。何兆武在《上学记》里提到有个同学汪曾祺:“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就知识分子的派头。”两者连一块看,老头年轻时可真的是“落拓青衫载酒行”。
出乎我意料,汪曾祺似乎并不是个交游广阔的人。他最好的朋友是朱德熙,从前就看他在不止一篇文章里提到他写的一首小诗:“莲花池外少人行,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讲的是他和朱德熙在昆明小酒馆遇雨的事。一次次引用,可见真是写得比较得意,也可见他跟朱德熙之间的深情厚谊。汪朝写到朱德熙去世后汪曾祺在书房里独坐,想写点什么纪念老友,结果掩面痛哭,手边是一副没画完的画。这真是“一片伤心画不成”,读得让人鼻酸。
汪曾祺在小说《星期天》里提到过常和一位天才横溢废话很多的青年画家逛霞飞路吃咖喱牛肉面,我猜想是黄永玉。《老头汪曾祺》证实了我的猜想。汪朝还写到老头和黄永玉之间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后来交情不如从前。这种八卦讲了一半吞回去的做法让人好奇的要命,到底是什么事呢,大概不是什么很愉快的事。再真诚的作者,回忆起自己的亲人来,在有些地方都难免遮遮掩掩吧。
名人后代写名人,包括名人写自己,少有不给自己身世贴金的,看多了真是不耐烦,好像出了一代名人还不够,光辉必须回溯到三代之外。这一点汪曾祺和他的孩子们很好,不夸耀,但是看得出来有感情。
汪家肯定是行医的,似乎还做点药材生意(跟西门大官人一个行当哈),汪朗开玩笑地说就是现在说的“儒商”。不知道这个“儒”字怎么定义,汪的父亲属于读过些书但是不因为读书显达的小知识分子,他的形象除了在汪曾祺自己写的《多年父子成兄弟》里面出现过以外,还在老头一些家乡风味的小说里找得到影子: 比如喜欢“一庭风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乡间名医;还有妻子得了忧郁症自己无法诊治而远走他乡的年轻医生。他们都姓汪,都多多少少有点像汪增其的父亲,好诗书,开明,有点小小的迂,为人散淡而不冷漠。
汪曾祺反感别人说他是乡土作家,因为觉得乡土这个词用地域定义作者,让人感觉很受限制。他一生游历全国,少年时代离开家乡,再回去的时候已是暮年游客了。比起山药蛋派的赵树理,凤凰城出来的沈从文,确实不够“土”。我倒觉得乡土二字,一是乡,二是土,乡不一定是故乡,也可能是他乡。他去哪里都喜欢揣摩当地的风土人情,写出来的东西都有踏踏实实的泥土芬芳,我特别喜欢,不论是高邮,是昆明,是上海,是北京,还是内蒙。
让人唏嘘的是汪朗和汪朝都提到对父亲那边的家人很生疏。解放后汪家成分不好,跟他们来往不多,兄妹俩曾开玩笑对老头说“你爸就是个地主嘛。”我猜想还有个原因是老头惧内。
有一次在某论坛我说起汪曾祺的一篇文章,马上有人问是不是有什么好吃的。我替老头惭愧了一小会儿,因为他的文章里面专门讲“吃”的比例不大(估计还比不上梁实秋),可是很少有不提到“吃”的。
所以不管他多不情愿被称为美食家,好(四声)吃这个名头无论如何是摆脱不了的了。相比之下专门为写吃而写的散文,我更喜欢他写人物讲故事的时候“顺便”念叨出来的那些好吃的:叶三给画家季陶民送的四季时鲜水果、尼姑庵里的全素小饺子、让八千岁滴下泪来的满汉全席、螺丝姑娘为爱人准备的油煎豆腐、还有贫寒的生物系大学生生前来不及尝一口的气锅鸡。
汪曾祺骨子里还是文人。吃归吃,吃过了还有一些小小的情绪和思想,必须传达给读者。《老头汪曾祺》说老头读书很杂,记忆力不错,小聪明是有点的,说起用功,绝对不如他的老师沈从文。他的这些小聪明散散碎碎地撒在他写“吃”的文字里,非常生动,看过以后让人过目不忘,功利一点说,还是文盲提高文化修养的好捷径。
比如他说过最欣赏裴度的话:“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我觉得好得不得了,恨不得贴在墙上当座右铭。当然最近几年才明白,座右铭这种东西,喜欢是一回事,能够身体力行,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写家乡的炒米的时候,他引用《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 -- 暖老温贫四个字常让我想到小时候日暮时分的一些暖乎乎的往事,因此我虽然从没吃过热水泡的炒米,但是炒米却是我想象中常出现的comfort food。
汪曾祺不喜欢袁枚,原因之一是袁枚不会做菜:随园食单很多菜谱都是抄的。听他这么说,再加上他也在散文里谦虚地承认自己会做几道拿手的小菜,我一度以为他是厨房大拿。《老头汪曾祺》里却记录了不少老头在厨房里的糗事:馋爆肚又买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结果做出来的爆肚连牙口极好的孩子都嚼不动;还有和面发面做糕饼最终做成了面糊糊 – 这一点我是很同情他的,对于很多南方人来说面食的确是终极挑战;以及别人送他一只鸡他养在厨房里不敢杀出来吃,只好打电话给汪朗,催他快回家杀鸡。
这些糗事看得我乐不可支。他在小说里借着金冬心的口讽刺袁枚,“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他对袁枚的嘲讽里读出点这个调皮的老头的自嘲来。我家有位调皮的长辈也曾经跟我说,以前秀才们讲究吃,也就是个穷讲究,囊中羞涩,又“过场”甚多,只好在精细上做文章。现在流行鼓吹文人菜的人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所谓的文人菜,有多少是穷酸们的穷讲究。或许真正的吃货们会觉得这种穷讲究不够纯粹专业,或许那点文人式的迂腐正是老头跟袁枚一样在厨房里眼高手低的根本原因。我倒是特别喜欢汪曾祺谈吃里面那种穷讲究的劲头,觉得像听老人讲故事,那些吃的喝的,以及那些人那些年代那些城镇乡村,交织起来,不用多繁琐的文字渲染,都能让人读得有滋有味。
在《泡茶馆》里汪曾祺引用过一首诗:“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说是他小时候不知道在哪里见过,到晚年还记得。我对这种儿歌一样简单明了却蕴意绵长的文字非常迷恋,而这样的审美情趣,很多时候我是通过汪曾祺的文字获得的,所以我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总觉得“记得旧时好”几个字,是汪曾祺文字的精髓之一。他不是遗老,但是他怀旧,不是乡土作家,但是他对故乡有深刻的眷恋。他说过他写文字是想大家感觉到“生活的美好”,而他自己也不止一次感概“活着真好啊” – 而他写的美食正是让人感到“活着真好”的一部分。
汪曾祺的文字朴素,真诚,同时又非常美好,我觉得很难得。他也写恶霸造反派,也写死亡,也写贫穷,也写人性里的各种丑陋和罪恶;他不是哲学家,不是教育家,不是心灵导师,他不会告诉我们那些丑恶,那些疼痛,那些不如意,都是虚幻的,都不值一提。可是归根结底,就像他写过的美食一样,他的文字不只让象我这样古文功底极差阅读面又浅又窄的人领略故纸堆里中国文化独有的沉静和简明朴实的美和好,还能够劝慰所有有幸读到他文字的人,那些人间五味,那些世情烟火,正是支撑我们忍受这个充满了荒谬,空虚,孤独的世界的力量和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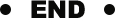
本文版权归 夏安 所有,
任何形式转载请点击【阅读原文】联系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