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滨一直想写一本刑事诉讼法方面的书,对此,我是十分支持的。虽然他以刑法研究为主业,但对刑事诉讼法也颇为关注,并有一定的知识积累。
其实,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从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例如,德国罗克辛教授不仅是刑法大家,在刑事诉讼法领域亦造诣颇深。
当然,因为时间与精力所限,大多数学者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这两个领域,只能选择其一而为其志业。
我在《刑事法治论》一书中,除了刑法内容以外,也涉及刑事司法体制、警察权、检察权、审判权和辩护权等内容。
因此,我对刑事诉讼问题亦有一定的兴趣,但谈不上对刑事诉讼法的专门研究。
本书作者是一位观察型和思考型学者,对社会现实问题具有敏锐的捕捉能力。
在《斑马线上的中国》第三版中,收入了作者发表在《读书》2015年第12期的《中西法律的初始差异与后续流变》,也即本书前言
“如果没有刑诉法——从《创世记》到《五帝本纪》”
,该文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刑事诉讼法的理解,从该文可以窥见他对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观念。
作者指出:
刑事诉讼旨在发现真相并将罪犯绳之以法,刑事诉讼法则旨在减少错案并维护个人尊严。
简言之,如果刑事诉讼是奔马,刑事诉讼法则是道路。没有道路,马照样可以狂奔;有了道路,马奔跑起来更加安全。
奔马和道路的比喻意在说明,法治文明国家,必然珍重刑事诉讼法。也因此,刑事诉讼法反映着大众安全利益与个人自由利益之间的重大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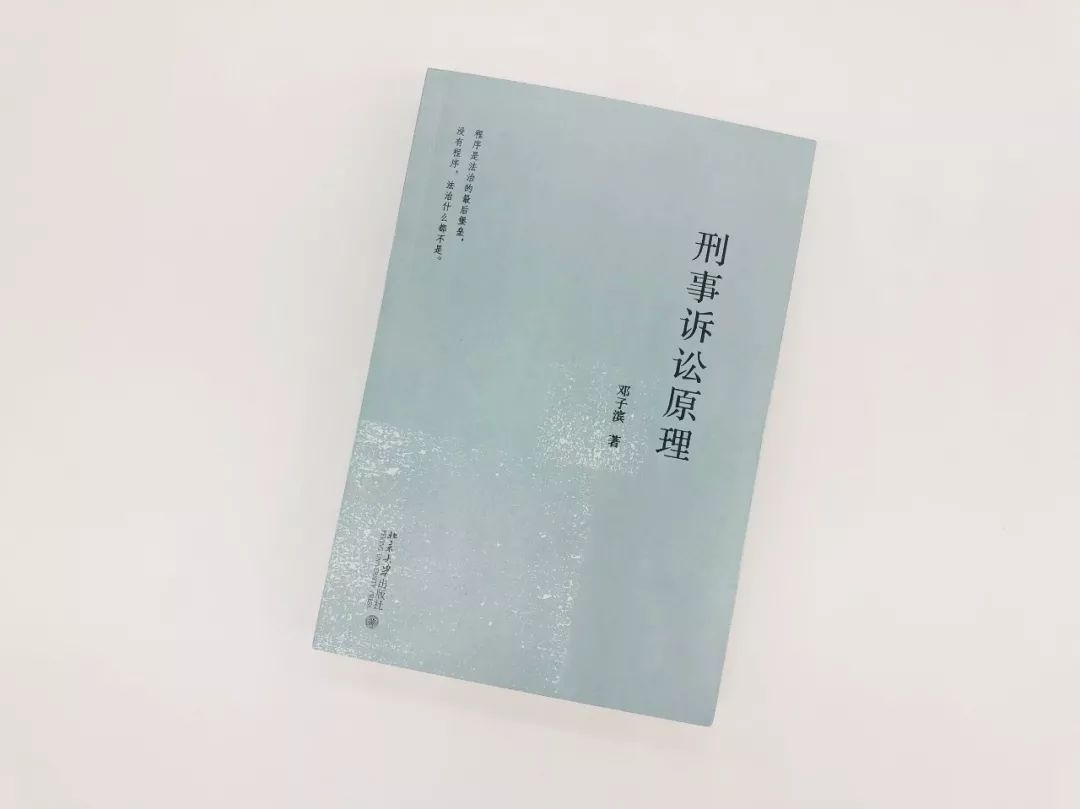
在此,作者论述了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
刑事诉讼是一种发现真相的活动,而刑事诉讼法则是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规范的法律。
这两者显然是不同的,对刑事诉讼法进行研究,是一种法教义学的研究。
这里涉及刑事诉讼法的教义学研究,它以刑事诉讼的法律规范为对象,采取规范分析和语义阐释的方法,揭示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内容,从而为刑事诉讼法的适用提供理论指引。
作者将本书的研究限制在刑事诉讼而不是刑事诉讼法,这是别有深意的。
因为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法规范的对象,避开刑事诉讼法的规范内容而直接面对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对于作者来说,正好可以扬其长而避其短。
作者曾经有志于撰写一部《刑事自然法论纲》,也就是超越刑法规范的刑法原理,然而至今“壮志未酬”。
而这部《刑事诉讼原理》,则可以说是刑事诉讼的自然法,即刑事诉讼的应然之法。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
“这是一本关于刑事诉讼的书。我在本书中努力描绘的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刑事诉讼,这意味着本书不仅不以现行法条为依归,而且立法的某些体系结构将是本书批评的对象。”
换言之,这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论思考,而不是司法论研究。这也正是本书不同于其他刑事诉讼法著作的鲜明特征。
作者虽然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但也是兼职律师,办理过不少刑事辩护案件,对于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运作具有切身感受。
正是在与司法实务的密切接触中,培养了作者对于程序问题和证据问题的敏感性。
在自序中,作者提及十多年前亲历的纽扣案,可谓指控事实与定罪证据严重脱节的典型事例,可以作为反思素材。
这里所说的纽扣案的基本案情是:
“几个妇女,因为自己一方有人在前日的冲突中意外死亡,跑到对方的住宅兼纽扣厂哭闹。她们不仅打碎了一些门窗玻璃,还将装在袋中、摆在庭院周围的大量不同型号的纽扣倒在地上,掺杂在一起。这些纽扣有成品,也有半成品;有合格品,也有不合格品。”
本案涉及的首先当然是刑法问题,即被告人将各种铜制纽扣“掺杂在一起”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毁坏”行为,进而是否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因为这篇论文而使纽扣案得以闻名,成为讨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毁坏行为”含义的绝佳案例,我亦多次引用。
在纽扣案中,不仅涉及对毁坏行为的定性问题,还涉及作者所说的指控事实与定罪证据严重脱节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多次见到。
在一起合同诈骗案中,法官认定的犯罪事实与证据呈现的案件事实居然完全相悖,由此得出的判决结果当然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对于这样的案件,甚至不用翻阅案卷,只要将判决书引用的证言与认定的事实相对照,就可以发现问题。
更有甚者,我还在一份行贿罪的判决书中发现法官为了认定被告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对已经查明的客观事实进行裁剪,这实际上已经是篡改或者歪曲事实,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判决结果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如此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问题,当然是与刑事诉讼程序相关的,这就是没有严格遵守刑事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
中国民间解决纠纷时,为获得真相往往采取“三头六面”的对质方法,而这一任务在现代法庭只有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才能实现。
因此,证人出庭作证,通过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尽可能地还原案件真实,这是法庭审理的基本要素。
然而,目前在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基本上不出庭,辩护人也没有途径对证人进行询问质证。法官不是根据法庭审理情况下判,而是根据案卷材料下判。因此,我国目前的法庭审理,即使开庭也不具有实质意义,基本上都是书面审理。在这种情况下,案件真相如何查清?
这可能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在本书第十一章“法庭审判”中,作者指出:
“在刑事诉讼中,庭审是指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各自提出主张和证据,并且展开质证和辩论,法官进行主动程度不一的证据调查,并最终作出有罪或无罪判决的过程。”

作者提出了庭审需要解决的控辩审三方在场以及如何在场的问题。
可以说,控辩审三方在场,对于庭审当然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证人在场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证人在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从属于控辩双方的在场。
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证人在场对于刑事审判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在本书第四章“基本原则”第三节“直接言词”部分有所涉及,作者指出:
“直接言词原则是与书面审理主义相反的一套理念和规则,它要求法官直接面对被告及证人,不得以侦查、起诉阶段形成的笔录文本或者以宣读笔录代替庭审中从被告、证据及质证中获得的印象,应以真实的感受来完成一项判决。”
而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显然没有实现直接言词原则,正如作者所言,我国刑事诉讼法事实上认可证人以书面证言为原则、出庭作证为例外。
证人即使不出庭作证,其证言仍然可以作为定案根据。这使得我国刑事诉讼的庭审流于形式化,其后果是通过刑事诉讼获得真相的能力大为降低。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证人一定都要出庭,至少重大案件或者重要证人,以及凡是辩方申请出庭的证人应当到场作证。
证人作证制度是刑事诉讼原理的重要内容,在本书中,对证人没有单列一章进行论述,这是存在缺憾的。
......
法科学生一定要看看《罗生门》。这部影片由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执导,1951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从此,“罗生门”一词经过发散与凝结,生成一种特定涵义:
一个过去的事件,根据不同当事人的各自表述,呈现为不同版本的故事。
不过,真相并不是完全消失在历史中,否则也不称其为罗生门;真相只是不再唯一,它可能像刑事诉讼,在有罪与无罪间择一存在,也可能像两个影院同时放映同一部影片,并行存在,还可能像薛定谔的猫,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既存在,又不存在。
影片《罗生门》取材于新思潮派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密林中》,原作以几个人对同一案件的不同证词或告白,于扑朔迷离中凸显人性的机微,虚实相生,玄机四伏,但又各自符合逻辑,能够自圆其说。
《罗生门》则是芥川龙之介的另一短篇小说,是其步入文学殿堂的成名作。
译者林少华评价说:
“它以风雨不透的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从而展示了‘恶’的无可回避,展示了善恶之念转换的轻而易举,展示了人之自私本质的丑陋,第一次传递出作者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无奈与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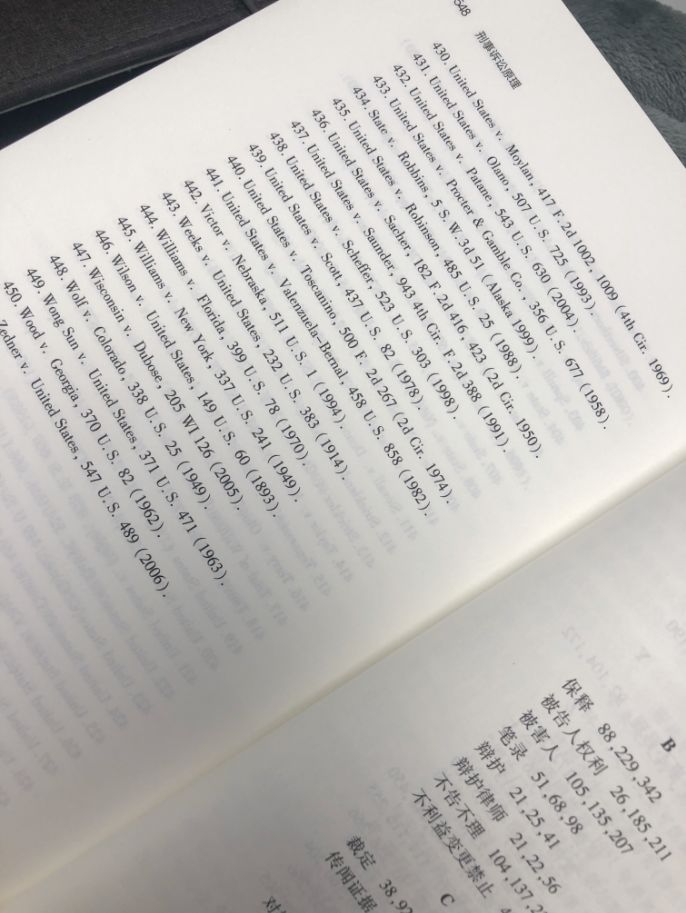
黑泽明只是借用小说《罗生门》的名字讲述《密林中》的故事,许多人因此将小说《罗生门》揭示的“沉郁而悲凉”的人性恶主题,直接套用于对影片《罗生门》的理解,这种解读实际上限缩了黑泽明的恢弘境界与复调结构。
影片《罗生门》可被视为一份独特的庭审笔录,记录了被告人、被害人和证人的当庭陈述,以及庭外讲述。
因此,不应认为“每个人都在撒谎”,如果每个人讲的都是假话,那就根本不可能还原真相。
只有假定每个人都说了真话,或者至少部分人说了真话,才有可能澄清待证事实,或者在无力澄清时作出某种结论。
在诉讼程序中对案件事实的重构,非常类似考古,不应对掌握历史真相有过分的甚至绝对的自信,应当根据不断挖掘出的证据,像拼图游戏一样逐步还原历史中的一个场面或者一段过程。
不过,正如儿童预先知道要拼什么就更容易完成拼图,对一座古墓事先的了解程度,会影响对古墓出土文物的一系列判断,继而影响如何拼接泥土中的碎片以及拼接到何种程度。
其间还要时刻小心,不让假碎片掺杂进来,影响历史拼图的样貌。与刑事程序相比,考古既不必遵守法定期限,也不必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许多事情变简单了。
黑泽明的影片对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进行了两处重要修正:
一是将砍柴人从犯罪现场的发现者升格为主要犯罪过程的目击者,独立叙述了一个故事版本;
二是没有让女人穷凶极恶地亲手杀夫。细小的修正包括强盗的腰刀变为宝剑,等等。
小说和影片可以看作两次开庭笔录,有重叠一致,也有抵触歧异。隐没于历史中的真相,只能靠当事人的回忆表述,但刑事诉讼中最为特别的是,对哪些人可以参与回忆,有一套限制规则,对相互印证或者相互抵牾的说法,也有一套处置规则。
接近真相,是在规则约束下小心翼翼进行的,实在无法确定真相,也会依某种规则给出结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