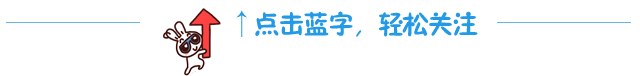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7年第9期
一
第一次见到齐明,是在粮食局家属院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他拿着一叠历代的县志,我口袋里余下的一百多块钱工资,要掏出八十块来换。
这叠县志大多是复印的,看上去比巷子风化的砖墙更旧,也比他本人更显年老。在交给我的时候,他又有点迟疑了,说这是一全套,新县志虽然编完了,也想一直留下来。复印时他自己掏了不少钱,不是看在我对历史这么有兴趣的分上,不会拿给我的。我不得不又加了二十块钱。
那确实是一整套,有康熙、乾隆、光绪直到民国时期的县志,还有民国时编的一套平利乡土志,另外是新县志面世之前单独编印的一本人物志。在手上摩挲起来,像是一叠陈年的落叶,远远比不上新华书店柜台里摆设的精装烫金封面的新县志光鲜。齐明是县志办公室副主任,新县志版权页上的“编纂委员会人员”中,他列在五人中的末尾一个。但其他几个人手中,却没有这么完整的一套历代县志。
他口齿有点涩,不像是完全的平利口音,也不是我那时想像中名士修史的风度。不过他参与的新县志也确实不像我手上历代县志的样子。我们匆匆地分手了。
这套县志在我身边待了几年,终究归于散落。我和齐明也再无联系,直到多年以后,在一个朋友参与编辑的《平利文学》上,偶然看到作者齐明的名字,打通了他的电话,去粮食局家属院看他。
这是一幢老式家属楼的底层,方便腿脚不太好的老俩口居住。老伴沉默寡言,像是农村人的样子。有一个儿子,但不常来,齐明也很少提到他。和八年前相比,除了风湿病引起的腿脚不利索,齐明似乎并无变化,但在面容和体态上,却又分明老了很多,初识的那种涩味淡去了,连他的外乡口音,听起来也柔和了许多,只是和他的腿一样有点微微发抖。
他说到自己的老家,是安徽蒙城县,“就是笑星牛群代言的那个地方”,因为蒙城县著名的出产是黄牛。齐明是属牛的,比我大三轮。
我想到有次坐车从家乡去上海,沿途在山坡上看到络绎不绝的黄牛。有的在耕田,还有的一大群或立或躺在树林下水塘边乘凉。我还曾试着数这些黄牛的头数,想弄清从湖北到安徽一共见到了多少头黄牛。但并不清楚,那一大群一大群牛所在的地界,是不是蒙城县。
他是年轻时跟着母亲来的平利县,起因是寻父。抗战开始前一年,父亲离家来了陕西。正像很多古老的故事里讲的那样,母子辗转来到了平利县,父亲却去世了。日本人占了河南,回不去了,母子只好就地扎根,成了大半个平利人。
说起那本十年前编的新县志,齐明说自己虽然挂名办公室副主任,连副主编也不是,实际却算得上是出力最多的,最初的筹备组连他一共三个人。前面从主编到副主编一溜名字,无非是县领导和文化局长,都是要挂名修史的意思,毕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修县志。
他一个外地人,在平利县志上挂名靠前,似乎也不合适,但当初确实是因为喜欢写几篇小文章,从粮食局被领导借调到县志办,退休后又返聘,清水衙门冷板凳坐了十来年,下乡出差也最多。
说到出差调研,他来了些精神。本县有个先烈廖乾武,是建党早期重要人物,因为参与过南昌起义,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又跟部队南下到海陆丰,需要去查证这段经历。齐明和另外两人一起,从南昌逆水行到赣州,又顺流下到陆丰,途中还特意在东江坐过筏子,水急滩险,体会了当初起义部队南下的艰苦。在南昌档案馆还查到资料,廖乾武参加了决定发动起义的“小划子会议”,船上只有五个人,确证了廖乾武当时的领导人身份。这是编新县志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新县志编出来,精装的一大册,有大半块砖头厚,却并不令人满意。原因是后期编写上面强调“废除传统修史人物为中心的老套,重点展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各部局的人都把本部门近年的成绩指标塞进去,历史上的事反倒不重要了,县志成了一部统计数据汇编,这些数据又水分很多,互相攀比,开会扯皮也解决不了。早期筹备组的几个人反倒靠边站,无奈之下另行编了一本薄薄的人物志,印了几十套,算是留个纪念。
不论如何,“我一个初中文化的外乡人”,参与这件大事,也算是有缘。要说他和平利县的缘分确实深,远远超过了蒙城家乡。详细的经历,他写在一本回忆录里,最近县文联资助出版了。为了这本书,也费了好几年的事,最后总算印了几百册。“我不是非要出这本书,是领导先说了,换了届又没人管了,来回找人。”
我来时带了一本自费出版的诗集送他,他也送了我一本,书名叫《求索集》。薄薄的一本,里面大致是他在一些日报晚报上发表的小文章,尾页上标了四个字“内部交流”。他说,这是领导为了省钱,没有买书号。
二
回到宾馆,我打开了这本书。第一篇文章很长,没有发表过,就是他说的回忆录。
原来他来到平利,是出于父亲的原因。抗战爆发那年,父亲出门躲兵灾,一直来到了平利县,一年多之后,母亲得到了消息,带着齐明辗转到了陕南,寻找到了父亲,父亲却不久就生病过世了。齐明和母亲在平利县住下来,解放以后,齐明参了军。
没过两年,齐明所在的部队调派到安康茨沟的大山里伐木。那时没有电锯子,伐木都是靠斧头,树木又起码是合抱粗以上,一个人一天砍两棵就累躺了,又很危险。
当时齐明正在申请入团,接受组织考察,干活特别卖力气。遇到一棵胡栗头树长了个结巴,树虽然不是特别粗,却砍得特别吃力,斧子卡到结巴里出不来了。齐明不想喊战友帮忙,自己尽力左右别着往出拔。别了两下不动,下一把使了全身的力气,斧子没摇动,却听到嘎嘣一声响,紧接着胸口一阵剧痛,胸腔里什么地方别坏了。齐明往后坐到地上,一会儿就开始吐血。
后来检查,是因为用力过猛损伤了肺部。大山里医疗条件不行,创口感染转成肺炎,又发展成肺结核,险些丢了命。一场大病过去,齐明只好离开部队,转业到了平利县,进了粮食局。不知道出自父亲的什么遗传,齐明喜欢写点小文章,在单位办个墙报什么的。1957年“整风”,组织上让齐明汇集批评意见,出了两期墙报,齐明自己也难免写了两篇。“反右”一来,粮食局有指标,齐明自然成了“百分之五”。
以后的二十年自然历尽艰辛,丢了工作落户农村,一把锄头讨生活,中间旧伤复发时也想过死亡,不过终究活了下来,熬过了“文革”,年纪已经五十来岁,旧病之外又落下了风湿。落实政策回了单位,老母已经去世,旁人劝说来这世上一趟,好歹总要成个家。没有合适的对象,只好找了个乡下进城做保姆的寡妇,就是一直不说话的老伴。没什么共同语言,算是凑合着共同生活。那个儿子,也是老伴带来的,齐明从十来岁抚养到大。
老家那边,以后回去过一次,也没什么人了。工作没几年,又要退休了,正巧赶上全国统一编地方志,返聘到县志办,算是参与了值得一提的一桩大事。
看完了回忆录,回北京途中,大巴经过高速路茨沟出口。茨沟地名我早有耳闻,隐约知道是个黑老扒,这次看到路牌,想到在这么个陌生的地名背后,藏着一个人的命运转折。
后来又有一次,在参加一次公益组织的残障人士维权会议时,遇到一个被拐卖做过奴工的中年人。他本身并不是智障人士,却受骗被拐到茨沟,在深山里强迫伐木烧炭,没有工资,中间还有人被打死,埋在树林之下。他两次逃跑被抓回,第三次才成功,脑壳上留下一道被钢钎杵下来的凹槽,嘴唇上也连带有一个缺,像是兔唇。逃脱之后,他举报了这家黑窑,领人去那片山坡找同伴埋下的尸骨,却踪迹全无。
三
大约过了两年,我在县作协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恰巧这一期前言是特约齐明写的,在前言中也提到了我这篇文章,用了“乡情、乡音、乡韵”三个词。以后齐明打来电话,说到读了我这篇文章,又说他新出了一本书,想送给我和朋友各一本,让我们有空去他家。电话里他的声音似乎抖索得更明显了一点,让我想起那几本发黄散落的县志,似乎虽然当初掏了一百块钱,仍旧有点对不起他。
几次回县,跟朋友提到去齐明家,但丢了一次手机,找不到齐明的号码。朋友一直说打听起来不难,直接去的话怕记不清地方,但这事一直拖下来。心里像是欠了个东西,欠久了,也就似乎可以一直欠下去,似乎他会一直在那里。
直到前一次回乡,在朋友邀我参加的县作协几个文人的聚会上,遇到县城一家大药房的陈老板,意外地认识齐明,问起来说,去年过世了。
这似乎使我意外,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不过出于老年病。倒是去世之前的几年光景,让人有些无言。
因为两人都写文章,齐明又经常在大药房拿些老年治风湿的药,陈老板是齐明去世前几年交往最多的人。老伴走在前头,过世之后养子就更不曾回家照看齐明,齐明有什么事都是给陈老板打电话。
齐明的风湿病越来越重,腿打颤得更厉害。有天快半夜他打来电话,说自己起夜下床摔倒了,在地上一直起不来。陈老板赶过去,把他送到医院,小腿骨折了。摔伤一直没全好,也缺乏人照顾,拖拖拉拉地就去世了。过世时身边也无人送终,陈老板是事后才知道。
他的坟墓,不知在哪里,也没有搞告别仪式。一个外乡人,留在世上的痕迹,也只有县志版权页上不算起眼的那个名字了。
(文内图片若未注明均来自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