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宗教与经典社会学理论、也分析了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的关于宗教的论述。
从19世纪中晚期西方现代科学思想开始进入中国以来,“理论”二字似乎被人们赋予了某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时还会被人们冠以“真理”的名号。在人文学科的日常语境中,每每提起“理论”,人们或许很快会将这个词与“xx主义”挂钩。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先生曾发出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疾呼;也有人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试图厘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然而,悖论在于对“理论”与“实践”、或二者关系的表述,一旦诉诸于人类语言,也将随即成为一种“理论”。那么,当我们在谈理论时,我们究竟在谈什么呢?
1.浅谈理论
“理论”(Theory)这一概念,我们不妨将之简单地、广义地界定为:人类对自然界、人类界、甚至超越界,经过(系统或非系统性的)观察、实验、记录、反思,再通过对关键性概念的抽象化,结合逻辑上的演绎推理、或归纳总结等一系列认知过程后而产生的,对于不同“界”内的现象,以人类语言的方式做出的具有描述性、或带有洞见的宣称(descriptive or insightful claims)。这样一来,当我们评判某种理论时,就能从其解释力方面的好坏,或对实践指导方面的有用与否,而非其论点本质上的真伪进行区分。运用这一广义定义的唯一问题就是,这样一来,我们所熟知的许多“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也有被套上“理论”的光环。
英国作家G.K. 切斯特顿(Chesterton)对于“好理论”(A goodtheory)有过一个经典表达,可以转述为:评判一个理论的好坏与否,应考量其,1)能否最大程度上地光照我们所经历的外部世界,2)能否与我们内在的经验感受相契合。如果运用一个科学上最常见得“三角定位”(Triangulation)原则,那么我们可以为评判一个理论提出大致三条标准:
1)用于表述该理论的语言是否具有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Logical consistency),
2)该理论是否有充足的外在经验证据作为支撑(Empirical adequacy),
3)该理论与我们自身日常生活经历或内在感受是否相关(Experiential relevance)。
此种“三角定位”的方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培养面对某种理论或主义时,所应具备的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精神,破除我们对“理论”的迷思。进而或也能帮助初入社科学界的青年学人们,依据自己所研究的具体案例和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在种种“主义”的海洋中,快速而准确地定位适合于此项研究的理论,亦或能帮助推动研究者进行新的理论建构的尝试。
那么问题来了,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短短百余年时光中,从经典到当代,各式理论著作早已汗牛充栋,理论的更新换代速率,某种意义上也与知识信息传播速率的加剧成正比,我们为什么还要对一两百年前那些如同老古董般的经典理论进行学习和探究呢?
本文是此专题系列中的第三篇文章,我将从经典开始,向朋友们介绍宗教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家。由于这些理论家们大都知识涉猎极广、且著述颇丰,才疏学浅的我自然不可能全面再现先贤们珍贵的思想遗产,只能对其在在宗教-社会方面的论述做出有限的归纳与评述,在“专业”与“非专业”之间架一座桥梁,多有不足之处,期待更多的学习,理解不完全之处,也希望得到同道朋友们的谅解与指正。
由于这一话题所涉及的内容较多,文章将分上、中、下三篇(暂定)。本文在简单澄清“理论”这一概念、并设定相对实用的判定标准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两位现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同时也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奠基人:埃米尔.涂尔干(杜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
2.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迪/杜尔凯姆”)
关键词:社会整合与分化(Social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失范(Anomie)
代表作:《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1895),《自杀论》(Suicide, 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1912)
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生于法国洛林地区的一个保守的正统犹太家族中。他于189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成为了的经典社会学著作,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作为其对宗教方面研究的专著,则是涂尔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涂尔干是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于社会理论方面的贡献着重于:对社会整合所亟需的规范性基础的讨论,个人/个体主义思想的危险,社会失范,和集体的意义等。
涂尔干属于法国社会学的传统,此传统中比较注重对社会整合、分化与团结(unity)的问题。这一传统所考量的问题与法国学界对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给法国社会、及整个西欧大陆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无关系。涂尔干对于宗教–社会的论述最早见于其著作《自杀论》。书中,涂尔干将统计学量化分析的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发现当时西欧国家中,基督新教国家的自杀率要高于传统天主教国家。泛言之,基督宗教的传统伦理教导方面都对自杀的行为做出了严格的禁止,并提供了一系列的神学教义基础,因此要对这种现象的出现做出解释,则需要考察宗教中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亦须考量社会中非宗教/神学的其他因素。
涂尔干对“宗教”的定义,可能是他对宗教社会学理论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影响也最为深远。他将宗教界定为:1)一个统一的体系(A unified system);该体系包括了2)一系列信念信条和实践活动(Beliefs and practices);这些信念信条与实践活动与3)“神圣性的”事物(Sacred things)相关联;且4)将一干人信此类信条并付诸实践的人们(People),整合进5)一个单一的道德社群(Moral community),如“教会”(Church)。在此定义中,涂尔干试图概括性地描述宗教中包含的几大关键元素(Key elements),这样的定义方式被学界称为“实质性”定义(Substantive definition)。
理解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思想的核心,要发现其理论中的一个前提假设(Presupposition),即:所有形式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涂尔干认为,在那些看似最简单最原始的宗教中,可以发现宗教最根本的表现模式(Patterns)。所以,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他选用了大量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原始图腾崇拜的宗教的二手民族志材料,用以佐证其论述。也正因如此,他的宗教社会学说才受到后世学者诟病,认为其所用的分析材料一方面缺乏一手的实证研究数据(Empirical data);另一方面,由于此原始社群的非典型性(Untypitcal),也导致其相关理论难以从人群广度方面进行推广(Generalisation to population)[1]。
不过,涂尔干的宗教理论中,对后世学者最具启发性的一点就是,他以一种二分法式的观察思考方式,将宗教现象(religious phenomena)归类为信念信条与实践活动两类(Beliefs and practices)。信念信条属于人类的理念层面(Conceptual),而实践活动,即宗教仪式仪轨,则属于人类的行动层面(Action)。在信念信条层面,涂尔干的二分法再次发挥作用,将“宗教”所涉及的信条归类为“神圣性的”(Sacred);而将非宗教的归类为“世俗的”(或“亵渎神灵的”,Profane)。在实践活动层面,涂尔干尤其留意了宗教仪式仪轨(Rituals)在社群中所具有的“社会粘合剂”(Social glue)的作用。他认为所有的宗教实践都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于某种个人或超个人(即社会)的道德伦理现实(Moral reality)的符号化的表现方式(Symbolic expression)。
涂尔干对于宗教–社会关系的理论阐述,属于社会学在初创阶段,相关研究方法论建立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系列理论初探与建构尝试。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略显粗糙,许多概念的界定澄清、以及逻辑思考方式上所充斥着的一种勉强的二分法原则(Binary views),导致其对于社会现象复杂性方面的考量往往带上了一种化简主义的倾向(Reductionistview),因此也受到了诸多后代学者的批驳。但是,涂尔干在社会学方面的对宗教进行的探索与研究,尤其是他对于宗教中社会层面/维度(Social dimension),而非教义/神学维度(Doctrinal/theological dimension)的执着探索,也启发了后世诸如托马斯.卢克曼[2]、玛丽.道格拉斯[3]、丹尼尔.厄维尔.蕾结[4]等杰出的西方社会–人类学学者。
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关键词:社会行动(Socialaction),意义(Meaning),合法化(Legitimation)
代表作:《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Capitalism)
马克斯.韦伯(1864-1920)生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图林根州,1889年获得法律方面的博士学位后,研究兴趣开始投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他在博士毕业后,于柏林大学短期任兼职教师,于1894年获得弗莱堡大学教授席位,并于两年后受聘为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版于1904-1905年间,而大多数著作都出版于其身后,尤其是他多卷关于社会科学的系统化与经济–社会方面的论述类著述。
虽然与涂尔干基本处于同一时期,但很显然韦伯并没有受到法国社会学中,源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法国“实证主义”(positivism)社会学影响,反倒更加注重历史对社会事件和现象的影响,即“历史主义”(Historicism)。“历史主义”承认人类行动(human action)的独特性,不主张将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论直接套用到研究人类现象的领域,并认为研究者在从事人文社科的研究中需要对“直觉”(Intuition)加以运用。韦伯虽然认同历史主义对于人类现象特殊性的观察,但对所谓“直觉”的运用有所保留。他指出,社会科学中对一些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以及研究应有的“客观性”是“直觉”无法替代的。韦伯一生致力于理解人类(历史与社会的)行动,认为这样的“现实”(Reality)是呈关系性存在的,因此也有可能做出预测。对于韦伯而言,人类个体在社会学分析中如“原子”(Atom)一般。这就意味着,虽然社会学的分析研究单位(analytic unit)可以使用诸如国家(Nation)、政权(State)、阶级(Class)、社群(Community)等集体性/集合性(collective)概念术语,但对于集体与个体并非是对立而存在的,研究中对集体的探究也同时暗示了对个人行动的影射。
宗教对于韦伯而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他主张,要理解人类的社会行动,就必须从“意义”[5]的角度加以探究。他也深信,宗教之所以对大众常人产生影响,其原因需从人类在世俗生活中所有的一系列期许(Expectations)中进行发掘。在宗教方面,人类对于某种宗教信条的认信,必有其植根于人性与人类历史中的非宗教性动机(Motivations)。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中,他将人类“理性所呈现的形式”(Rationality,也译作“合理性”)做出了两种区分:一是凡可以被预估的行动背后,都有某种目的性的动机(Purposive motivation),即“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二是凡有意义的(Meaningful)行动背后,都有某种价值性动机,即“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因此,在对人类宗教行动进行解释时,韦伯倾向于从行动者/方的动机的这一主观性(Subjective)角度出发。
韦伯同时也在其著作《宗教社会学》中提出一种类似于“宗教演化论”[6](The evolution of religion)的观点。他认为宗教缘起于人类个体早期尝试操控自然、乃至超自然界而进行的一系列类似魔法/魔术一般的尝试(Magical efforts);随着人类智力的发展与知识的增加与积累,这一系列的尝试会逐渐被趋向理性化的、对人与自然或人与上帝(超自然界)关系的理性解释所取代。由此理论逻辑进行推导,在科学逐渐超越神学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人类理性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宗教或许有朝一日可以被其他学科,比如哲学或社会科学学所取代。可以说,当代社会理论中对于现代社会世俗化的论说中,韦伯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始作俑者。
韦伯在其宗教与社会的著作中,一直致力于发现人类宗教现象中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其中尤其注重宗教思想与个人/社会伦理间的关系,以及宗教与社会阶级和不同身份地位群体之间的关系。前者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过精辟的论述,基本论点可以概括为:现代西方式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之一,在于其根植于基督教新教中具有经济伦理意义的神学教义思想。这种教义源自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大众化层面的加尔文主义神学,Popular Calvinism),其“极端预定论”的神学教义宣称,上帝在每人降生以前就早已预定下了每人应有的人生轨迹,一个人在世间的物质经济上的成功与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因此每人都应该努力奋斗,尽可能地或许世俗的物质财富,并恪守其他教义教规(如肉体上的禁欲主义,经济上的积极奉献等),从而荣耀上帝[7]。
在宗教与社会阶级/不同身份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韦伯基于历史资料的分析与解读,发现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宗教的不同倾向或偏好,与其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利益有着某种关联性。韦伯首先从经济层面将人类社群分为农业、商业、工业、与手工业四个群体。他发现那些在经济与政治上处于较强势地位的社群中,宗教常常被用来作为他们在生活方式与所处社会境遇等方面正名,即合法化(Legitimation)。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则更趋向于一种单纯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性宗教思想。在农民阶层中,魔法(Magic)或泛神论(Animism)更容易大行其道;而官僚阶层对于宗教的认信更趋向理性化。中产阶级可能更容易拥抱一种趋向理性、道德教化、或更加强调内在世界的宗教观;而工人阶级则更有可能对宗教采取一种冷漠,甚至嗤之以鼻的态度。
总言之,韦伯对于宗教的分析主要注重于宗教信仰体系的内容/内涵(即Religious ideas,宗教思想)、宗教的变体(Religious variations)、以及社会历史进程中宗教的演变形式(Religious change)。在宗教的内容层面,韦伯认为宗教的思想体系是人类价值观,经过历史进程发展演变而来的结果。在对于宗教变体方面,韦伯的思想与卡尔.马克思有共通之处,更多地强调宗教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中不同社群中所取整合的作用。然而这种关系并不具有决定性,其与马克思不同之处在于,韦伯认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不会局限于某一社会阶层的人群中;而某一社会阶层也不可能同时信仰某一种意识形态。在研究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宗教演变上,韦伯对犹太教中“先知”与既存的社会习俗与意思形态间的动态性互动关系也做出过精彩的论述。
英语学界对于马科斯.韦伯学说的重视与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常认为是始于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英文译介韦伯的《新教伦理》一书。德国社会/政治哲学界中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则尤其注重韦伯在科学理论方面所用的诠释学进路(The hermeneutical approach),以及现代社会中不同形式的“合理性”(Rationality)。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对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之一彼得.伯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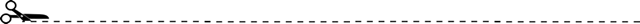
[1]社会科学中普遍运用的两种研究方法路径,即通过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所产生的理论均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推广。不同之处在于,量化分析所产生的理论通常可以推广至某个人群(Generalisation to population);而质性分析所产生的理论则更多地可作为理解当代社会多元性以及进一步量化分析研究的理论基础,即理论层面的推广(Generalisation to theory)。
[2]ThomasLuckmann,与彼得.伯格合著了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著述之一的《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1967),引领了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潮。
[3]MaryDouglas,英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之一,代表作如:《纯净与危险:对污染与禁忌等观念的分析》(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1966)。
[4]DanièleHervieu-Léger,法国当代著名宗教社会学家,代表作如:《作为记忆链条存在的宗教》(Religion as aChain of Memory,1993)。据我了解,这位社会学家在华语社会学界似乎鲜有人知晓。
[5]“意义”这一概念在哲学上可以界定为“(被)理解的可能性”。
[6]对于“宗教演化论”的当代论述可参见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大众科普类著述如《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976,已有中译本);或美国演化论主义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打破魔咒:宗教作为一种自然现象》(Breaking the Spell: Religion as a Natural Phenomenon,2006,暂无中译本)。
[7]这种神学思想也是当代基督新教中福音-灵恩派教会(Evangelical-Pentecostalism)中常常暗含的“成功神学”(Prosperity gospel)思想的来源之一,可参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于上世纪90年代完成的对当代基督教在拉美地区的爆炸性增长的著作《炽火之言:拉美基督新教大爆发》(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Blackwell, 1990))。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宗教学术研究”,作者为英国拉夫堡大学宗教社会学博士。

本期小编:清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