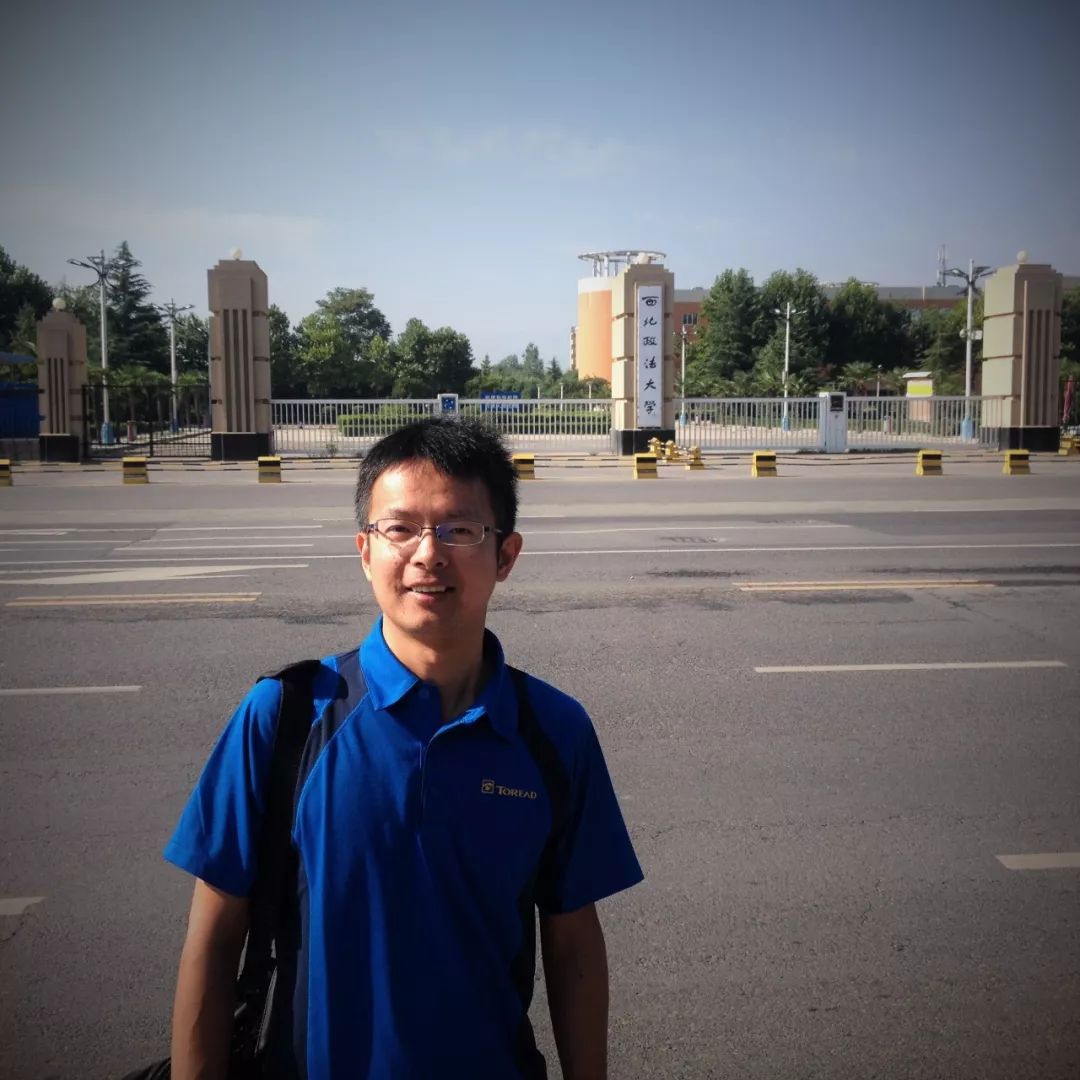
【石头引】
做学问永远都是在爬坡,易退难进。而且一旦形成一些学术成果之后,又容易陷入一定的思维定势。所以,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之后,如何继续进步,是为学者的终生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听听本期嘉宾的分享。
【作者简介】
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1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2010-2011年度访问学者。在《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史学理论研究》《史林》《二十一世纪》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博士论文题目为《日常生活与阶层的形成——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为例(1927-1937)》。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写在前面】
从《博士论文》系列的忠实读者,到自己也有机会忝入其中,无异于一个在班级篮球比赛中都上不了场的臭小子,有朝一日接到NBA球队的邀请函。激动过后,更多的是惶恐与不安。我毕业于一所二本院校的理工科专业,本科阶段并未受到系统的人文社科专业训练。从学术基础角度,属于先天不足类型。我在硕士、博士两个阶段的研究题目完全不同,显然不利于起步阶段的学术积累。然而,深厚的学术功力是高质量学术生产的必要条件,却也容易沾染学科壁垒、门派之成见,未必能够促进学术研究的新陈代谢。在许多学科的发展史上,来自学术共同体边缘外围“小人物”的创新和挑战并不鲜见。
问题在于,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层累过程,并不止步于创新之“破”。倘或没有追本溯源之“立”的巩固,那些新意迭出的“破”只是无根之水,难免“各领风骚三五天”的速朽之运。学位论文选题,既有针对前人留白的填空式“破”题,也有将前人研究再问题化的梳理式“立”题。前者更像探索一个遍布荆棘的黑暗领域,后者更像对一个杂乱无章的房间进行归类整理,建立一种新的排列组合秩序。两种研究章法不同,各有优劣。学术基础深厚者,从事“立”题研究可以发挥其学术底蕴的优势。而学术基础薄弱者,从事“破”题研究,也不失为一个另辟蹊径,扬长避短的策略。但是,“破”与“立”并非截然二分,而是相互交织、螺旋前进。回看自己问学之路,最大的艰难和挑战在于“推陈出新”之“破”与“追本溯源”之“立”两者间的不断切换。
一、工会研究的“见制度不见人”
2005年,我来到江城武汉桂子山,成为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一名研究生。读研第一年,我仅仅是整日泡在图书馆,随意翻了不少杂书,并未思考过日后的论文选题。二年级时,需要拟定选题方向。为了借鉴华师在近代工商业社团史方面的研究优势,又避免与其“撞车”,我拟定工会作为研究对象,得到魏文享老师的认可。魏老师建议我,相较于以往关注较多的“红色”工会,应当重点关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黄色”工会。郑成林老师曾建议我们,选题时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家乡或学校所在地档案馆收藏的文献资料。我选择1945年至1949年间的武汉工会作为研究对象。相关一手档案资料主要集中在武汉市档案馆,方便搜集。在一次课后交谈中,魏老师建议我,不妨关注一下法团主义理论,作为论文的研究视角。开题报告通过后,带着老师的建议和前期搜集的档案资料,我进入了论文的撰写工作中。
尽管我在选题上没遇到什么障碍,但在论文写作阶段,我遇到了两个难以驾驭的困境。第一,对工会组织体系的整理归纳。民国时期的工会,既有产业工会,也有行业工会,还有政府直辖的省、市、区工会。这些不同的工会,在组织结构、会员人数、运作方式等方面都有差异。如何能将工会的组织体系条分缕析,呈现一个区域内出不同类型的工会组织之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第二,与社会冲突理论不同,法团主义理论侧重社会整合。因此,该理论更侧重结构-制度分析,而不是过程-事件分析。而主流史学强调避免某种先入为主的理论视角和观点,主张用占有、穷尽文献资料的方式,还原历史事件过程,深度发掘作为个体的人或群体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抉择与行为方式。借用杜赞奇的话说,历史学是反理论的。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花了大量篇幅去描述和分析工会的组织制度、经费开支等问题。但我其实更希望看到事件和故事,例如工会的干事、理监事、书记等大量“无名之辈”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怎么奔波、周旋于政府与军警之间,又如何安抚心生不满的工人。然而除去有限的劳资纠纷材料外,其他类型的材料少之又少。档案文献中几近无迹可查,地方史志等辅助资料中也鲜见涉及。字数越码越多,无趣与困惑之感也日渐强烈。
如果说引入法团主义理论视角是相较于以往社团组织研究中国家与社会视角的创新,接下来就应在这一视角能看到哪些国家与社会视角看不到的问题上用力。然而,出于对“见制度不见人”的困惑,我既没有在法团主义理论视角方面继续用力,也没有在文献资料方面持续深挖,而是选择了转向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避重就轻”,对林毓生、列文森、史华慈等老一代美国中国学者的著述产生了兴趣。柯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制度、社会结构、事件的背后,难道不是人的思想最为深邃吗?进入研三时,我觉得我的兴趣已经完全转移至思想文化史领域。但是,我当时对思想文化史的狂热一种票友式的喜好。我没有系统研读过思想史脉络里的原典文本,仅仅是一目十行地读了一些思想史方面的二手著述而已。在硕士论文与思想文化史八竿子打不着的情况下,我“任性”地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老师的博士,幻想到上海滩“见世面”。
二、从“思想云端”到“日常生活”
许老师没有因为我的“二本”出身歧视我。在与我面谈后,他肯定了我的研究兴趣,鼓励我完成这一学术“变道”。我的愿望“得逞”了。我终于避开了那些枯燥、无趣的工会研究,进入我所期待的思想文化史领域。博士期间,要完成学校规定的学术发表任务。我的发表,是个误打误撞的经历。入学不久,我按照往届学长们的做法,将硕士论文打磨修改,投稿。由于我引入法团主义理论视角,因此我在论文引言部分不是从史实出发,而是对既有理论进行梳理。这种更接近社会科学的写作风格并非主流历史学论文风格。给几个史学专业期刊投稿,均无音信。一次在宿舍与同学聊天,对方建议我,不妨给《社会学研究》之类社会科学专业刊物投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社会学研究》杂志网上投稿。两个月后,收到杂志社的邮件回复,认为文章选题很好,但是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有失周全,结论部分尤显草率,建议对武汉工会的组织、运作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功能机制分析,在结论部分对法团主义理论视角的适用半径等问题予以系统梳理。
根据审稿意见,可以揣见这篇文章在引入法团主义理论视角的“破”方面得到认可,但是在自成一说的“立”的方面显然没有让杂志满意。尽管当时收到这封邮件时无比惊喜和激动,但激动过后,头皮阵阵发麻。因为我已经转向了与硕士论文完全无关的另一个领域。而修改此文,恰恰就是要解决文章怎样能“立”起来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重新盘活已经被我搁浅了一年有余的硕士论文,还要对已经有些生疏的法团主义理论重新回炉。这一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暂时中断博士论文的资料搜集工作,全力投入到修改硕士论文的过程中。幸运的是,经过修改,文章被杂志正式接受,刊出时间也指日可待。
然而,发表领域的意外成功丝毫不能掩盖我在博士论文进展方面的困难重重。早在许老师招收我时,他根据我在华中师大受到的注重一手史料训练的特点,建议我从事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博士入学时,正值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埃斯的5卷本《私人生活史》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发行,反响不小。一直在思考开辟知识分子研究新路径的许老师认为,以往知识分子研究大都基于传统思想史路径,而知识分子本人的生活史则鲜见关注。许老师建议我,以1927年至1937年这一民国“黄金十年”期间上海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为博士论文选题,从日常生活视角切入,考察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建构过程,寻找生活史与思想史之间的交叉点。
很显然,与硕士论文选题类似,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是一个前人未曾涉猎的“破”题类型。然而,硕士论文中引入的法团主义理论本身是一个有着自身发展脉络的理论,论文所需的资料也主要来自相对集中的档案材料,执行难度相对小。而博士论文选题在执行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首先,从日常生活视角考察身份认同建构,并没有一个已经得到学界公认的相对成熟的分析框架。其次,这一选题暗含很多难以厘清的概念和问题。知识分子与日常生活两个概念都是包罗万象的“大词儿”。在撷取材料的时候,如何取舍?再次,民国时期的上海,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一个地方。他们的“朋友圈”五花八门。有的紧密,有的松散。不同圈子之间既有排斥,也有交集和流动。如果说硕士期间对工会组织体系的分类已经倍感头痛,对数不胜数的知识分子加以归类更令人绝望。最后,知识分子研究主要是以研究对象本人留下的日记、文集、回忆录等公开出版物为主,并不十分依赖于档案。档案材料相对集中,而日记、文集、回忆录与报刊文献等资料,则如漫山遍野采蘑菇一般,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堆里逐字逐句翻检。尽管可以免去“蹲档案馆”之苦,但资料分散、庞杂所导致的搜集资料的前期准备阶段大大拉长,是执行研究计划的沉重阻碍。
在修改《社会学研究》稿件的过程中,我初步体会到历史学与社会学在问题意识、写作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我意识到将社会学相关理论视角嵌入历史学研究,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模式。我的硕士论文带有明显的社会科学问题意识和研究框架的嵌入,并非以梳理事件源流、考辩典章制度等为着力点的主流史学风格。为了化解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诸多障碍,加之《社会学研究》投稿成功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使我开始寻求一种借助既有社会理论和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去统摄资料的“策略”。为此,我借用刘欣、李路路等社会学者关于社会分层与身份认同等问题的研究框架,确定了以阶层位置、日常交往、精神生活与生活方式几个层面为主线的篇章结构。每个章节从一个生活侧面考察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凭借不同的惯习完成区隔与分化。
在这一“策略”的执行过程中,我的论文写作几近一个码字与搬书交织的体力活,留给行文论断本身的思考和斟酌不免仓促。尽管我的论文体量颇大,涵括了许多知识分子,但在日常生活的庞大统摄下,对其中具体人物的涉及多是蜻蜓点水式的,难以形成立体的、丰满的人物论述。结论部分,对于论文的核心问题——如何从日常生活层面考察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也存在不少语焉不详的模糊之处。当我即将完成博士论文之际,已经开始思考另起炉灶、重新出发的新问题。
三、重新出发
博士毕业后,我于2012年入职杭州师范大学,开始了平凡的教师生涯。从985高校的博士生到普通本科院校的青椒,身份和学术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思考新的出路。
尽管我的硕士和博士阶段做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但两者都侧重拓荒式的“破”题研究。这两个研究都不属于侧重一手史料、以还原史实、考辩典章制度为宗旨的主流史学风格。在问题意识和框架设计层面,两个研究都引入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在资料运用方面,前者侧重相对集中的原始档案,后者侧重相对分散的多种文献。尽管我在博士阶段付出远较硕士阶段辛苦的努力,但这主要是由于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庞杂以及引用文献的分散所导致的资料搜集阶段的延长,并非意味着我的博士论文在理论视野和论述水平上就一定好过硕士论文。从执行研究计划的角度,放弃宏大的理论追问和拔高雄心,选择开口较小的问题切入点和狭窄、明晰的研究对象,设计一个紧凑的研究框架,搜集相对集中、便利的资料,这种操作办法与现代知识生产体制高度匹配。只是对于后者而言,在执行这种“脚踏实地”的研究的同时,不应放弃对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这使你能够在今后的学术工作中避免因重复劳动而导致的长期停滞。学术之路涓水长流,停滞就意味着学术激情的消散甚至学术生命的死亡。
学术研究的创新之“破”多源于不同学科之间碰撞擦出的火花。因此,历史学研究中引入相关学科理论有助于历史学本身的新陈代谢。。对于研究者而言,在不同学科之间切换,既取决于自己的知识储备与个人喜好,亦取决于所论述的问题本身。在教师生涯的起步阶段,我延续了修改硕士论文的方式,以社会关系网络、惯习与区隔等理论进一步统摄博士论文中的部分章节,向《开放时代》《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投稿,并获成功。然而研究本身不应止步于发表。在引入这些“舶来”的理论的同时,更应追问这些理论视角能够看到那些之前所忽视的东西,在哪些方面能够推进已有认知。这个认知既涵括历史学层面的史实叙述,又涵括与相关学科理论的对话和反思。从这个角度,引入相关学科理论,看似在“了无新意”的因循守故中“玩花样”,但却面临跨越两个学科的“双重作战”。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境地,难度和挑战翻倍。
我的硕士论文引入的法团主义理论源于欧洲经验,其主旨是探讨一个充分组织化的公民社会如何化解社会组织相互间的冲突。然而,民国时期的“公民社会”尚未正式形成,社会组织体系的发育十分有限。用法团主义视角考察民国时期的城市工会,是否存在理论“错置”的问题?这些问题,意味着引入法团主义理论视角进行实证研究,还具有相当大的阐释空间。
我的博士论文,除去那些资料剪裁、缝合的技术问题外,我想一个最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够把身份认同与阶层建构这一问题放入相应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当我今天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拿起6年前的博士论文,我会问当年的自己,你所研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与阶层建构对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十年建设”时期完成了知识分子从五四时期的“个体”发现到“智识阶层”的群体整合,这种蜕变对国共两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规训有什么影响?
前不久的第三季《诗词大会》总决赛上,一位来自杭州的外卖小哥雷海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夺冠的最大黑马。主持人董卿的“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一席话也随之成为网络红语。尽管我没有直接从事思想史研究,但读博期间,我处在一个以思想史为主的学术共同体内,耳濡目染了不少思想史的“皮毛”。记得许老师不止一次说过,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对市场、公民社会等问题关注较多,但对于国家的角色和作用,涉猎较少。由此导致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中,双方在相当程度上均未能就对方的问题意识展开实质性探讨。之前对许老师的这番话一直未曾留意。近年来,在思考未来的研究方向时,我注意到与自由主义理论相反,法团主义理论则因为关注国家对社团组织的协调、体制化功能的强调,对市场与行业秩序等问题缺乏关注。于是,我近年来重拾一度耽搁的工会研究,通过对战后行业工会卷入的各类纠纷考察工会在市场秩序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局限,试图在法团主义理论的幽暗之处打开缺口。在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史方面,我在打磨即将出版的以博士论文打底的专著的同时,有意对之前那种“包罗万象”式的“宏大”研究予以纠偏,回到以单个人物为主的个案研究,将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细节放入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结合相关理论关注点,探究研究对象本身所面临的时代之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