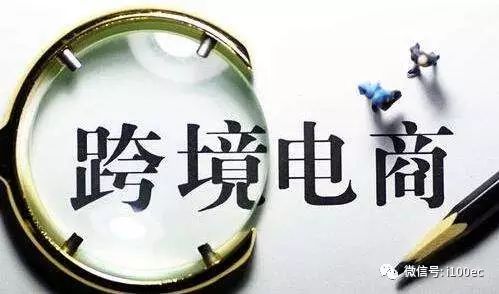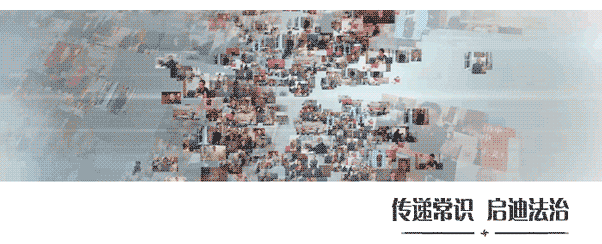
文/徐贞庆
近日,在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邓辉提交了一份《关于降低故意伤害罪入罪标准的建议》,呼吁降低故意伤害罪入罪标准,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
2009年以来,我国犯罪化、重刑化呈现“双重提速”态势,刑法的范围不断扩张,并呈现一定的“过度刑罚化”倾向。
邓辉的建议如获通过,这只新的“蝴蝶翅膀”将扇来一股强劲的“社会治理刑罚化”之风,一些伦理非难性有限、法益侵害性有限的伤害行为将被犯罪化;随着大量由于“一时冲动”而“锒铛入狱”的“有前科的释放人员”的出现,“犯罪”将变成新的社会“普遍现象”。
诚然,以严厉的刑罚惩治邓辉提议入罪的那些行为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却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诉诸刑法”作为解决社会治理难题的唯一有效手段。
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与一般的行政处罚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刑罚具有相当的残酷性,是国家施加在社会成员身上的最严厉的处罚;
其次,任何一个个体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对本人、家庭、子女都将产生贯穿一生的不良影响;
第三,刑法坚守的是社会的底线,其作用是保障社会不变得更坏,而无法使社会变得更好,因而完全寄望于用刑罚手段解决社会难题无异于缘木求鱼,最终将与真正的法治越行越远。
当前,刑事立法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是在开放的舆论环境下,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形成的,符合现代民意政治对法治建构及社会治理的要求,是时代的进步。降低故意伤害罪的入罪标准反映了一部分群众的内心真实想法,邓辉提交的修改建议正是一种对民意的积极回应,也将会对相应的伤害行为形成一定的遏制。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降低故意伤害罪入罪标准,有重复立法之嫌。
社会治安管理法规已经对“在公共场合当中殴打他人”等行为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我国刑法也已将“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的行为列入罪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当中。这其中就包括“多次随意殴打他人”、“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等行为。
降低故意伤害罪入罪标准,将增加司法成本。惩治违法行为的社会总成本,是违法者的成本,警察、诉讼还有法庭方面的公共支出,与社会其他成员的私人支出之和。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应考虑总的效果。
一旦前述建议获得通过,故意伤害案件数量将激增,在“案多人少”矛盾已经相当突出的情况下,司法部门势必要新增办案人员,增加财政支出。如此做法是治标不治本,以酒驾为例,刑法已规定将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但酒驾的现象仍大量存在,每年仍有大量的人因酒驾被判刑。
降低故意伤害罪入罪标准的本意是保护民众的人身权利,但却在事实上造成了个体自由因社会对安全的追求而不断萎缩,行为人也更容易受到权力者的损害——这是“以社会管理之名行权力扩张之实”。不难想见,一旦故意伤害罪的入罪范围扩大,民众在公共场所中受到不合理的刁难和对待时,或会因刑法过度介入社会生活而产生恐惧心理,进而选择忍气吞声,见义勇为时的顾虑也将更多。
另外,社会治理刑罚化将会陷我国“法治”于“法律工具主义”的“囹圄”。
封建时代的法治视法律为社会治理的工具,强调人对法的操控,法出于权,导致“法治”就是“人治”。法律工具主义是一种形式上的法治,是从人治过渡到法治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统治者强调法律的治理功能,但实质上还是把法律作为治理百姓的工具。法律的制定者,实际上成为法律的操纵者,这种法律无论在形式上表现得如何公平正义,都脱离不了工具主义的窠臼。通过诉诸刑法来解决社会治理难题的做法,将刑法当作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而非保障人权的屏障,其实质依然是把刑法作为打击犯罪的工具,并没有跳出物性刑法的窠臼,更无法实现向人性刑法的转变。
这与真正的法治相去甚远,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理性:
首先,虽然当前我国法律的外部框架已经搭建完成,各个部门法也在不断完善中,但是以往立法更多的是针对“治民”,在“治官”方面略有不足,而且以往立法受舆论、政治、权力等因素影响较大,某些法律规范的出台更像是事后的“亡羊补牢”。
真正的法治,要求法律在社会治理中至高无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都得依法办事。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首要的是公正,要以法限权,把官员职权关进法制的“笼子”里,让为官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
其次,刑法既不能为了维持秩序、控制社会而忽视保障个人的权利,也不能为了一味追求保障自由而无视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刑法奉行单一的社会干预理念并不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为防止中国社会治理落入刑罚化的陷阱,完善以法限权的法律体系建设,需要创造更为宽松的话语环境,让更多的“声音”得以呈现,让社会治理及法律演进能够在多元、包容、均衡、理性、平和的话语生态中展开。
最后,遵从刑法谦抑性的原则,保障个人自由先于维护社会秩序。能够不使用刑罚,而以其他手段亦能达到维护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及保护社会与个人法益之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手段。即使出于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个人自由的目的,但在采用其他措施可以实现的情况下,也不得轻易使用刑法。由此,才能真正实现由物性刑法向人性刑法、由敌人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