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唐朝鲜卑论”最早源头,是宋朝儒学大师朱熹的话,《朱子语类》中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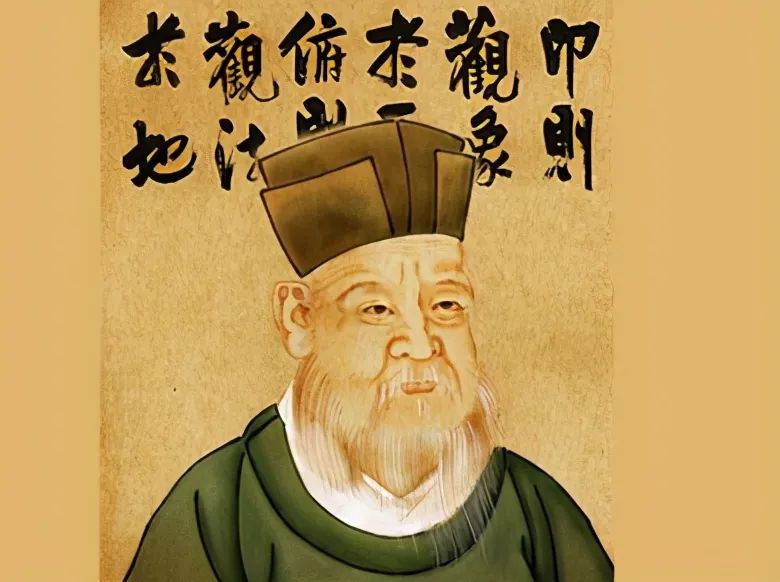
上世纪民国大师
陈寅恪
,便引朱熹这句话,进一步发千年之新论,相继提出了「唐朝河北胡化论」「李白西域胡人说」。
【唐代河北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两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族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属于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李白其人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其父之所以名客者,始由西域之人其姓名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兴贾区域”,至入中国方改李姓也。】——《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陈寅恪
主张李唐皇族并非出官方说法的凉武昭王李嵩之后,也不是其自称的陇西李氏,而可能是赵郡李氏破落户冒名。
而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民国大师的另一位民国大师
刘盼遂
,则相继写就《李唐为蕃姓考、续考、三考》,力主李唐皇室先人为胡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掀起一场关于李唐族源的大讨论。王桐龄、萨孟武、朱希祖等学者都曾前后参与讨论。
陈寅恪与吕思勉、钱穆、陈垣被称为上世纪的“前辈史学四大家”,随着年代推移,更成为历史学界被奉若神明的泰斗级人物。
从此当了一千多年汉人千古明君、不世英雄的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及其子孙一众大唐皇帝,甚至还有诗仙李太白,就在许多人的认知中莫名其妙被改了户口本,变成了胡人。

前辈史学家的贡献是必须敬重的,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必须正视的,谬误同样也是要予以批判与否定的。“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才是论史治史者正确的态度。如吕思勉的“岳飞军阀论”就长年被诟病,如今已经被史界彻底否定了。
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政治史文化史方面的各种创见,如“关陇集团”的提出,特别是「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这一精妙论述,皆是真知灼见。但他同样也不可避免有其时代局限性,比如很著名的一例,就是陈寅恪坚决反对汉字简化,坚决反对书籍报刊从竖排改为横排。因此他许多版本的文集,至今皆遵其遗愿,繁体竖排。此见解是否正确,相信自有公论。
同样,陈寅恪的「唐朝河北胡化论」「李白西域胡人说」,也只是证据极不充分的一家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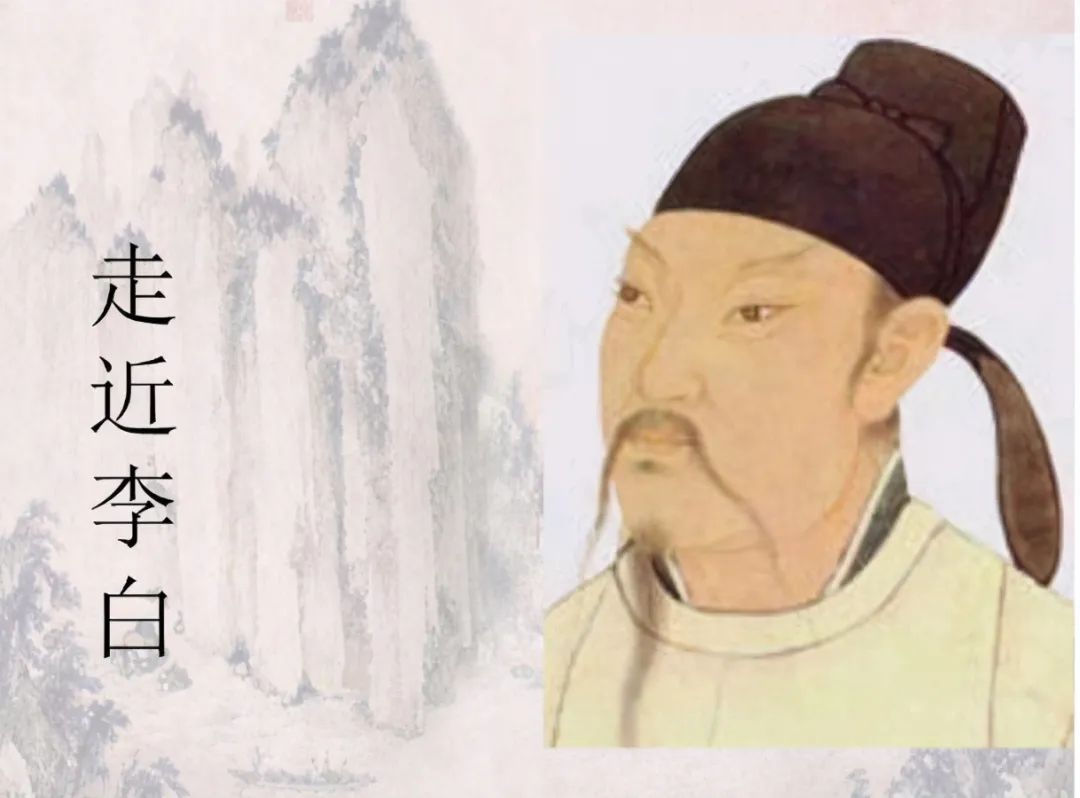
从初唐起,不断有突厥、契丹、回纥、高句丽、沙陀各部被迁入中原,其部酋为唐政府效力为唐将,中间也确实有过处置不当,后突厥回漠北复国这样的反复。
然则就总体趋势而言,一直是这些胡部被汉化,胡人被汉人融合,而从来不是相反。即使到唐末才迁入的西突厥沙陀人,经过五代几十年融合后,也彻底泯灭民族意识,和汉人毫无区别了。
而安史之乱后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所谓“尚攻战而不崇文教”,确是不假。
但他们的地域民族认同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当真变成了胡人。更不说河朔三镇同样还有大量的汉人士子,一样参拜孔庙,传承六经,参加朝廷科举。
陈寅恪先生以河北地域重武轻文,不重儒学,便大呼这是”汉人被胡化“之论,仿佛我汉人天生就不该尚武,就该用天灵盖去顶狼牙棒不成?以其魏晋史大家的身份,见识是不当至此。
对所谓“河北胡化说”,不妨反问,唐朝灭亡后经五代到宋朝建立,那些据说是“胡化了河北”的胡人怎么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唐末可没有再出个发布“屠胡令”的冉天王去杀光他们吧?后周至北宋都领有河北,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是个常识。甚至被契丹割去的幽云十六州,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还是个常识。
陈寅恪先生是史学大家,却不是全能全知不会犯错的神灵。科技发展如此迅速,从前民国大师穷尽一生能翻阅到的资料,在今天信息爆炸时代俯拾可得,因此他们的许多结论,都有时代局限性,并不能盲目迷信。
吕思勉先生之“岳飞军阀论”如是,陈寅恪之于“河北胡化论”“李白胡人论”理应同样如是。
陈寅恪先生关于“河北胡化论”的论述,亦为今天网络上一小撮人拾其牙唾,长期散布,甚至进一步曲解散布为“唐朝鲜卑论”。
有些是不识者为人所欺,或因为对“民国大师”和“史学大家”的盲目迷信,以讹传讹;有些就不免是曲解历史,别有用心了。比如在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添加一句「李渊之先本为鲜卑杂胡,其家世为鲜卑破落户」,四处散布,笔者也曾为其所欺,对照原文才发现是恶意篡改。
唐朝时有影响甚大的著名高僧法琳,积极投身佛道之争,出于抵制道教发展的宗教目的,对李世民胡说“陛下并非老子李耳后人,而是胡人后裔”,被勃然大怒的李世民下狱,以讪谤罔上之罪,死于流放途中。
同样,今天竭力鼓吹“唐朝非汉人王朝论“的那些人,恨不得将从秦始皇到朱元璋都考证成胡人的那些人,其用心也无非也是和当年的法琳一般,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当真针对李世民子孙的血统,目的无非或为摧折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志气,故意搅浑水罢了。
笔者虽然才学见识万不敢比拟前辈大家,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是做此文正本清源,以明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