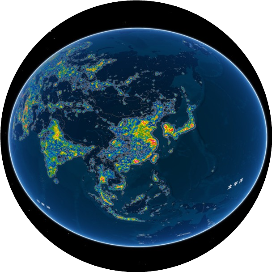以北京和成都为对象,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在都市圈范围内研究超大城市非户籍人口职住空间格局和通勤特征。研究发现:(1)跨城通勤成为超大城市重要的通勤方式,超大城市都市圈正在形成。(2)超大城市非户籍人口居住和就业呈现“圈层加放射”式分布格局。(3)超大城市非户籍人口就业郊区化滞后于居住郊区化进程,非户籍人口职住分离程度高于常住户籍人口。(4)超大城市都市圈外围地区承担着中心城市人口外溢和集聚外来人口的双重功能,并具有明显的过度通勤特征。最后,提出超大城市都市圈非户籍人口职住空间布局的优化策略。
★
张 莉,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公司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王 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余加丽,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非户籍人口市民化和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深圳、上海、广州、北京、成都、天津等超大城市流入人口总规模已达到5 000万。超大城市既是我国非户籍人口的主要分布地,也是进行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重点。以超大城市为对象,研究都市圈范围内非户籍人口职住通勤特征和空间格局,判断非户籍人口就业与居住的问题和难点,对于推进非户籍人口市民化、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大城市居民职住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职住平衡、职住空间、职住分离和职住通勤是重要的研究主题。研究认为职住平衡是西方城市规划界在与“城市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规划理念,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的探索城市通勤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国内学者以北京、广州、上海等超大城市为对象,利用人口普查、问卷调查、手机信令数据、公交卡数据等资料,对城市居民职住空间、空间错位、通勤模式、通勤成本等进行了研究,流动人口、农民工通勤特征与职住关系亦成为研究对象,都市圈跨城通勤特征、通勤模式成为衡量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本文在既往研究基础上,以北京和成都两个超大城市为对象,利用全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和手机信令数据,在都市圈范围内研究非户籍人口职住特征、定居意愿与空间格局,探讨在都市圈范围内解决非户籍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通过手机信令大数据进行用户行为分析、职住空间分析、城市功能地域划定,是当前规划研究重要的数据获取技术方法。本文主要利用联通手机信令数据,基于微观视角对比不同属性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和职住通勤等差异格局。北京都市圈采用2019年度6月份的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采集范围包括北京、天津、廊坊、保定4个城市。成都都市圈采用2018年10月份的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采集范围包括四川省全省。手机信令数据来源规范可靠,经过了脱敏处理和识别规则验证,并根据两大城市手机份额进行了扩样处理,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本文把同时满足3个条件的手机持有者界定为非户籍人口。一是在某个城市居住或工作但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异地;二是春节期间1—2月份不在该城市;三是暑假期间7—8月份在该城市。常住户籍人口是指该城市常住人口中减去非户籍人口以外的其他人口。为了验证数据的可用性及准确性,将北京手机信令识别到的居住人口和六普常住人口进行线性相关性分析,发现区县级两者数据的相关系数为0.93,乡镇级两者数据的相关系数为0.74,表明采用手机信令进行城市职住通勤分析是可行的,也说明手机信令数据在越大的空间尺度使用,误差越小。
使用通勤率度量区域之间的通勤联系强度,通勤率以乡镇、街道为统计单元。北京和成都市域范围内,计算乡镇、街道去往中心城区的通勤人口占本乡镇、街道总通勤人口的比重;市域外计算乡镇、街道去往中心城市的通勤人口占本乡镇、街道总通勤人口的比重。
运用马丁(Martin)提出的空间错位指数(SMI)来测度非户籍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程度,匹配程度越高即空间错位程度越低,SMI越小,反之则SMI越大。SMIj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P
ij
是
i
区县
j
属性(非户籍、户籍)的居住人口数,
e
i
是
i
区县的就业人口数,
P
j
是城市
j
属性的居住人口数,
E
是城市就业人口数,
n
为区县个数。
都市圈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形成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城市功能地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把都市圈定义为“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通勤联系是都市圈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跨城通勤联系成为研究、界定都市圈的重要依据。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北京市和成都市与周边城市的通勤研究表明,都市圈通勤已经成为超大城市通勤的重要形式,北京市、成都市通勤范围均超出行政边界延伸至周边中小城市。
以乡、镇、街道为单元计算都市圈范围内通勤率,形成北京市和成都市通勤势力范围图(图1、图2)。北京市通勤半径超过50 km,成都市通勤半径东西方向主要在30 km范围内,南北方向达到50 km。把前往中心城市通勤率5%以上的县级单元纳入都市圈,三河、大厂、香河、武清、广阳、固安、涿州、涞水等区市县形成密集的环北京通勤圈,北京市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远郊区部分乡镇与中心区通勤率尚没有达到5%。成都市同样形成密集的跨界通勤圈,主要分布在什邡市、广汉市、中江县、乐至县、雁江区、仁寿县、彭山区的环成都地区。以1%通勤率为标准,北京市远郊区和市域外围的安次区、永清县进一步纳入都市圈,均在北京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确定的50 km半径通勤圈内;成都都市圈则基本包括了德阳、眉山和资阳3个地级市,与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在推进的成德眉资同城化战略范围保持一致。

超大都市圈范围并不是一条固定的边界,而是随着识别标准、考察时间的差异而不同,也会随着交通设施建设、城市管理要求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尽管边界处于不稳定状态,超大城市与外围地区同城化发展的都市圈正在形成。探索超大城市都市圈职住关系的空间格局和分布规律,对于优化引导都市圈人口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3.1 北京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非户籍人口居住和就业均具有“圈层加放射”分布特征
从非户籍人口居住和就业的数量分布看,北京市和成都市的核心区都是非户籍人口分布的洼地。从核心区向外围,非户籍人口逐渐增多。北京市在二环到四环沿线形成非户籍人口居住和就业的集中分布区域,成都市非户籍人口主要分布在一环路到绕城高速之间区域,两市非户籍人口分布均呈现出圈层分布特征。
从北京市四环路和成都市绕城高速继续向外拓展,非户籍人口呈现出“廊道+组团”式分布特征,重要交通沿线出现非户籍人口聚集规模大、比例高的典型地区。北京市西北部(北七家镇、回龙观地区、沙河镇等)、东部及东南部(八通线沿线、马驹桥镇、亦庄镇等)、环京区域(燕郊镇、固安镇)形成多个非户籍人口集中分布地(图3)。成都市外围非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人民南路—天府大道沿线、双流城区,西北部郫都城区,东北部新都城区,东南部龙泉驿城区等地,放射状分布特征明显(图4)。

3.2 北京市和成都市非户籍人口居住地和就业地均具有明显的近郊化趋势,非户籍人口职住分离趋势明显
为定量比较北京市、成都市的非户籍人口分布特征,参考北京市2016版城市总体规划和学术研究对北京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的划分,本研究把北京市划分为核心区、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成都市域划分沿用3个圈层的划分方式,在功能上相当于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
北京市核心区和中心城区都具有就业比例高、居住比例低,非户籍人口比例低于常住户籍人口的特点,中心城区是主要的居住和就业空间;近郊区承担了重要的居住和就业功能,居住比例高,就业比例低;远郊区面积小,人口居住和就业占比低(图5)。成都市一圈层仍是最主要的就业空间,二圈层的居住功能高于一圈层,三圈层远郊市县占有一定的居住和就业比例(图6)。

与常住户籍人口相比,北京市和成都市非户籍人口居住地和就业地在近郊区的占比增加明显,在远郊区的占比有所降低,两市非户籍人口居住和就业均出现近郊化趋势。就业与居住比较,北京市和成都市非户籍人口在中心城区的就业比例明显高于居住比例,近郊区居住比例又明显高于就业比例,非户籍人口职住分离趋势明显。
计算非户籍人口与常住户籍人口的空间错位指数,见表1。北京市和成都市非户籍人口的职住空间错位指数都高于常住户籍人口,表明非户籍人口的空间错位问题比常住户籍人口更加严重。与成都相比,北京市非户籍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的空间错位指数更高,职住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

3.3 北京市和成都市非户籍人口比重从中心向外围逐渐升高,外围临界地区形成非户籍人口居住与就业集中分布圈
北京都市圈与成都都市圈非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中心向外围逐渐升高。北京市核心区非户籍人口比重最低,近郊型中心城区比重略有增加,近郊区非户籍人口比重明显增加,环京临界地区非户籍人口比重最高,非户籍人口分布呈现出“异化同心圆”圈层结构。成都市非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同样具有从中心向外围增加的趋势。成都都市圈范围内,天府大道和成德绵乐交通廊道的拉动作用明显,非户籍人口在南北轴向区域的分布更为集中,东部外围组团尚在培育之中。
对北京市和成都市的周边地区而言,来自中心城市的人口是其非户籍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河、大厂、涞水、固安、涿州等县市非户籍人口中北京人口的比例占到40%以上。超大城市都市圈外围地区既承担着中心城市的人口外溢功能,又分担着中心城市集聚外来人口的功能,北京市人口“外溢”范围与强度比成都市更加明显。
4.1 北京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非户籍人口均以去往中心城区的通勤为主导,临界地区跨城通勤联系明显
将北京市核心区与中心城区其他四区合并,计算北京、成都市域各功能区之间以及与市域外的通勤关系。如表2所示,北京市非户籍人口内向通勤比例为16.34%,逆向通勤为4.45%,去往中心城区的通勤量占总通勤量的70.45%。成都非户籍人口内向通勤比例为17.35%,逆向通勤为6.43%,去往中心城区的通勤量占60.74%。北京市去往中心城区的通勤量明显高于成都。
北京市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内部通勤率分别为92%和93%,近郊区内部通勤率只有52%。成都市中心城区(一圈层)和远郊区(三圈层)内部通勤率分别为88%和78%,近郊区(二圈层)内部通勤率为59%。北京市和成都市近郊区都具有跨区域通勤人口多,比例大的特点。北京市跨城通勤人口以中心城区和近郊区为主导方向,成都市跨城通勤人口则以三圈层和二圈层为主要方向。
从通勤流量流向看,外围地区与中心城区的通勤以及临界地区的跨城通勤共同构成超大城市都市圈的跨城通勤形式,环北京区域和环成都区域均形成多个跨城通勤集中的地区。北京市市内及跨城通勤均具有很强的单极特征,向心性明显。成都市域内通勤具有较强的向心性,跨城通勤联系则呈现出双向通勤特征,同城化水平较高。

4.2 北京都市圈以中长距离通勤为主,成都都市圈以中距离通勤为主,北京都市圈和都市圈非户籍人口通勤均具有从中心向外围距离递增的特征
通勤时间和距离是衡量城市职住平衡的重要指标。根据非户籍人口从居住街道中心经实际路网到达就业街道中心的通勤距离和通勤人数,计算非户籍人口的平均通勤距离。北京市非户籍人口单程平均通勤距离为13.8 km,通勤距离主要集中在5—15 km和15—30 km,15 km以上通勤的人口占46.4%。北京市跨城通勤的非户籍人口平均通勤距离达到40.7 km,其中通勤距离在25 km以上的非户籍人口比例高达66%,50 km以上的比例超过了26%。成都非户籍人口平均通勤距离为11.84 km,主要集中在5—8 km及8—12 km两个范围,5—12 km的人口比例占49.1%,15 km以上通勤的人口占23%;成都市非户籍人口跨城通勤距离平均为33.6 km,30—50 km的人口比例达到34%。国际上将通勤时间1 h定义为过度通勤或极限通勤,北京都市圈过度通勤人口规模明显高于成都都市圈。
北京市非户籍人口和常住户籍人口通勤距离均呈现距离城市中心越远,通勤距离越长的特征,通勤距离较长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东部、南部的近郊区及环京区域,远郊区通勤压力相对较小,但是城市功能培育不足,生活质量有待提高。与北京相比,成都都市圈非户籍人口通勤压力相对较小,空间分布同样呈现由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距离递增的通勤模式,通勤距离较长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近、远郊区及交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