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个人生阶段很忙,整天有推不掉的应酬,吃不完的宴请。有时都连上了,直接就从这个饭局被送去下一个饭局,根本不着家。或者两拨人冲突了,不得不专门进行磋商,以保证我的出席。还有那种情况,夜生活过于消耗,榨干了我的精力,最后被送回家时我已经睡得人事不省。
那时我五岁。
五岁时我的社会价值达到了一生的巅峰。
我被十几对青年男女用作约会的利器,陪着他们谈一场又一场的恋爱。我消除他们的尴尬,我促进他们心灵和肉体的接近,我缓解他们的疼痛和悲伤,我见证他们美丽的青春。那时他们无论做什么,看电影,逛公园,轧马路,甚至带回家见父母,都要带着我。他们对我的需求很强烈,强烈到什么程度呢?我把话撂在这儿,没我他们不行。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谈恋爱干嘛要扯上熊孩子。然而这就是三十多年前的社会风尚,在谈恋爱的初期,往往有一个亲戚街坊的小孩参与,而且并不是冒充什么角色,就是光明磊落地以“亲戚街坊的小孩”这一身份参与。仿佛我们的存在能够为恋情宣示一种正当,诚实,信誉,纯洁,庄严,等等。
我们的功能如果写成说明书应该有一整页。简言之,第一条是距离标志,有个孩子夹在两人中间,这两人是没法靠得太近的,这个既给旁人看,也约束自己。第二条是掩人耳目,利用人们在第一条中形成的错觉,暗中突破大防。第三条是作为“题目”用来考察,怎样对待孩子是成立家庭的重大参量,他们都通过我鉴别对方的素质,这一点有点儿像现在牵着狗狗谈恋爱,善不善良?有没有责任心?这些都得靠狗狗试探,所以自己没狗借也要借一条。第四是转移视线,这个功能主要是在他们承受不了外界过高的关注时才得以发挥,比如带到家里了,众目睽睽下他们难免慌乱,就把我推到前线吸睛。有时候我表现得太突出了,以至于很多年后会有完全陌生的亲友长辈热情地招呼我——“你小时候到我们家玩儿,那天晚上吃了太多桃子,拉稀拉了一椅子,你不记得了?”——我猜就是这种情况。桃子我有印象,但成全的是哪一对儿我就不记得了,太多了。
太多了,不记得了。但提那些我因此得到的好处,我就能恢复一些记忆。
在机关游泳池外的冷饮店喝泗瓜泗,粉红甜水水加了冰坨坨,喝得走不动路喝成望娘滩,是跟杜叔叔和小邢阿姨;出了文殊院吃洞子口凉粉,海椒油漫到碗边,锅盔里裹着肉糜,辣红了双眼也停不下嘴,是跟龚家大姐姐和二明大哥;平生第一次吃到正宗下午茶,喝热可可,就一块又软又厚的黄油饼,一抬手黄油流到腕子上,可恨他们不许我舔,是跟唐叔叔和芳妮;平生第一次吃到北方紫铜火锅,筒子里烧炭,涮了肉圆、豆腐和海带,还喝光了蘸料,是跟我姨和姨父。
因为实实在在到嘴了,那么对我来说,每一场我参与的恋爱都是成功的。然而实际上,前面说的那四对,除了我姨和姨父终成眷属,其余都是凄切的结局。他们以为我不知道,但没有我不知道的。
终成眷属乏善可陈,结局凄切才百世流芳。

杜叔叔和小邢阿姨都是机关里的,他长得很帅,她地位很高。他们,“不合适”。这我都是偷听大人谈话听来的。
我妈说:小杜浓眉大眼的,女孩儿就喜欢这个。
我爸说:浓眉大眼没用,这回都没评上副科,就怕……
我妈说:唉是啊,小邢去年就评上正科了吧?她父母还都在省里。
那时都以为杜叔叔迟早会被小邢阿姨吹掉,然而最后却是杜叔叔主动提出分手。这内幕我是上高中了才听说,但稍一回忆,我其实应该是最了解情由的啊,因为他们最后那段忧伤而沉默的时光,我是亲眼目睹的啊。
三十多年前整个成都都很空,很多地方都像旷野。杜叔叔和小邢阿姨带我去的是他们机关后面那片荒草地,更广远稀声。初夏黄昏,草地上开着一丛一丛紫色的苜蓿花,蛇莓已经结了红浆果,黄色的野菊花闪着金光,大片大片狗尾草的穗子像一团团云絮停在低空。我记得我疯跑着逮一种蓝肚子蜻蜓,杜叔叔喊我别跑远了。
小邢阿姨在哭。她脸上湿透了,一动就反射出微光。杜叔叔也没什么话,但他偷眼看她,看了好几下。
他们以为我什么都不懂,为人贪吃而糊涂。别的不敢说,糊涂我可是一点也不糊涂。我甚至感觉到他们今天格外需要我,因为他们今天格外沉默。泗瓜泗我喝了两杯,站起身时差点漾出来,这要搁了平常他们早就乐了,一个讥讽我,另一个卫护我,快活地斗嘴。“你肚子会不会爆炸啊?”“才不会呢!我们肚子通着大海!”“我捅你一下你就成喷泉了!”“不行!我们要捅你的肚子!快来捅杜叔叔的肚子!快来快来捅杜叔叔肚子!”她拽着我捅他肚子,他抱住了她的肩膀,几秒钟。他跑了,她率领我去追,她追上了,我远远看见她抱住了他的腰,几秒钟,他转过身的一霎那,她手松开了。
但今天他们既不理对方,也都不理我,理我也只说了我最不爱听的话,“你别吃了。”
小邢阿姨是刚在草地上坐下,铺开她的白裙子那会儿,哭的。她是北方人,说普通话,哭声也是普通话口音,很正,很规范。杜叔叔也是北方人,他的沉默是沉默而不是哑,是北方式的寂静。
“你的条件……”
“……我的条件。”
“条件不好……”
“……条件是不好。”
我没跑远,蓝肚子蜻蜓不见了,我就围着他们俩跑圈儿。我听见了这个词,“条件”,他们说了好多遍。条件条件条件。最后一个条件是小邢阿姨说的,说完她就伏在自己拱起的膝盖上大哭了。杜叔叔半天没说话,突然叫住我:“别跑了,我都让你跑晕了……我送你回家吧,回头你妈非跟我急不可。”

后面的事情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喝泗瓜泗的好日子到此为止,再就是杜叔叔几年后回北方了。高中时我妈有天告诉我杜叔叔带着老婆来成都,说要到家里坐坐,一再叮嘱我不要提小邢阿姨,又转头跟我爸叹道:“小杜当年可够绝情的,哪有男的提分手的啊……但小杜也是,自尊心那么强,上高干家当女婿他受不了。”
我才知道他们经历过那样一番挣扎,被一个叫“条件”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给分开了。
带我吃洞子口凉粉的龚家大姐姐,是我家对过的邻居,她跟四楼的二明大哥“交”了“朋友”,邻居加同学,所谓亲上做亲。
那时二明大哥刚从部队复员,常常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风纪扣不扣,露出挺括的白色假领,军帽也拆掉了帽徽,并不戴,总是卷着,拿在手上。龚家有四个女儿,大姐姐最美,刘海儿用铁管子烫得卷卷的,大辫子盘在顶上,腰细得跟醋瓶颈子一样细。她有一条纱巾我垂涎多年,玫瑰红底子编进去亮晶晶的黄丝丝蓝丝丝金丝丝银丝丝,谁戴谁像公主,纱巾很少离开她脖子。
大姐姐在校办工厂,校办工厂最好了,都不用去上班的。但区文化馆的职工演出又缺不了她,她报幕。穿了带荷叶边的连衣裙和丁字皮鞋,画了他们说的舞台妆,她漂亮得我和二明大哥都嗫嚅着不敢相认了,在台下听她朗声道:“下一个节目……”我们都深感荣幸,如醉如痴。
两边父母都很熟,是从没有吵过架的邻居,孩子们也知根知底,一看也都郎情妾意的,没有比这一对儿更合适的了。父母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去哪儿都得带上我。
实际上他们只去一个地方,文殊院。不过既不拜菩萨也不赏花木,每次都直奔偏院的那片竹林,坐在一条石凳上。石凳长长的,却没有我的位置,他们叫我“去耍嘛,跑远点儿都莫来头。”我遵命跑出很远,看鸟,看鱼,看草,看天,我真是天资聪颖,知道绝不能回头看他们。
为了奖励我跑得够远,他们常带我吃文殊院门口的凉粉锅盔。红油和花椒,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四川人。有好几次在凉粉店里大姐姐被人认出来是“区里的报幕员”,她却故意转过脸去留给他们一个剪影,二明大哥忽然就木呆呆的,埋头大口喝面汤,使劲吸面条,发出很大声响。
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是从幼儿园回来,经过大门口时看见二明大哥在传达室打公用电话,惊人的是,他哭了,不停地擤鼻涕甩在地上。传达室的大爷领着三五闲人都退到外面,脸上是一种不忍的戚戚,分明是听到了最糟的消息。
同样,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凉粉店,因为只剩下二明大哥一个人了。龚家大姐姐说是参加了一个什么文艺演出,结果被那个文艺单位招工招进去了,专演漂亮姑娘。单位在雅安,雅安虽然没有成都好,但文艺单位却不是业余的,是专业的硬牌的,“多次进京汇报演出,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得到中央领导接见”,我听大人说。
她走了,留下他活在全院老小的注视下。他去食堂打饭,人们看着他;他出来拿报纸,人们看着他;他爸病了他送去医院,人们更关心的还是他;他妹妹结婚,人们祝福的仍然是他。
很多人都听他说过“等她”的誓言,可后来没过多久他就结婚了,娶了另一位邻居姐姐。他的第二次恋爱,我没有参加,没有吃到一样东西。而且他结婚以后虽然并没有搬离父母家,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来往。

去年春节在老院子里我见到了二明大哥,他抱着孙子站在枣树边上晒太阳。阳光照在他灰白色的头上,让我想起了他那顶从不戴的军帽,想起了他金刚石一般的年华。
“回来啦?”二明大哥主动招呼我。
“哎回来了!”我站住,不知道该说什么,想逗一下孙子,但孙子头一歪睡着了。
我感觉到二明大哥没打算跟我叙旧,他大概以为我根本什么也不记得了,他绝想不到我有那么清晰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他抱有深深的同情,心疼。他以为他的爱情里只剩下他自己。而我永远也不打算告诉他,还有我呢,虽然我跑得远。
芳妮让我就叫她芳妮,不让叫孃孃阿姨,而且妮字既不读二声也不读一声,要读成轻声,因为这本来就是个英文名字。在八十年代中期,“洋气”恢复了地位和名誉,上海的很多家庭也都恢复了本来的生活面貌,弹弹琴,跳跳舞,吃点心,穿时装。芳妮并不是假洋气,她是真的,她弹肖邦李斯特,她读海涅普希金,她们家住在思南路,据说在东南亚有家族的橡胶种植园。她喜欢的杂志是《世界文学》,她冬天穿呢子裙,她不吃葱蒜,她决不跳“两步”(一种交谊舞,一男一女勾肩搭背,不管舞曲本身是几几拍,他们只是钟摆似地摇晃),要跳还是快三慢三的华尔兹。
我这辈子只见过芳妮一面,却对她了解到这个深度,全是因为我唐叔叔。他为芳妮“疯掉了”,据我家里人说。他们还有很多描绘他的词,“神之物之”,“痴头怪脑”,“脑子坏特”等等。
唐叔叔是我爸的同学,也学美术,晚很多届。他毕业后去了甘肃,只有过年大家都回上海探亲时,我们才见到。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已经“疯掉了”。
那是一个晚上,很晚很晚,因为爷爷已经洗好脚要去睡,正叮嘱我爸再看一眼前门锁好没有。忽然前门门铃响了,我爸领进来一个蹦蹦跳跳的小伙子,他蓄着一点唇髭,烫过的头发上卷下直,打了一条阔大的鲜红的领带,穿件白衬衣,但里面窝窝囊囊又有几层绒线衫,厚外套搭在臂上,一进来马上就扔到藤椅里。掏出几块糖果给我,拖长声气说:
“囡囡好——。你是小四川,对伐?喊我,我是谁认得伐?”
然而他马上就甩掉我,转向我爸妈了。他其实也毫不关心他们的情况,对他们的寒暄更是不理会,他只是来宣布一个消息的,重大消息。
“我会跳慢三了!——就是华尔兹,晓得伐?——哪,我跳给你们看。”我爸妈像傻了一样,看着他在窄小的厅堂里翩翩起舞。
他自己唱舞曲,虚虚摆出一个揽着舞伴的姿态,跳了一会儿大概觉得不得劲,满屋子找舞伴,但我爸妈都拼命摇头,他又看了一眼我,实在看不上,最终他跳到屋角,端起了我的一个小凳子,搂在怀里旋转着陶醉着。我们全家都目瞪口呆地看他作怪,连爷爷也听到动静从楼上下来,见状愣在楼梯半中,紧紧裹着长袄子像个大蚕茧一样,哆哆嗦嗦地问:
“做啥啦——”
唐叔叔闹到半夜才走。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神经病同学啊?我爸跟我妈解释了好久。
说唐叔叔本来是很正常的,在甘肃分了房子长了工资评了先进,转年就要提级。但是自从春节前回上海,在某工会办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姑娘,他就神经病了。探亲假早就到期了也不回甘肃,单位里连发电报猛催,威胁要记过处分,他也不听,党小组严肃要求他回去,否则就取消“积极分子”资格,他也不听,最严重的是未婚妻都起了疑心,勒令他速归,然而他也扛住了,说这里老娘犯了心绞痛他走不开。老娘犯心绞痛并不假,但那也是因为多次哀求他走他死也不肯啊。
因为那个姑娘,芳妮。
有天中午唐叔叔又来了,跟我爸说要带我出去玩,我爸问去哪里?他低声说去芳妮家里,之前芳妮听他说有个干女儿外号“小四川”,讲一口四川话,蛮好玩的,就要他“带来玩玩呀。”我爸那时困得东倒西歪,想睡中觉,正乐得把我打发出门,当然同意了。
然而我们走到街上,唐叔叔又并不急于赶路,而是给我买了一大块雪糕后带我去了理发店,他要理发,我就坐在旁边吃雪糕等他。等他理完发牵着我走到外面,看眼表,高兴道:“好!正好!这个时候她肯定起床了。”我才知道我等他理发是为了等她睡醒。

芳妮跟父母住在一起,房子是老式的公寓房子,除了厅堂极宽敞,其余开间都小。从窗户望出去,是一棵大树,初春那么寒冷,树叶也都绿蜡一样鲜亮。他们家的窗帘是两层的,一层薄纱一层厚绒布,薄纱上踏着暗花,绒布的颜色这么看绿,那么看又紫了。后来我读《长恨歌》里描写的严师母家的卧室,说到窗帘,地板,家具,房间里红棕色泛着幽光的影调,和既温馨又忧伤的气氛,简直一模一样。芳妮家的厅堂里垂下来一盏吊灯,虽然有残损,但毕竟是水晶,即使纹丝不动也波光粼粼。我站在灯下用四川话念了一个儿歌,“王婆婆在卖茶”,背了毛主席诗词“乱云飞渡仍从容”,芳妮和她爸爸妈妈笑得前仰后合。我瞄一眼唐叔叔,他很得意。“这小孩灵伐?——灵的。”他道。
芳妮斜着胳膊,用手背挡了嘴,笑得泪水涟涟,拿手绢印了印眼角,半天才停下来。“灵的灵的。”她向唐叔叔赞许。唐叔叔高兴得好象要晕过去了。
一时阿姨端来点心给大家吃。首先给我,一杯热可可,一大块又软又厚的黄油饼。我没有经验,吃黄油饼怎么能竖擎,必须横握啊。所以一抬手黄油就流到腕子上。我埋头去舔,引起一片惊呼,芳妮和她妈妈都说:“快快,湿毛巾拿来!不好舔的噢!怎么好舔的呀!小姑娘哪能嘎难为情啦——”可恨他们不许我舔。
倒是唐叔叔没有嚷,他脸上是错愕,我一看就知道他跟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舔,甚至他大概正要舔,我先舔一口完全是替他顶了雷。然而他真不够意思啊,一旦反应过来,就立刻参与了她们对我的规训。
“出洋相了出洋相了出出出出洋相了。”他讲。一边讲一边看着芳妮,羞愧得差点咬了舌头。
我们离开的时候是晚饭时间,人家并没有相留。唐叔叔蔫头耷脑的,直到把我交到我爸手上时他也没恢复一丝活泼。我猜可能是因为我替他丢尽了脸。但实际上当然不关我事,后来听我妈告诉我,那天唐叔叔受了很大的委屈,他隔着门听见芳妮母女的对话,大意是芳妮妈抱怨女儿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唐叔叔才知道原来他算“什么人”。
唐叔叔很快就回甘肃了,我爸还收到他的来信,信里说自己“提了级,结了婚,可谓双喜临门。”然而我们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是几年以后听他老娘说的,他离婚了,正在准备调回上海,难哪,但他说难死也要回上海,因为芳妮一直没有结婚。
(本文摘自故园风雨前《幸得诸君慰平生》,本文图片来自pixab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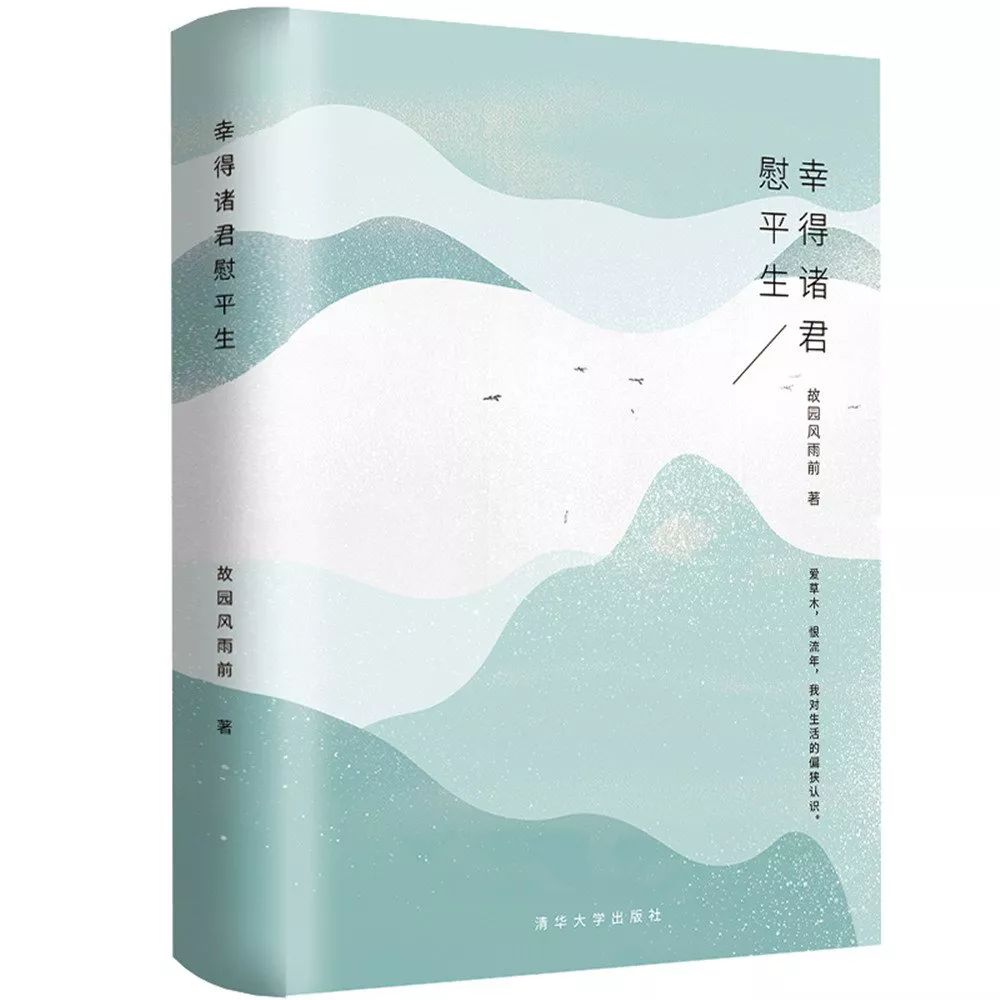
作者: 故园风雨前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12-1
大家都在看这些👇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以下封面图
一键下单「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

▼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周刊书店,购买更多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