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我们常见的两种政策术语。这一段时间,我国“供给侧”改革谈得比较多,那么“需求侧”呢?通过对“需求侧创新政策”发展历程的追溯以及OECD“需求侧创新政策”的研究,或许能够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引言
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后,作为应对创新及生产力效率趋于放缓的一种建议性手段, OECD于2011年5月发布了著名的《需求侧创新政策》(Demand-Side Innovation Policies,DSIP)报告。报告认为,需求侧创新政策是可以“帮助强化创新市场,帮助聚焦在特定挑战和机遇”的一种特殊的创新政策“新组合”。“需求侧创新政策”一般理解为:直接增加公共或私人需求,或间接通过实现以及改进同需求的结合,激发创新和创新扩散的一系列活动。
和OECD发布的很多其他报告一样,政策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了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很多研究认为,需求侧创新政策旨在克服系统失灵,提供创新动机,将创新引导向社会目标和政策需求,并通过开拓市场潜质的方式促进地区/国家的商业发展。
因为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少数核心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的作用,所以从主要政策企业家的视角对需求侧创新政策进行分析,或许可以深化我们的认识。
埃德勒(JakobEdler)需求侧创新政策主张的形成
按照金登(John W. Kingdon)的“多源流模型”理论,
政策企业家是指那些能够成功地让问题流、政治流和政策流三条源流汇合,让政策议题受到决策者关注的人。
从学术文献和政策报告的署名情况来看,现就职于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创新研究所的埃德勒教授是需求侧创新政策的政策企业家:在2007年加入曼彻斯特大学以前,埃德勒博士就担任了德国弗朗霍夫学会系统和创新研究所(ISI)创新系统与政策部主任。与学术界和政策界长期密切联系所建立起来的网络,保证了他能够顺利完成政策企业家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埃德勒博士还能充分理解“本土”政策与境中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理念、动机和关切并及时做出反应——这也是其能够成功完成倡导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2004年,欧盟报告《服务中的创新:现状与发展趋势》(Innovation in Services: Issues at Stake and Trends, 2004),就阐释了“需求侧创新政策”的相关理念——只不过当时埃德勒博士还只是项目组的成员之一,而且没有在出版报告中署名。但这份报告提出,需求和消费者(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并愿意为升级付费的群体)严重不足,已经成为服务业创新的一个重要障碍。对此,一个可能的解决途径就是公共采购以及规制和标准设定。
从政策议程的角度而言,整份报告最大的贡献就是第一次尝试阐明了问题流,并用需求侧这样一种包含了公共采购的政策组合提出了有别于以往的政策流。
但问题恰恰也在于,仅强调“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作为政策拟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有些单薄。
同样,2005年以弗朗霍夫协会的名义出版的另外一本《创新和公共采购:现状回顾》(Innovation and Public Procurement–Review of Issues at Stake)报告进一步对政策流进行了细化,且第一次以“最佳实践”的方式提供了部分OECD国家的案例,但没有包括那些本来研发强度就比较高的国家,而且“需求侧”的提法没有明确的问题指向。另一份2006年发布的报告《需求导向的创新政策》(Demand oriented innovation policy)明确了
政策的问题流是“如何通过激发需求的方式鼓励创新及其扩散”,
报告中所提及的案例也包含了瑞典、芬兰、美国等传统上在供给侧比较有优势的国家;而且政策手段有了扩充,包含了直接支持私人部门对创新产品的需求、普及新的“需求意识”、帮助民营经济力量掌握必要的信息、公共采购等。然而,依然没有明确解决政策问题流自身的问题。
加入到曼彻斯特大学以后,埃德勒博士并没有作为政策建议者活跃在欧盟的舞台上。为数不多的报告之一,比如2009年以工作论文形式发布的“中东部欧盟国家的需求创新政策”(Demand policies for innovation in EU CEE countries)被用以解决经济实力相对偏弱的中东部欧盟国家的转型和追赶问题。这样的一种界定问题的方式是合适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对中东部欧盟国家单纯地强调供给侧政策显然是痴人说梦,相反,需求侧变成了几乎唯一的解决方案。需求侧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政策被OECD接受,事实上也大抵出于同样的原因。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后,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各种凯恩斯主义为需求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于是,三条源流终于得以成功汇合——
需求侧创新政策被特别用于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创新及生产力效率趋于放缓的问题
,代表性的案例也随着问题流的变化进行了重新遴选和表述。
对需求侧创新政策的几点认识
以上虽然只是从埃德勒博士一个政策企业家的角度对OECD需求侧创新政策的发展片段进行了分析,但不妨碍我们得到如下认识:
一是需求侧创新政策绝非“上手可用”(ready-to-hand)的政策工具
。即便对于埃德勒这样的核心政策企业家而言,需求侧创新政策拟解决的问题及其所对应的最佳实践都是在时刻变化的,要适时调整。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根据其对自身经济条件、发展愿景的判断,特别是对“需求”的不同认知、掌控和反应能力,对需求侧创新政策形成不同评价也似乎是必然的。因此,任何照搬照抄甚至刻舟求剑似的盲目标杆都并没有任何意义。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身情况“走自己的路”。
二是需求侧的本质是一种协调,包括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协调以及公共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
尽管(创新型)公共采购、标准和规制始终在政策工具集中占有突出且相对稳定的位置,但却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协调中处于绝对甚至唯一的重要地位。相反,多个报告所形成的共识是,多层级、多中心的“善治”(good governance)下“共享愿景”(shared visions)的建立才是最为关键的——而且一再被提醒和强调的是,“需求侧政策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
三是需求侧的提法而不是政策本身,为OECD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实践开辟了新的空间。
毫无疑问,“需求侧”这一提法在OECD乃至世界更大范围内起到了开创新意识(creation of awareness)的作用。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美国案例并没有被列为典型,仅仅是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智能中小企业市场验证项目(MVP)中提到该项目同美国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项目类似;但与SBIR“巧合”的是,OECD各国的典型经验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放在中小企业。所以说,“需求侧创新政策”最大的创新其实并不在于对(创新型)公共采购的强调,也不在于将目光从供给再次转移到了需求,而是“侧”(side)的提法为欧盟国家探索一种同美国所倡导的(技术推动型)线性创新模型不同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基础。
(责任编辑:张冬梅)

王程韡,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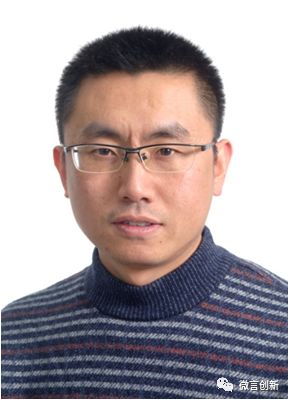
李振国,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碧晖专栏 | 科技园区与产业创新
面向创新热点的讨论工具
提升科技创新服务,上海怎么办?
闻香识书 | 你还在做创新的“门外汉”?
数据时代的五种创新模式【上】
数据时代的五种创新模式【下】
新兴技术向产业演化的瓶颈到底在哪里?(上)
新兴技术向产业演化的瓶颈到底在哪里?(下)
将创新热传导到基层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科技外交
当代创新需重视R&BD和I&BD
关于上海科技创新的挑战和机遇的若干思考

(本文不代表微言创新观点。欢迎投稿、转载和商务合作,请联系
[email protect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