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微信公号改版不按时间流推送,很多哲友可能无法在第一时间读到哲学园文章。为及时看到新推文,可将哲学园“设为星标”。
转自:哲学门
如涉版权请加编辑微信iwish89联系
哲学园鸣谢
长按二维码关注


作者简介:
曹青云,云南大学哲学系
人大复印:
《外国哲学》2017 年 01 期
原发期刊:
《哲学动态》2016 年第 201610 期 第 67-75 页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 本原/ 形式/ 质料/
摘要: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理论(Hylomorphism)”是他的形而上学的重要部分,但它的确切含义似乎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当前流行的“构成性”解释模型把形式与质料看作构成复合实体的不同成分,并认为它们的关系类似于属性与物质对象的关系。然而,这种解释遇到了许多理论上的困难。本文指出,“构成性”模型是对“质料形式理论”的误解,因为形式与质料不是构成实体的两种成分,而是生成实体的两种本原;形式是首要的和终极的本原,它以目的的方式规定着质料之本质;复合实体作为被生成物具有一个存在的原因结构,即形式展现在被实现了的质料之中,质料亦处于形式这一目的之中。“质料形式理论”便是关于可感实体生成的本原和存在的原因结构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可感实体是一种复合物,它由形式和质料复合而成,例如一个铜球是一个实体,它是由球形这一形式和铜这种质料构成的。这一学说被称为“质料形式理论”,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即“hylomorphism”;亚里士多德自己并未使用过这个词,它由后来的研究者所造,“hylo”是希腊词“”(质料)的英文转写,而“morphi”是希腊词(形状、形式)的英文转写。[1]
一
“质料形式理论”之惑
质料形式理论是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他的思想传统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经过阿奎那的继承和影响,它逐渐成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代表。然而,自漫步学派开始直到当代亚里士多德学界,学者们对于“质料形式理论”的确切含义及其表达的形而上学观仍疑惑不已。沙普勒斯(R.W.Sharples)指出,在漫步学派中,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和斯特拉托(Strato)并不关注质料形式理论的问题,他们似乎忘记了它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组成部分。[2]在当代的研究中,刘易斯(F.Lewis)曾说:“尽管亚里士多德总是断言形式和质料构成了个体实体,但它们以何种方式构成实体‘始终是神秘的’。”[3]格雷厄姆(D.Graham)甚至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形式-质料模型本身都是不确定的”[4]。
许多试图理解亚里士多德质料形式理论的努力似乎都失败了,有些学者认为这一重要学说存在着理论缺陷,甚至是不融贯的,因而需要修复和重构。在当代形而上学的讨论中,种种经过修正的质料形式理论正在成为理解和解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主流思潮。[5]然而,在接受这些修正之前,我们需要谨慎反思亚里士多德质料形式理论:它真有理论缺陷吗?抑或这种理论的“神秘的、不确定的”形象根源于我们的误解?
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理论涉及其哲学体系诸多方面的内容,它有几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第一,亚里士多德是如何介绍和规定“形式”和“质料”概念的?第二,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如何?第三,形式与由形式和质料构成的复合实体是何种关系?第四,质料与由形式和质料构成的复合实体是何种关系?其中第二个问题尤为重要。对亚里士多德质料形式理论的探索应当围绕它们展开。
二
质料形式理论的“构成性”解释及其问题
我们先来分析对亚里士多德质料形式理论的一种流行的解释。尽管它以阐述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问题为核心,但它从根本上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用意,这或许是它面临种种解释困境的根源。
这种解释认为,球形和铜的例子最为典型地表达了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正如球形是这块铜拥有的一种形状和性质,形式也是质料拥有的一种性质,即本质的性质。质料与形式的关系类似于个体实体与属性的关系,正如属性可以谓述个体实体,形式也可以谓述质料。[6]所以,质料是一个物质载体,而形式是这个物质载体的本质属性。[7]对形式与质料的这种理解或许来自《范畴篇》中的洞见,有些学者认为《范畴篇》描述的个体实体与属性的关系与质料和形式的关系是平行的[8],因此前者的模型应当成为理解后者的基础。
这种解释与一种对实体的生成和毁灭的解释相关。持这种解释的学者认为,一个具体实体的生成是持存的质料从缺失一个实体形式到获得这个实体形式的过程,因此任何被生成的实体应当被理解为持存的质料与它所获得的形式的复合物。[9]正如个体实体从缺失一个属性到获得这个属性的过程是偶性变化,质料从缺失实体形式到获得实体形式的过程便是实体生成。
这种解释的基本思路是:把形式和质料的关系看作性质与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把形式与质料看作复合实体的“构成成分”或“组成部分”。由此,形式和质料之间界限清晰,它们的关系是偶然的——即质料的存在独立于形式,它获得哪种形式是一个偶然的事件。[10]笔者把这种解释称为质料形式理论的静态的“构成性”模型,它是当前亚里士多德学界的主流解释。
然而,“构成性”模型遇到了许多解释困境,我们在这里简要讨论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形式和质料如何构成一个具有严格统一性的实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复合实体是一个严格的统一体——它只有一个单一的本质。“构成性”模型易于区分形式和质料,但难以澄清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是同一个存在者。个体实体与某一属性构成的复合物在数目上为“一”,但在本质上不是“一”,即它拥有可区分的、不同的本质和定义——它仅仅是“偶然的统一体”,例如“有教养的苏格拉底”只是在数目上为“一”的、偶然的统一体。倘若质料与形式类似于个体实体与性质的关系,那么复合实体便不可能是本质上的“一”。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有些学者把形式-质料与现实性-潜在性对应起来,以便解释复合实体的统一性。[11]然而,在引入现实性和潜在性概念之后,他们发现质料与形式的关系似乎不是偶然的;而即便忽视这个问题,“形式和质料作为不同的部分或成分如何构成一个不可分的实体”仍旧是令人困惑的,因为一个严格的统一体不存在任何可分割的部分。对于“构成性”模型而言,复合实体的统一性问题似乎是无解的。
第二个解释困境是“构成性”解释似乎认为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当人们把“构成性”模型中的形式-质料与现实性-潜在性结合起来时,这个矛盾便显现了,因为质料获得何种形式是偶然的,但是潜在性实现为何种现实性却并非偶然。这个矛盾在分析生物体的形式与质料时表现得尤为突出。球形与铜块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偶然的,但视力与眼睛之间的关系并非偶然。例如,失去视力的眼睛不再是眼睛,而只在“名称”上被称为“眼睛”。(412b13-15)阿克里尔(J.Ackrill)指出,根据形式与质料之间的偶然关系,亚里士多德对灵魂的定义是不融贯的,因为灵魂定义表明身体(作为质料)的存在依赖于灵魂(作为形式)——它们的关系是必然的。[12]阿克里尔提出的问题对于质料形式理论的“构成性”模型来说是无法回避的:有人提出了调和两种矛盾关系的解释方案[13],而有人则认为亚里士多德持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质料形式理论。[14]
第三个问题是“构成性”解释倾向于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理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模型,这造成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不仅表现在《范畴篇》和《形而上学》在实体观上的冲突,还表现在Z卷和H卷中交织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质料关系;这个矛盾甚至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神学的分裂。[15]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极其失望的图景:亚里士多德在一个如此重要的基本问题上未能给我们一个融贯的解释,而只留下了碎片式的文本。当然,有些学者采用发展论来解释这里的冲突和矛盾,并认为现实性-潜在性模式是对早期的形式-质料模式的代替,这种观点的代价是需要回应对于发展论的各种反驳。
我们对这种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质料形式理论的描述或许是简略的,但它的核心观点已经呈现。我们发现它无助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观点。显然,在遇到如此多难解的问题之后,它的捍卫者们不得不宣称这些观点是“神秘的、不确定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它自身是空洞的,因为在《范畴篇》的形而上学图景之外,我们几乎所知寥寥。
三
形式和质料作为实体之生成的两种本原
要了解形式和质料的关系以及形式、质料与复合实体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引入“形式”和“质料”概念的。
质料形式理论的“构成性”模型的支持者们把形式与质料看作类似于属性与物质对象的关系,并以为这是从《范畴篇》中得到的洞见。这种观点未免过于武断。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并未提及“ϵιδοζ ”(质料)这个词,而“ϵιδοζ”这个词在这里用来指“种”而非“形式”——它是像“人”、“马”这样的抽象概念,但不同于“灵魂”。《范畴篇》也没有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复合实体”,相反,它反复强调他是单一的(3b10-12)、不可分割的和没有程度差异的(3b24-25)。另一方面,《范畴篇》的一个要旨是区分了实体与属性,倘若形式的本体论地位犹如属性,那么我们便难以理解为何亚里士多德一再坚持认为最终只有形式才是实体。(1029a29)事实上,《范畴篇》并未提出任何质料形式理论,因为它并未涉及个体实体的生成与毁灭,更没有探究个体实体的内在原因结构。
亚里士多德是在研究一个具体实体之生成的语境下引入“形式”和“质料”概念的。在《物理学》第1卷中,“质料”概念和与之相应的“形式”概念是围绕自然实体的生成而被提出的;为了描述和解释一个自然实体何以能够生成,亚里士多德引入了两种本原(或作为本原、原则的“元素”),即形式和质料。他说:“显然,如果一些本原和原则构成了自然对象,并且……每个对象的产生就是其在实体意义上的生成,而不是偶然的生成,那么任何对象都是从基体和形式而生成的”。(190b1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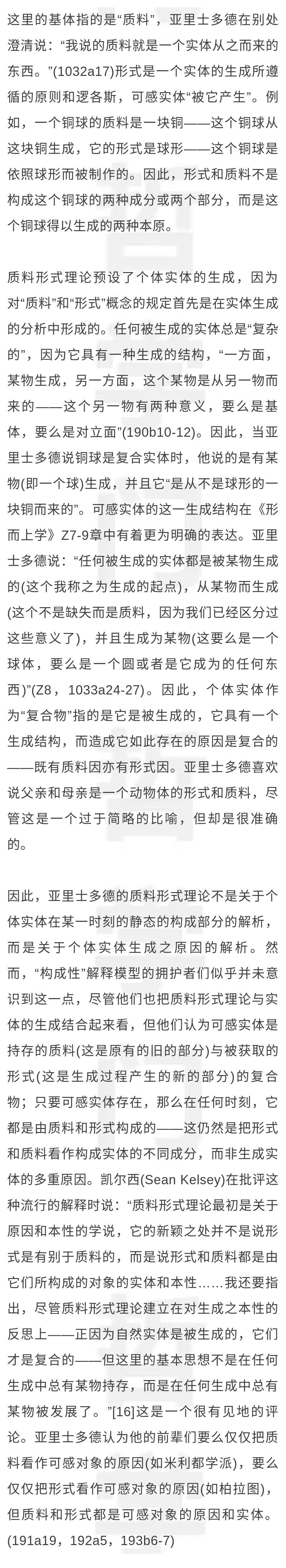
或许,有人认为将形式和质料作为可感实体的“原因”是令人困惑的,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处于后休谟时代。当代人理解的“原因”和“因果性”仅仅指时间上在先的、产生一个事件或对象的充分条件,它们与这个事件或对象的本体论意义无关。例如,书房的玻璃窗碎了,引起这个事件的原因是一块空中飞过来的小石头击中了它。亚里士多德的“原因”概念则要宽泛和复杂得多,在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和质料因中,似乎只有动力因可以被解释为现代意义上的“原因”。“今天,在后休谟时代的讨论中,因果性限制在事件的因果性上,而这种因果性通常意味着动力因。”[17]例如,荷马铜像的动力因是制作这尊雕像的工匠;有些学者认为工匠的制作活动恰恰是现代意义上的这尊雕像的“原因”。[18]然而这并不准确,因为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动力因是工匠头脑中的制作雕像的技艺(195a6-8),而这归根结底就是雕像的“逻各斯”和形式。
因此,在面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时,许多学者并不主张把它们理解为因果性中的“原因”,而是认为它们是关于对象的四种“解释模式(modes of explanation)”,[19]分别回答了四种“为什么”的问题,即它们是四种类型的“因为什么(because)”。[20]
然而,把“四因”看作对一个对象的四种“解释模式”的观点是肤浅的,它的动机来自于把亚里士多德的“原因”概念整合到后休谟时代的“因果性概念”之中。我们注意到,在现代的因果性概念中,原因具有时间上的在先性和产生性(productiveness),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和偶然的。例如,砸向玻璃窗的小石头与破碎的玻璃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如果当时刚好横向吹来一阵风,那么这块飞行的石头或许并不能导致玻璃破碎。因此,现代的“原因”概念只具有解释上的优先性,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原因不仅具有时间上的在先性和产生性,而且它对结果具有绝对的规定性,它与结果的关系是内在的和必然的(190b20,198a6),它恰恰展现在结果之中并与之“共在”;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原因”概念在本体论上是优先的,它们是本体论世界中的奠基者;正因为这种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它们才能成为对结果(即个体实体)的某种解释。为了与现代的原因概念相区别,我们最好把亚里士多德的“aitia”称为“本原”。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1卷的开篇说道:“在任何一门科学中,如果研究的对象是有原则、本原和元素的,那么只有通过对这些东西的了解,我们才能获得知识和理解。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知道了一个事物,直到我们熟知了它的第一本原或第一原则,并把我们的分析深入到它的元素中去。”(184a10-14)在确定自然实体的本原是什么及其有多少个的讨论中,他提出了“形式”和“质料”概念,并在第2卷中明确了可感实体的四种本原并最终归之于形式因和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通常是重合的,198a24-26)。因此,质料形式理论是关于可感实体之本原的研究,形式、质料与个体实体并不在同一个本体论层次上;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实体处于一种依附的和衍生的地位(1037a29-31),它在本体论上并不是最基础的,而这正是《范畴篇》尚未触及的内容。
因此,我们并不能从《范畴篇》的实体观中得到关于质料形式理论的洞见,质料和形式作为实体与苏格拉底这样的个体作为实体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一点可以在《形而上学》中得到确证。(Z3,1028b36-1029a3;H1,1041b25-31)所以,形式和质料不可能是性质与物质对象的关系——无论我们是否把这种性质看作本质的或实体性的。那么,作为两种本原,形式和质料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系呢?
四
形式与质料:两种本原间的关系
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是质料形式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从直观上看,质料与形式的区分是明显的,前者是一个物质性存在者,而后者是非物质性的原则。然而,形式不是与物质对象相分离的、超越的存在者,而是驻于对象之中的逻各斯,它是可感实体的内在本原,亦是可感实体之所是的由来。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质料与形式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毕竟一个物质对象和在定义上可确定的内容最容易让人联想到个体实体与属性的关系,以至于认为它们只是一种偶然的谓述关系。理解这个问题的最好角度是潜在性和现实性,而亚里士多德也是用“潜在性”和“现实性”概念来解释“质料”和“形式”概念的。
潜在性和现实性是一个存在者的两种存在方式,潜在的存在者与现实的存在者不是对两个不同存在者的区分,而是对同一个存在者的不同存在方式的区分,这种区分可以应用于任何范畴中的存在者。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既称潜在地看见又称现实地看见的人为‘见者’,同样,我们也称能思的和正在思的人为‘思者’……类似地,对实体而言,我们说赫尔墨斯在石头中,半条线段在一条线段中,还未成熟的东西被我们称为种子”。(1017b3-7)人们总是在潜在者和现实者的相互对照中来理解它们;《形而上学》
Η6进一步指出,“潜在性”和“现实性”概念是无法定义的,我们只有通过类比的方式把握它们。(1048a36)这对概念有两种典型的示例:一种是能力与运动,另一种是质料与实体。(1048b9)亚里士多德把质料规定为“潜在的实体”(1042a28),而形式是现实的可感实体中的内在本原;就现实性而言,形式与可感实体的区分是不重要的。
亚里士多德用“潜在性”和“现实性”概念来解释可感实体的生成,他说:“现实者总是从潜在者中生成,并被某个现实者产生,例如人被人产生,音乐家被音乐家产生。”(1049b24-15)结合我们上面谈到的可感实体的生成结构可知,可感实体作为被生成物是现实的实体,但它是从潜在的实体——即质料——中生成的,并且它因形式而产生,形式存在于同种类的另一个现实者之中。因此,可感实体的生成是从一个潜在的实体到一个现实的实体的过程,是质料在形式的作用下从潜在的实体发展为现实的实体的过程,亦是形式从在质料中的潜在存在落实为在可感实体中的现实存在的过程,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称质料潜在地拥有形式(1034b1),而可感实体现实地拥有形式(1050a6)。实体的生成是一个质料被形式改造直至被完全统治的过程,也是一个存在者从“质料性的”、潜在的存在方式发展为“形式性的”、现实的存在方式的过程。因而,形式不是在生成结束时才被获得的,而是贯穿于生成过程之始终的原则,它指导着生成过程的每个环节,并在生成结束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
然而,能够接受形式改造和统治的质料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是与形式本身有着必然的关系。例如,能制造成斧子的质料是铁或铜,而不是木头或泥土;能长成橡树的质料是橡籽,而非其他。这种“必然关系”体现在形式作为目的对质料的“拣选”以及质料在本体论上对形式的依存。
质料作为潜在者是因为它能够成为现实者,潜在者在自身的规定性中预设了作为目的的现实者;换言之,潜在者是为了现实者而存在的,而它对目的的指向集中地表达在实体的生成过程中。因此,一个特定的形式以作为目的的方式规定了与之相应的质料。
此外,形式对质料的规定性还表达为形式在本体论上优先于质料。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 Η8中指出:“现实性在实体上是优先的。”(1050a4-10)这说的是潜在者的本质依赖于现实者的本质,即潜在者“是什么”是由现实者之所是决定的;这种决定方式又与目的论有关,即潜在者是为了(成为)现实者而如此存在的。[21]
因此,形式和质料作为实体生成的两个本原,它们之间具有必然的关系:一个特定的形式规定了一种特定的质料,而一种特定的质料预设了一个特定的形式。形式是质料的目的并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性,这意味着形式是两个本原中更为基础的那个,它是终极原因、首要的存在(primary being)和第一实体,而质料是依存于形式的次要本原。如果非要用一种模型来概括形式和质料的关系,那么我们说它们是在实体的生成中遵从的原则和展现的功能(ϵςγον)与适宜展示并能逐步完善这些原则和功能的物质对象的关系。
五
可感实体的存在及其内在原因结构
质料和形式是可感实体之生成的本原,那么对于可感实体的存在呢?它们与可感实体之存在有着怎样的关系?从上述讨论中,我们知道任何可感实体都是被生成的,即它的存在是一个生成过程的结果。但形式本身是不被生成的,质料作为生成的基体也是不被生成的,被生成的只是一个具体的可感实体。亚里士多德说:“正如我们不生产基体——即这块铜,我们也不生产球形,除非在偶然的意义上,因为铜球是一个球形,而我们生产的是前者,因为制作‘这个’就是把‘这个’从一般的基体中制作出来。我的意思是制作铜球不是制作圆形或球形,而是别的东西,即把这个形式生产进别的东西之中……因为我们从铜和球形那里把它(铜球)制作出来;我们把形式带入这个特定的质料中,而结果正是一个铜球。”(Z8,1032a28-1033b11)铜球作为被生成的实体,它是一个“在这块铜之中的球形”;对它的制作过程正是把形式带入特定的质料中,即把球形完全融入和表达在这块铜之中。因此,被生成的可感实体应当被描述为“在质料之中的形式(enmattered form)”。
上文中谈到了“质料”概念是指实体生成的“从之而来者”,它是在实体生成之前存在的,我们称为“先在质料”。实体的生成过程是“先在质料”在形式的作用下从潜在者变为现实者的过程。当一个可感实体被生成以及它的生成过程结束时,质料便从潜在的实体发展为现实的实体,而形式作为非物质形态的逻各斯便落实为这个现实实体的内在本质。因此,当一个可感实体现实地存在时,作为潜在者的质料已经不存在了——它在生成结束时变成了现实者,因为它获得了自身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说:“质料是潜在存在者,因为它能够获得它的目的;而当它现实地存在时,它就在它的形式之中。”(1050a15-16)因此,当质料变成现实者,可感实体经由生成而得以存在时,“质料在它的形式之中”——这是指质料达成了它的目的、获得了形式,它处于一种完备的存在状态之中。[22]这种“在形式之中的质料”是被实现了的质料,不再是先前的潜在者。
因此,就一个可感实体的现实存在而言,它的形式是“在质料之中的形式”,而它的质料是“在形式之中的质料”。形式和质料彼此的“在之中”就是一个可感实体的存在结构。可感实体的定义恰好反映了这个结构。亚里士多德指出,对可感实体的定义与对形式的定义是不同的[23],因为任何可感实体都是“一个特殊的形式在一个特殊的质料之中,或者特殊的对象处于一个特殊的状态”。(Z11,1036b23-24)所以,对可感实体的定义必须既包含它的形式也包含它的质料,例如我们应当把“门槛”定义为“一根木头或石头放置在这样的位置”(H2,1043a8),把“房子”定义为“砖石和木材处于这样的位置”(1043a9)或者“砖石和木材为了遮雨蔽日而处于这样的状态”。
在可感实体的存在结构中,形式和被实现了的质料是不可分离的,因为原先的潜在者(先在质料)已经变成了现实者;经由实体的生成,形式实现了对质料的完全统治,而质料实现了对形式的完整展示。因而,一个可感实体只有一个定义和本质,或者说它在本体论的层次上是单一的、不可分的和无部分的,这正是可感实体作为严格统一体的意义所在。[24]更准确地说,可感实体作为“复合物”关乎的是其生成的意义,而作为“统一体”关乎的是其现实存在的意义。
可感实体的存在结构亦是它的内在的原因结构。“在形式中的质料”或者说“被实现了的质料”已经获得了自身的形式和目的,它不再朝向这个目的而运动,但它本身仍旧是“为了形式而存在的”,只不过此时它的目的在自身之中,因此它也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着”。形式是实体生成的首要本原,在生成过程中,形式潜在地存在于质料中并规定着质料的运动;当可感实体现实地存在时,形式以完备的方式落实为可感实体的内在本质,它便是可感实体在自身之中拥有的目的与功能。一个可感实体从生成到存在,形式作为本原和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完善的展现。因此,形式不仅是实体生成的本原,亦是实体之存在的本原。可感实体的现实存在展示了这样一种原因结构:被实现了的质料仍然以形式为目的(同时形式在质料自身之中),并仍然在本体论上依存于形式,而形式是可感实体存在的终极本原。质料的“同名异义”原则就是对这一原因结构的反映。
亚里士多德在多处文本中谈到这一原则,他说:“并不是在任何状态下的手指都是一个生命体的手指,死了的手指只是同名异义上的手指。”(Z10,1035b22-25)《论灵魂》第2卷第1章说:“如果(本质或灵魂)从斧子之中消失,那么它就不再是一把斧子,除了在名字上还被称为斧子……当眼睛不再能够看见,那么它就不再是眼睛,除了在名称上——它不过是像雕塑的眼睛或者画上的眼睛。”(412b16-22)因此,无论是斧子还是手指和眼睛,如果它们失去了在自身之中的本质,那么它们仅仅保有这个名字,但实际上已经不作为斧子、手指和眼睛而存在了,因为在可感实体的现实存在中,被实现了的质料仍旧在本体论上依存于形式,一旦与形式相分离,那么它就不再是原来的质料了。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一个可感实体的存在不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仅仅在那里的,而是作为某类事物中的个体——它的存在就是它如何作为这样的事物。生物体是可感实体的典型代表,它们的存在就是如何活着。(415 b13)因此,可感实体的存在是“动态的”,它表达为自身的各种功能和活动。我们在经验世界中遭遇的总是复合实体,或一个个具体的可感实体。我们不可能面对一个分离的、超越的形式,也不可能面对一个独立的、自足的质料;然而,倘若我们要真正理解个体实体的存在,理解它们特有的功能和活动,我们就必须深入到它们的生成和存在的原因结构中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理论所揭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