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潜伏,刺激!”——余则成
世相如迷宫,走不出来的人,都是迷宫的潜伏者。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 心中覆盖悲伤
在悲伤里忍受孤独/ 空守一丝温暖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温暖若侈在你心里/ 愿用一生祝愿
生命只为一个信仰/ 无论谁能听见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 心中覆盖悲伤
在悲伤里忍受孤独/ 空守一丝温暖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在剧情结尾的地方,意外事件再次扰乱了人们关于“未来”的全部计划,击碎了脆弱的时间经验;对此,飞机上的吴敬中不禁慨叹:
“在天上也要受支配啊。”
他身边的余则成却评论道:
“命!”
对其中的语气无法进行盖棺论定式的简单把握,其中既有顺从和创伤式的哀婉成分,也富含有愉快、爽朗、乃至暗自欣喜的成分。种种要素的这种复杂组合并不奇妙,也不矛盾,这是一个深深体验过
“命运”和“偶然”
之活生生的力量的人的正常反应。
《潜伏》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命运”和“偶然”是世界的根本性要素,它施展至高无上的力量,处处带来混乱,既造就巨大的创伤,也造就巨大的幸福,而这两者都让人既陶醉其中,同时又难以承受;这一切都构成了基本的生存经验,这样的经验与任何意义和秩序都没有任何关联,相反,它完全摧毁了生活实践中所有导向体系的有效性,换句话说,所有这些经验都与文化方面有可能指导人类活动的阐释模式产生了强烈而本质上的拒斥。
谁有这样的经验,谁就将跨越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界限
;
谁如果不跨越对世界和对自我的日常理解,谁就无法将这些震撼人心、未被阐释和不可阐释的事情保持在感知和回忆的疆域之内。
没有谁能比
莎士比亚
更为典型地呈现《潜伏》的世界:
上帝啊!我多想能够展读命运的书卷,
看看时代的变迁,
看看偶然的机运如何把人作践,
变数如何将不同的酒浆向人生的酒杯倾灌!
啊!要是这一切都能看得见,
看见自己一生的流年:
过去有几多危难,未来又有几多考验,
那么,世上最幸福的青年也愿意合上这书卷,
静静地坐下来,安待终年。
命运破坏了“文化”所要求的意义和时间秩序,让它变得混乱,并对人类的精神提出了严厉挑战,要求将行动、受难与时代变革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完全一致,而非完全矛盾。余则成内心以及生活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应该首要地归因于这一点,而非某种“信仰的飞跃”;正是命运迫使他以创伤为代价,不断跨越理解的日常界限。
对于成熟状态的余则成来说,如果失去那种种令人不安、甚至是摧毁性的时间变化的经验,生活将难以想象;如若没有人试图作出克服和战胜这些经验的努力,生活也同样是难以想象。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段段的历史,勾勒着过去时代的本质,当与余则成互为知己的吴敬中在空中以总结式的口吻最后一次询问余则成“为什么坚持留下”的时候,余则成的回答是清晰无误的:
“我喜欢潜伏,刺激。”
有规范力量的事件和个人、以及社会对这些事件和个人的回忆,构成了一个群体的认同。在余则成的历史世界和当下世界中,没有哪一件事情具备规范力量,可以像美国革命对美国人、或者法国革命对法国人的意义那样,足以以之为坐标,建立起他的自我理解。实际上,任何事件或个人均完全有可能在余则成的生活中扮演自我理解的参考值的角色,这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战争、阴谋、屠杀等等事件,也包括
左蓝、吴敬中、翠平、李涯
等等人物,但很显然,余则成与这些人所持态度竟是如此若即若离、晦暗不明,致使其能否成为价值坐标大成疑问;在价值领域,余则成可说是经历了从完全混乱到完全自由的奇特变化,是本能和他对基本善的直觉判断引导了这一变化历程;确切地说,余则成最终学会了将价值领域视同宗教领域,他用纯粹的头脑去理解世界,用纯粹的心灵去体悟价值。这使他不愿建立起一个非宗教的、被称为“文化”的认同。
命运在余则成的生活以及自我评价中持续不断地发挥出
摧毁性的力量
,带着这种力量的事件链条对所有出自文化关联的认同均构成致命的威胁,对于余则成这样具有高度敏感性和高度才能的人来说,如此情景,只有命运才足以成为其生活中具有关联性的一个既不可逾越,又可无限扩展、没有边际可言的边界。
因此,《潜伏》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部悲剧,余则成也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悲剧虽然讲述了令人陌生和恐惧的事情,但悲剧也将一切的恐怖化解为一个可被理解的事件,使之得以进入有意义的时间秩序当中,由此恐怖便被阐释为文化,完全丧失了其罕见的毁灭性。《潜伏》并不具备这样的性格,它的真正性格在于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无意义必须成为意义的构成要素,它迫使人们直接面对日常生活薄薄盖子下面的恐怖要素,不无必要地偶尔考虑一下有关罪恶的沧桑正道。
余则成的时代尽管混乱,但也是一个总结的时代,在慌乱和战争的硝烟之下,隐藏着一种处处进行广泛审视的精神。不安、考验、失败、疯狂,所有这些词语都可以单独用来描述这一时代的氛围。吴敬中不厌其烦地告诉余则成:
“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
他期待的是
以稳定和固定的方式来实现靠风暴才能解决的事情
,他参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面相,因为他自己就长时间地以精英身份置身其中。这种“扎根于人情”的政治以利益与政府的存在理由之间的一致为最基本前提。吴敬中屡次告诫余则成
“远离政治”
之时,政治领域在他的思考中只获得一种纯工具的视野,是“社会”的当前处境和已知条件的直接延伸而已,它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和巩固已经存在的一切。对吴敬中来说,政治也许是独立的,但这是因为政治什么也不会创造,它最理想状态下的任务也就是纠正社会自发的危险风向;“人情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
18
、
19
世纪的英格兰普通法思维
,即将社会关系视为先于政治共同体的表现,因而更为本质于政治表现;至于其具体的运动形式,吴敬中的思维则典型地呈现出
19
世纪“法制国家”的形态
,政治在此一形态中获得了最为明确、最具科学化的理解,那就是一种在法定的状态中得到确立的社会。
吴敬中从教养上看颇具现实主义的政治眼光,“普遍利益”并非社会真理的表达,他所理解的财产以当前的社会隶属状态为前提,而非以个人为前提,统治权则体现为财产的集体占有形态。政治权力在这种最强有力的现实主义视野中,必须首先退回到社会特定利益绝对必须的界限之内,普遍利益只是团体利益的简单复合。在这个团体世界或者社会隶属的世界中,
每个团体都了解一些未被其他团体了解的事情,因此每个团体多少都有一些特殊的利益
。稳定有效的为政之道就在于谨记并顺从这一点。
然而在
左蓝的世界
中,——
政治却是人性的园丁;普遍利益以及社会附属利益的一统
既不遵循
斯密
的想法,是所谓利益的“自然属性”的产物;
也没有可能像
边沁
所确立的那样,是人为属性的产物;换句话说,这一切并非来自某种社会契约或者政治理性,相反,它只能来自本性的再造。政治将因此重新获得一个开端,以摆脱一切人情世故的造化本性。腐败的精英、以及难以理解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数代的时间之后,把国家引入歧途,大众直觉是惟一可能把国家这艘处境危急的航船引向正道的力量。
在吴敬中呼唤“人情”的地方,左蓝呼唤“美德”;“人情”与“美德”的断裂以及根本性对立,最终导致了政治理性无法处在人类呼吁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是理解余则成全部思考和行动的惟一关键所在。确切地说,
“人”与“美德”的断裂,导致余则成无法心甘情愿地认同其中任何一方
,他的生活也就成为时代矛盾的直接反映。余则成就教养、爱好、倾向、甚至语言来说,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他连接当前统治精英的纽带;然而,“人情政治”并未产生真正的精英,崛起的只是封闭的寡头团体。当前的统治阶层只是一个闭关的组织和秩序,而丝毫不是一个富有弹性、有自我保护直觉、有非凡的自我更新能力的活动阶层。

先知
默罕穆德
曾经试图把一座大山召唤到眼前,那山却懒惰得纹丝不动,于是他说:
“既然山不来我这儿,那我就去山那儿。”
大山并未向余则成走来,余则成也不曾向大山靠拢。
“人情”与“美德”的断裂恢复了政治生活不可捉摸的特征,有助于产生一种令人惊奇的力量,结果被置于无法预料的状态,仿佛是微笑中的斯芬克斯,余则成就是他的化身。
人们推测他的选择的奥秘,想从他所表现的不确定中获得明确和可靠的东西,试图在他多变的外表或者虚幻的借口当中寻找起支配作用的法则、或者有关未来生活的教训。机敏的评述、自以为是的谬论、徒劳的慰藉,这些比比皆是,除此之外,没有人愿意问一问:从所有这些矛盾和疑虑的雾瘴当中,究竟能知道什么?这也许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承受一种闻所未闻、但至高无上的事物,不愿意看到一种无法了解的力量。
转入天津卫之后,余则成迅速变化成为一个幽灵般的人物。不断产生的火花、分析能力、思维的活力、管理上的眼光、愿意妥协的直觉、非凡的意志力、以及说服语言的大师,这一切都综合在一个人的体内;他既能用政策事务的那种语言娴熟地说话,又能暗藏着另一种诗才的语言。他既非声称能够以文化的名义指导社会前进的人,也不是声称能够以专业知识的名义指导社会前进的人。他的才华并不走狭隘一途,而是与周围的世界产生完美的融合。这一点构成了他与谢若林之间的根本差异。
谢若林与晚秋之间的争吵,确切地说,现代版的“哲学与诗歌之间的争吵”,这对理解余则成有着典型意义。
晚秋能够十分细腻地体验到美,她渴望充满了困扰、危险和欢乐的生活,但她也因为没有能力体验自然及其必然性而产生强烈的惆怅和愤慨;她身上有寻找崇高的本能,但对世界的神秘魅力的领悟能力却极端有限。在她海阔天空的虚构中,时而点缀着优雅而纯洁的想象,时而穿插着满怀真情的低声细语,诗歌在她这里蜕变成为一种卢梭式的单纯的情感崇拜。
余则成对此种诗歌式的“忧伤”必然暗含极端的清醒和蔑视,不过他也明白,谢若林的哲学眼光因其过于纯粹和清醒,在指导世界或者个人方面不但必然面临失败的危险,甚至可能反过来伤害到世界和个人。
文化的瓦解往往并不使人对更为清醒和健康的哲学产生归属感,也不会让人皈依更为强有力的启示。
和霍布斯一样,余则成深知这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本能地愿意生活在睡梦当中。为了劝导晚秋,训诫诗歌,他必须首先发挥诗歌自身的力量,以掩盖谢若林式的哲学清醒
,迫使对手不得不就范,下面就是诗才语言与哲学论证的完美结合:
那儿有很多人像我一样,那是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你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可以选择的。你想想,晚秋,你站在一列雄壮的队伍里,迈着大步,高唱着战歌,去改变整个中国,那是什么气势?一个小小的余则成,就是路边的一个送行者,你看见了他,他看见了你,你们挥挥手就过去了,再往前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沮丧吗?无非就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留恋它就是一种高度近视!有时候看的远一点,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包括爱。
余则成必须杀死自己惟一可能的伙伴和盟友谢若林,这是多么地令人感到可悲!——
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够站在一个至高的共同点上,共同反对那种认为善的东西就是现时存在的东西的愚蠢见解
,和平与安逸、友谊与情感、财富与家庭生活、以及所有那些私人之间的博爱,无不是微不足道的善;这两个人比任何人都愿意更清楚地看到:
在遥远的将来,为达到真正的至善要经过多少血与火的洗礼,而现时的努力和牺牲必将不会带来一个政治上的黄金时代。这也许不是一种正确的心态,但却是一种正确的见解;即使不能说是正确的见解,至少也得说是强有力的见解。生活的真谛也许会呈现出多元的、自由的、暖乎乎的种种形态,但这是政治!政治的真谛必须在别的地方、在强有力的见解中寻找。
谢若林以令人吃惊的坚强意志力拒绝了这一来自神秘领域、或者至少具备神话特征的政治愿景,凭借对世界之崩坏以及人类情感和道德的内在腐朽性的见识,他以再终极不过的
伊壁鸠鲁式的哲学眼光
告诉余则成:
“两根金条放在一起,你说哪个高尚,哪个龌龊!”
余则成也以同样令人吃惊的意志力拒绝了这一终极的哲学世界,这并不是因为他不能领悟
这一
冰冷但健康的世界
,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追随命运,把生活转入统一的哲学原则的支配。
假如人们学会不加停顿地变幻角度,就能看到一副新奇的人物素描:余则成这个高明而清醒的行动中的
马基雅维利式的人文主义精英
,同时也是一个全神贯注、
低头阅读《荷马史诗》的孩子
,他完全被其中的语言和情节所征服,如同诗歌中的神灵那样:——
“坐在那里,对地上的事情漠不关心”。
那种种建立在伦理学原则上的美妙、轻松和乐观的宗教所发出的恢复道德权威的呼吁,对他不曾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在他身上,如同在
马基雅维利
身上一样,不曾产生过绝望;也正是因此,也如同
马基雅维利
一样,他身上天然地没有令许多寻找信仰的人们感到困惑的“信仰飞跃”的问题,这个燃烧的世界正是信仰的必要条件,而命运正是再充分不过的信仰对象。
传统、文化、哲学、情感、以及种种来自偏见的见解,他对这一切均有着非凡的免疫力,对他来说,这些东西不过是政客的通俗手册、庸众的精神食粮;他以一种类似罗马帝国时代共和派精英看待福音书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
余则成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而是一个成功的英雄;他既能全心
倾听海妖
的美妙歌声,又能同时做好
防备触礁
的各项工作;既能尝试探知全部世界指给他的大方向,又能保留
内心的全部秘密
,并坚守他的
本能
、才华以及对
善的直觉
判断。
借用一位过往政治家的评论,也许能够最为典型地刻画出,在
“我运”与“国运”不得不分道扬镳的时代
,一个像余则成这样的如此独特的马基雅维利式精英人物的荣誉意识:
“当国家已经衰落,他们在最后一息的自尊,如果确实没有增长的话,也将不会消退。他们对尊严的坚守恰如
塔西佗
在最后一息对
提比略
的爱的
掩饰一样。”
—Th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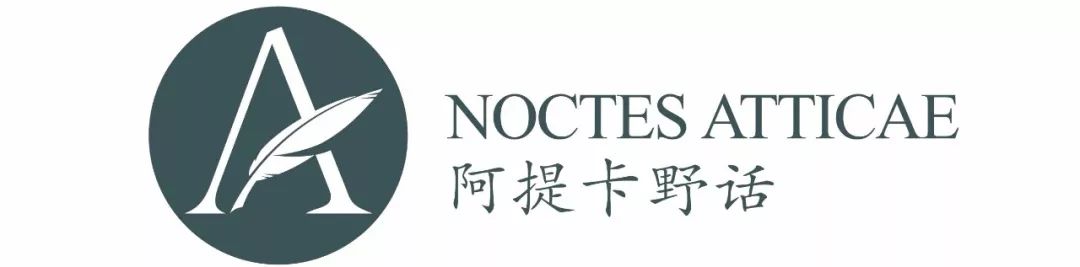

多山的伊庇鲁斯深处,幽暗的阿刻隆河畔,诸世代的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