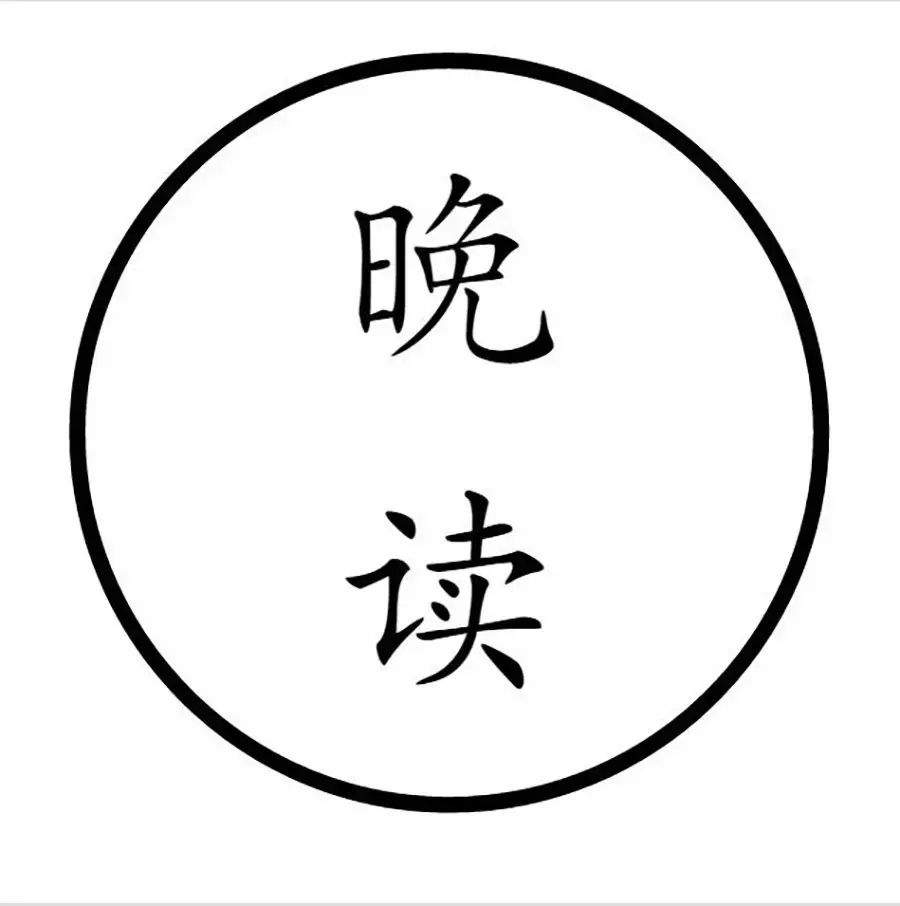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
Michael
SORKIN/
初译|
黎辰
/
校排|
PLUS
/
责编|
王家浩

迈克尔·索金
[Michael
SORKIN, 1948-2020]是一位建筑师、城市学者、教育家和批评家,纽约城市大学城市设计系主任。院外此前推送
《建筑与资本主义》对谈纪要
时曾经提及过他。遗憾的是,2020年索金因COVID-19引发的并发症去世。近五年来,国际建筑界有一些塔夫里之后最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相继去世,迈克尔·索金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包括我们曾经介绍过的
让-路易·柯恩
,
安东尼·维德勒
等。国内人文学界(甚至是建筑领域)未必知道索金,但是肯定会对他的同道、同事、好友,写过《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马歇尔·伯曼有所了解。
如果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这个时代对于建筑师的创作而言,可能未必是个好的时代。然而,幸或不幸,行动派的批判者在建筑界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这些新兴的建筑批评人对建筑业的审美、还有政治和社会诸多的弊端发起挑战。他们会利用更为广泛的媒介手段,而不只是建筑类的出版物,在这类批评出现之前,迈克尔·索金从1980年代起就已经在那么做了。
在公众心目中,索金作为批评家的形象远超过了他作为建筑师的形象。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向这位尖刻的纽约批评家学习:他在真理流行之前,就已经向权力道出了真相。
如果说迈克尔·索金从1980年代起不断地打开建筑批评的边界,那么反观国内从那个年代起,每过一个周期就会有人跳出来“批评”国内的建筑批评乏善可陈、隔靴搔痒、朽木枯株,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不过,这一周而复始持续到当下的对批评的“批评”都已经是老生常谈,差不多也可以成为我们所要批判的对象了。
我们并不期盼国内的环境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而是为了指出更为危险的问题:这种所谓的外部理由恰恰已经抽空了人们对建筑批评之所是这一内核本身的批判能力。如果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建筑批评是太少还是太多,是正确还是错误,而是大部分人想要的真的是建筑批评吗?为什么总是有人要求批评者给出所谓“正确的批评”?或者每一个这样的周期来临,对建筑批评应当如何在自身的语境中发生并没有从认识上做出改变,也根本不是为了
向权力道出真相
,甚至恰恰相反,只是为了服务于权力,或者成为新的权力继续扯谎遮掩?等等等等,那又会怎样?
如果真的如塔夫里在“
只有历史,没有批评
”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样一个时代更深层次的批评就只能是彻底的历史了,那么人们还需要“建筑杂志上靠那些建筑师们,靠那些蹩脚的历史学家搞出来的“建筑批评么?或者针对社会中的建造活动本身及其外延,人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批评?或许,我们能从迈克尔·索金的经历中寻到一些新的进路。

本次推送的短评选自迈克尔·索金2018年由verso出版的批评文集,这本书被誉为是“一位激进的建筑师审视当代城市不断变化的命运”。在这部文集中,
索金指责政府官员、开发商、“民间 ”组织和其他大财团的英雄们,正是他们让索金心爱的纽约变成了一座高楼林立、不平等日益加剧的城市。他不仅揭示了塑造当今城市的各种形式和做法——从分区规划和政治交易到建筑设计的细枝末节——而且还积极倡导另一种城市,从街道到人的尺度上重新构想的城市,一种可持续、公正、充实的邻里社区和公共空间的家园。
值得一提的是,索金在书中描写了观察和居住在城市和建筑的乐趣和技巧,以便更好地理解城市和建筑,并更快乐地置身其中。索金从不羞于指名道姓。他痛斥平庸的设计,痛斥“明星建筑师”对贪婪和特权的顺从。他充满活力地以专业知识、尊重和带刺的诙谐向学生、专业人士和城市居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没有资本主义的建筑”
还曾作为后记收录在2013年由佩吉·迪默编著的
《建筑与资本主义:1845年至今》
。
我们不妨把它
看作是对“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套用,而其中的问题式直指的是当前的“明星建筑师”体系。反观国内建筑界的情况,仍有一批人对此有所期盼,可能是认为如果没有过上这波瘾,就不足以证明“中国建筑”已经跻身于国际的版图。然而正如笔者很早前就在其他地方多次提到,不仅所谓“中国的”建筑这一无意识反应甚是可疑,而且所谓的全球明星建筑师体系在这个时代也只是无处发送的“末班车”了。看看近来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表现,不言自明的是这种让“中国”搭上“末班车”的强烈怨念不只是幻像,而且更是痴人说梦。

Michael SORKIN|1948-2020
What Goes up: The Right and Wrongs to th
e City
|
2018


迈克尔·索金
|
Michael SORKIN

去年,“占领华尔街”把祖科蒂公园挤得满满的,这场运动试想着一种没有资本主义的、甚至是无视资本主义的建筑,那是一种在体系之外的可能性。事实证明这很困难。
这座叛乱的小城市,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全面地颠覆了现实中的城市,同时它还充当了一个倒置过来的自由贸易特区,为非商品化的言论提供场地,但最终它凉凉了,条子来了。
无论多么的短暂,
这个社群
都是无法磨灭的,它传达的信息是:你选择攻击这一体系的方法,正是你如何理解这一体系的产物。占领运动一下子就精确地理解了这一体系,同时这种理解也是分散的。
不过,随着口号演变成“我们是99%”,对资本的批判就变得清晰明了起来,斗争也被量化,并与最原初的政治纽带紧密相连,那就是:分配。
所有的建筑都在分配:大众、空间、材料、特许权、使用权、意义、居所、权利。建筑和资本之间不可避免的连结是其核心的令人着迷之处,同时也是它能被如此有效和丰富地解读的原因之一。
环绕在祖科蒂公园周围虚有其表的建筑物的可读性,再加上为确保华尔街的特权不受到冲击而部署的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警治技术,这只是建筑坚持明确自己角色的第无数个例子。
大体说来,建筑只是助长了资本不平等的透明度而已。哪怕是最坚定的建筑革命者,也很少会做超出通货变现的事儿,拿物质去换象征。
怎么办?没有了资本主义,建筑还能生存吗?可能的出路有哪些?

animal houses collages
|
1989


1.
老套的庸俗做法,是
把建筑简单地看作经济基础反映上层建筑,这已经毫无实际意义了。人类的协作能力超过了我们的发明能力,而我们还迷恋发明,想买张票就可以跑路。
建筑的形式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成为危险的力量,除非它不在了,或者它暴力的破坏,才有可能威胁到所有人。各种国家和非国家的斗争者,包括那些在世贸遗址
(ground zero)
街对面创建“占领”运动的人在内,都没有丢掉这一经验教训。然而,和往常一样,问题是:谁会被晾在一边?
鉴赏力并不完全是敌人,但它的滥交可能是,尤其经不住想要往崇高方向去的引诱。不能只是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任何带口味的文化,甚或可以解构它,就以为我们必须认可它。邪性的符号学与“建筑图形标准”中的符号学并不相同,后者包含着抵抗的核心谓项,在这里要抵抗的是重力。
2.
或者,占领运动实际上可以沿着自己暗含的高速路前行,与其在那些由房地产剩下来的被指定为所谓“公共”的空间里安营扎寨,不如搬到那些交易室里去,在那里过日子。
为什么要默许僵化的生产关系如此强有力地在由市场打造的城市中刻下的条条框框?
如果没有要求重新分配的勇气,进步的政治也就无从谈起。
无论你怎么在
资本的历史形态中
解析资本,不管你称现在是晚期资本、全球资本还是贝恩资本的时代,这种描述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所有的经济都是分配的引擎,我们通过取用和分享的伦理,来审查它们的道德是否适当。
公园大道的公寓或阿斯彭公寓的错处不在于皇冠的造型或墙裙;而在于它们所体现和代表的空间、便利和特权的不平等扩张。这点显而易见,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不甚明了。
在《住房问题》(1872年)的经典阐述中,恩格斯提出解决方案不是在城市破败的尽头给工人们简陋的露台提供微薄的补偿,而是搬进中央公园西区的剩余空间,那才是相当经济的办法。
3.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弃绝之路,可持续的、甘地式的紧缩政策,简单地拒绝与消费打交道,不再被当成资本的斯特拉斯堡鹅。事实上,在美国肥胖症指数级增长,有可能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像一栋房子那么大的建筑。
我们以前当然也沿着这条路走过,但还有那么些人,阿米什人、无政府主义者和阿什拉姆居住者,他们制定了这些替代方案,或多或少选择了退出。
还有地方主义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它能够对跨国公司打着“随心所欲”旗号的收买行为做出反击的话。
在我们“启蒙运动”的现代化身中,政治起源于某种自然状态,无论是卑鄙野蛮的还是天堂般的,在那里,每个人都从他们资本主义之前的原始小屋中走了出来。
这个无处不在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森佩尔的、洛吉耶的,还是欧洲殖民扩张大时代探险家们无畏的素描本中记录下来的人物形象,都是这个历史主义和线性的伟大时代的一部分,对于某些人既定的结论而言,那是必要的起源点,这绝非巧合。
这是一种不断重复的行为,就像在二十世纪有关最低限度生存的论述一样,现代性的原始小屋,以其特有的分配和建构的简洁性确立了原点和零度。难不成回到树上去?

weed
|
Arizona|
1993


4.
我们不妨真正地去研究一下非正式性的本质,它长期地处于与法律谈判和反击的状态之中,是永久抵抗的媒介。
最近的一些思考表明,城市领域中的非正式运作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所谓的"例外状态",边缘人群
在这种状态下
用
他们可替代的空间方法,在涓涓
细流中蹭上一滴。
相反,
非正式性
就像
阿南雅·罗伊[
Ananya Roy]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习语”,在印度或巴西等地的各个层面都行之有效的,那是一种
不断重塑建设和权利的地景的规划形式,
利用法律解释、规避、被动和暴力。
一方面,这种作为持续争论主体的空间可控性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充满期许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中,被剥夺权利的人可以不断地为他们的愿望和权利找到战略开口,在这种局面中,需求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层面上被模拟出来,从边缘化的地形中挣脱出来,并被带到城镇的中心。
另一方面,这种运作领域的内在不安全感也为“创造性破坏”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空间,因为强权通过诡诈的法理或者彻底的驱逐,攫取了他们希望注入剩余价值的领土。
5.
我们为了自己的权利主张另一种模式,城市权,这是当今最好的主轴线。
如果这意味着,首先,我们要求财产在我们出入和集会的要求面前往后退,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可操作性,一个占领的空间。
如果这意味着,资本重新配置自身,以适应我们对其他生活方式、其他关系、其他城市、其他幻想的梦想,我们就会打断并迷惑资本的前途,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启动历史的引擎,并顺势而为。
乌托邦的意义总是在于它的短暂性:但你可以从各种梦想中学到很多。
6.
城市中是否有一种叛逆的风格,同化、遭遇、存在。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城市围绕着各种感知装置旋转,这些感知装置让我们热爱它、消费它、了解它。
我们是游荡者,在林荫大道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我们是购物者,从我们的私人空间中解放出来,毫无防备地与奇观和其他事物打成一片。我们是司机,用快速的连贯视角观察那个被激进地拉长了的空间。我们是电影制作人,用我们重组合成之术,创造出既存在又从未存在过的空间。我们是漂移论者,带着轻描淡写的刻意超然,尽力体验一种即兴的真实,一种无意识的图表,那种几乎没有事故的空间。喝酒嗑药
。
被绑架。
被阵雨浇头。
有没有一种感知的工具能把资本主义城市变成它的另一面,把它翻转过来,成为真正的异轨?
让我们继续寻找,偶遇陌生人,上演随机事件。
成功总是转瞬即逝的,尝试就是结果,但失败总是一目了然的:
如果横穿城镇的每条路线,最终都把你带去麦当劳,那么这玩意铁定是出问题了。

a habitable levee|
New York
|
2013


7.
好吧,那么,我们真地要为我们的梦想家喝彩了。当前的不可能性提醒我们如何定义这一类愿景。当然,有必要对不可能性的条件持批判态度,并弄清楚限制的必要性。
不包括我们身体的那种愿景不算建筑,要排除在外。我们要通过捍卫自己肉身的建设来对抗资本的大计划。
把居住和服饰这两边给联系在一起,那肯定是个阴谋,而且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让大写的“人”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广告宣传和名人效应来掩盖我们自己,不要在我们的头盖骨上镶金带钻。
我们也不应该屈服于我们自己这一方沉闷的家长式理论,这种理论常常是在啜饮桑塞尔酒的间歇时产生的,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偶然而已,简单地认为所有的偶像破坏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的另一种策略。如果你还是坚持要这么说,那就称之为“否定”吧。
我们要冒一定的风险,跨过反讽或愤世嫉俗的桥梁:谁想要一场毫无乐趣的革命?
为什么要以Archigram为代价高抬Archizoom的价值?为什么宁愿沉默而非欢笑?想要一锤定音够呛,死掉一千个笑话有戏。
8.
我们等待着那些个被吹嘘的具有创造性破坏的矛盾,来证明它实际上是多么缺乏创造性。如果这个体系诱惑并抛弃了它的每一个主体,让我们每个人都遭受抵押贷款的奴役,让每栋房子都处于水下,每个人都不得不往更高的地方搬,那就意味着
“
去他妈的
”
。
马克思梦到的正是这种崩溃。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减去时,建筑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一探究竟!
社会主义在宿舍里?
在临时屋?
车间?
邻里?
城镇?
城市?
国家?
星球?
为了找出答案,我们必须继续面对自由主义所特有的困境:
要多少个国家才算够?
我很清楚一点:
一个福利国家胜过一个战争国家。
9.
我们来到非实体化的共产主义,将我们全部的容量下载到了硅或其后继者上,成为纯粹的心灵,打败可触的财产。好吧,也许扯得太远了:存在于脑中的建筑只是个比方。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new york city (steady) state
|
2010


▶
版权归
作者-译者所有,译
者
已授权发布
。
文章来源
|
What
Goes Up: The Right and Wrongs to the City
|2018年出版
未完待续

▶ 目
录
01.
Jane's Spectacles
02.
New York Triptych
03.
A Dozen Urgent Suggestions for the Village
04.
NYU's Tipping Point
05.
Occupying wall street
06.
The Sidewalks of New York
07.
Learning the Hard Way
08.
Sandy
09.
Ada Louise Huxtable
10. Ground
Zero Sum
11.
Marshall Berman 1940-2013
12.
The Fungibility of Air
13.
Big MoMA's House
14. What's
behind the Poor Door
15
.
Ups and Downs
16.
Little Boxes
17.
Business as Usual
18.
Big and Bigger
19.
Another City
20.
Sow's Ears
21.
Lost at sea
22.
Getting Together
23.
The Cathedral at Ground Zero
24.
A New New York, the Same Old Story
25.
Manhattan Transfer
26.
Preserving People
27.
Need to know?
28. A Reminiscence of Hollin Hills
29.
Back to the Burbs
30.
Architecture without Capitalism
31.
Informal Formality
32.
The Trials of Rafi Segal
33.
Krier
♡
Speer
34.
Rumble in the Urban Jungle
35.
Working Drawings
36.
Cells Out!
37.
Presidents and Libraries
38. Critical
Measure
39.
Two Hundred Fifty Things an Architect Should Know
41. Civilian
Objects
42.
Clear Light
43.
The Architect as Worker
44.
Travel with ZaHa
45.
Pinkwashing Zion Square
46.
Burden of Gilt
47.
Architecture against Trump
48.
The City after the Autonomob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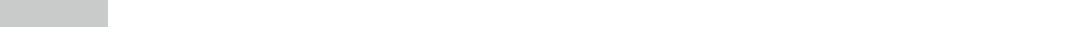

▶
院外
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
BAU学社
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
星丛共通体
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
回声·EG
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
批评·家
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
BLOOM绽
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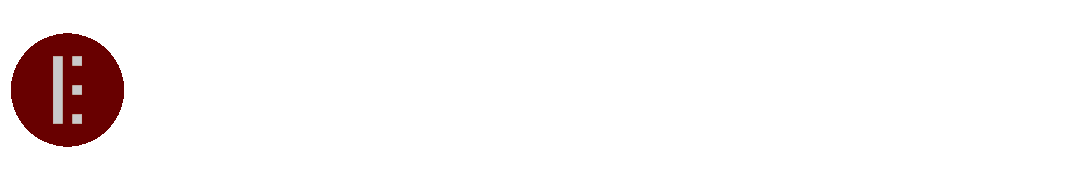

▶
院外计划
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
汇集、
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
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
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这一目标。

▶
星丛共通体
/
回声·EG
|
专题 ▶
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
|
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
|
包豪斯十四年:先锋派的临界点
|
共读 ▷
启蒙辩证法
|
走向新宣言
|
美学理论
|
装饰与罪恶
|
艺术与生产
|
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
|
计划与乌托邦
|
空间的生产
|
帝国与传播
|
理解
媒介
|
地堡考古学
|译-写 ▷
瓦尔堡
|
阿多诺
|
最后的马克思
|
塔夫里
|
后革命与世界体系
|
列斐伏尔
|
现代性与日常生活
|
麦克卢汉
|
生产方式对信息方式
|
居伊·德波
|
排场社会与地理主体
|
技术网络与人器纪
|
朗西埃
|
山寨现代性
|
画讲-图说 ▶
建筑物与像
|
论坛
▶
空间生命政治
|
美学与生命政治
|
美学与政治
|
媒介批判
|
都市魅惑与图像
|
建筑
批判
文献阅读
|
城市危机与空间政治
|
▶
批评·家
/
BLOOM绽|
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