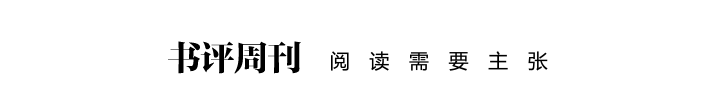
说到武汉,你会想到什么?热干面,或许是你的第一印象。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中部城市,在2013年武汉的铁路客运量就已经超越了北京、广州,居大中华区第一。它还是国内院线数量最多的城市,中国拥有高校数量最多的城市。以多少带着黑色幽默感的问题开场,是希望引向一个严肃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中国城市,国人对它的地方文化、城市气质知多少?
每个城市,在理想情况下,都可能拥有出落于其历史、文化沉淀的独特气质,比如罗马、比如伦敦,然而对于大步奔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多数中国城市而言,这还是一个奢侈品。多数中国城市在城市气质、文化及其对外输出上,还停留在“重庆小面”(在鸡公煲衰落之后)这种聚焦于感官上的层次。
但是,我们应该、也有能力做出不一样的“城市文化名片”。就以武汉为例,回想曾背诵过的历史课本中,武昌起义和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开埠条款,我们曾离汉口、武昌的历史如此亲近,它承载的地方文化曾经是那样丰富、鲜活。
但这些城市的地方文化及文化记忆,在人们的记忆中还留存多少?当北上广这类一线城市占据着国内主流的文化资源,当“大武汉”作为一座现代城市的口号已坚定,武汉要如何甄选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恰当的地方文化资源另辟新路,使之与现代都市文化相融合、形成武汉当代的文化新气质?进而形成武汉的新城市文化、制造新一代市民的公共文化记忆?

《知音号》于2017年4月26日在武汉开演。与传统戏剧表现方式不同,《知音号》不分观众区和表演区,每一个角落都发生过、发生着或即将发生不可预知的故事,而观众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历史变迁纵有沧桑痕迹,而江水味仍是这个城市挥之不去的绵长记忆。由跨界艺术家樊跃导演的《知音号》——一场“漂移式多维体验剧”,正在等待旅客登船。来,跟随本文作者开始这场关于城市历史记忆的新旧碰撞之旅吧。

撰文 | 孔雪
什么是“漂移式多维体验剧”?
《知音号》导演樊跃:我取名字是很大胆的,“漂移”船在行在漂移,城市记忆博物馆的漂移,演出的漂移,第二个是互联网在空中漂移,观众通过互联网分享、相遇;维度,观众和演员、观众和观众的关系每天都在变化,每天产生新的搭建方式、感触点。我们是什么,谁也定义不了,但不重要。但我做到多维体验,让观众从不同的维度围观、探寻,看完演出,戏剧还在发酵、演出还在发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在发生,大家用自己生活的经历来与这台演出相遇、遇见、了解、知己,这简直太奇妙了。
“知音号”之旅
“没有小太阳的年代,
你爷爷的爷爷冬天这么过”
面前是一艘根据上世纪30年代游轮复制的“知音号”。那个时候武汉——准确地说,老汉口——是什么样子?

晚清时期的汉口。
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使英、俄、法、德、日、比利时等西方列强先后涌入汉口开埠,12个外国领事馆和近30家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使殖民期的汉口呈现出畸形繁荣景象。当时,被誉为“中国芝加哥”的这座国际化都市别有一番追新求异的城市气质。这对近代武汉的城市文化有着鲜明的影响。就在30年代,刚迁入珞珈山不久的国立武汉大学打破女大学生游泳的禁令,在中国首开女大学生游泳课,一时轰动全国。
历史随江水逝去。1949年后,更多的人知道的是经历行政规划之后的新“武汉”,对汉口、汉阳、武昌的过往渐渐知之甚少。其实中国很多城市都经历过近代行政规划对城市名称和区域归属的调整,这多少会影响到地方文化对内、对外的记忆与传承,甚至在一家三四代人之间就可能存在对于同一座城市认知的差异。登船前,我遇到一家祖孙三代。外婆在1949年出生,孙子约7、8岁。对于外婆而言,这里是父辈口中的“老汉口”,而对于孙子而言,这是武汉新出现的一艘有趣的船。
船上打着三万多颗上世纪30年代样式的铆钉,导演樊跃为营造老汉口氛围精益求精。身着旗袍、长袍的青年男女演员散在四层船舱的走廊上,有人在送心爱的人登船,因太过不舍,索性连船也不想下了;有名伶在给认出她的人们签字,她为何上船、又去向哪里?108个演员的故事缓缓地各自抛出最初的情节。
以一位“知音号”旅客的身份登船后,旅程正式开始。一楼的开场舞中,故事又一次抛出线索。一旦深入其中,我就感受到这次观演的不同:舞台与观众座位并非泾渭分明,我放佛真的在上世纪30年代老汉口的歌舞厅,化身为和演员一样的其中一员。上世纪30年代的我,还是选择坐在暗处,还是喜欢走神,于是起身、走动,翻翻一旁书架上的《良友》杂志。而舞池中央的人们,无论是特意体面打扮的苗条女郎还是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任何一个船上的旅客都有可能被邀请进入舞池,和“演员”共舞——其实谁说得清楚此刻谁是主,谁是客呢?

等待在“知音号”外的观众。
身后大幕倏地拉开,老汉口的一个酒吧出现。酒保幽幽地又引出几个人物更具体的故事。一位从未走下“知音号”的男乘客,每天会打一个电话寻找虹表姐,寻人不得,已如此西西弗式地坚持多年。直到那一刻,对方忽然回话,酒吧场景就此戛然而止。以后会发生什么?灯光暗下来的那刻,当晚350位观众,350个故事在发酵。
二楼,10个房间,10个独立的故事。我进入的房间,主人是沈祝三。这个在汉口创办了汉协盛营造厂的商人曾承建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1931年武汉大水导致物价上涨,加之在估算中漏估开山筑路费用,在可能的巨额亏空面前,沈祝三不惜负债坚守合同。如今,武汉大学建筑已成为中国近代建筑走向成熟期的经典代表,汉协盛却在这段历史中倒下。1941年,还完了债的沈祝三一身清白地,在汉口去世了。
一个青年演员略带生涩地诉说着这段历史,他白皙的脸上看不到沈祝三的沧桑,但近距离地相对时,人很难不被这个房间里的这段故事所感动。三楼,房间的主人则变成了每一个旅客、老信纸、旧怀表和行李箱都是寻找一段故事的线索。我猜想,我选择走入的房间,大概曾住过一位青年人,他在这里给叔叔写信,诉说着对前途的迷茫,床头上还摆着一本让他忧虑不已的代数课本。一股遥远而清新的少年愁滋味。
故事会牵着人往四楼甲板上走,此时已经没有情节,只有一个主题,“知音”,旅客在这里自己创造各种可能。来说说我找到的“知音”——我认识了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两个人都并不出生在武汉,但却在武汉相遇、生子、变老至发白。我还看到在四楼的城市记忆博物馆里有来自武汉市民的“投稿”:比如老汉口的一张汇票,那是一张来自全世界最知名的戏剧之地百老汇的“民生公司汇票”,在半个多世纪后出现在“知音号”上;还有一个铜制烘笼,投稿人在一旁写“没有小太阳的年代,你爷爷的爷爷冬天这么过”。

《知音号》剧照。
想到登船之前遇到的那对祖孙,或许奶奶可以站在这里告诉孙子,“在没有空调的年代,奶奶的奶奶冬天这么过”。地方文化记忆在几代人之间的对话,青年一代人对父辈生活的了解,由此实现。这是这一次旅程中最让我感动的“相遇”,和一个安静地睡在这艘船上的老烘笼。
其他旅客或许会对着另一张旧婚书着迷,或许走向开阔的甲板,等候这个开放空间里他可能遇到的人,在“知音号”缓缓靠岸之前。
城市化之问
新旧文化资源如何相遇、
碰撞出当代城市的精气神?
一去一回,从“知音号”到码头的两道栈桥在这场老汉口穿越之旅中制造了恰当和重要的仪式感。如果说走向老汉口“知音号”的栈桥意味着观众对一场相遇的有备而来,那么走向码头的栈桥则把更多问题抛给了当代的“大武汉”,以及每一个对城市发展有所探索、思考的人。
《城市与城市文化》
作者:德波拉·史蒂文森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
城市景象在电影、文学、艺术和流行文本中的“再现”,即一些特定的城市空间——包括内城、城市滨水区是否影响了我们的城市观念呢?
一个城市的新旧文化资源才能相遇,碰撞出一座当代城市的精气神?我很好奇,在未来几年中,“知音号”将如何以艺术的方式影响武汉的市民文化,如何以一个艺术空间去参与构建城市的公共空间?它是否有可能促进长江沿线几个重要的港口城市的相遇,促成武汉甚至是一条江上几个城市关于一江水、几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
正如樊跃早已设计好的,今年,“知音号”会造访上海—把一个空间开过去,带着一个命题开过去。未来,南京、重庆都可能参与这种相遇。“莎士比亚就是莎士比亚”,我问樊跃是否会担心基于老汉口历史文化的《知音号》对其他城市的吸引力,樊跃回答,“怎么解释呢?我们设置的问题其实适用于全人类的,人和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就是知音,我们为什么不再次相遇呢?”

《城市之间》节目照。
这让我回想起十多年前,央视从法国引进的一个城市竞技游戏类综艺节目——《城市之间》。它每期邀请国内两个城市,以体育游戏竞技的方式增进对话和了解,在活跃、幽默的氛围中展现两座不同城市的文化风貌。对照当下各大卫视就明星真人秀打得火热的现状,这种有益于国内城市对话、展现城市文化和市民文化的节目反而消失,不得不说是国内城市文化发展落后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十年后,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在各项发展指标排名下陆续各自铺开发展蓝图、城市面目日益趋同的时候,《知音号》这样的艺术项目大有填补空白的空间。所谓“空白”,正是国内城市文化之间的交流、城市相通文化记忆的构建层面的缺失。
相比城际交流和一江水的连同记忆,“知音号”能否在武汉成长成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城市空间,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在未来几年中,它需要面临很多挑战,最核心的问题是处理好这个空间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作为艺术家,樊跃有自己的期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武汉大学的毕业典礼放到这里?它可以成为这个城市里所有人的‘知音号’”。
是啊,为什么不让它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呢?随着国内近十几年来公共生活的式微,除了KTV、公园、文化广场、电影院之外,中国大多数城市中并不存在活跃且开放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已在一二线城市扩撒、正奔向三线城市的星巴克或KFC正在成为青年一代消遣、聚会的主流地点,基于地方文化设计出的新文创空间极少融入青年一代的日常生活。一种担忧已被证实,即国内大多数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越发趋同,而地方文化的存续、传承、开发与创新的经验案例并不多。
《公共人的衰落》
作者:理查德·桑内特
译者:李继宏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1月
孤独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后果,致令个人向私人生活靠拢,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公共人的衰落。在城市,从建筑设计到道路安排,公共生活都在被拷问。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很期待武汉艺术类院校的毕业演出、武大或华师大等高校毕业典礼、地方文化相关新作品的发布会、老汉口照片展览等文创活动都可以和‘知音号’相遇,促使它成长为武汉的公共文化空间。在这里,老汉口的文化记忆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注入青年一代的生活中,促使出这个时代武汉人新的文化记忆。
这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愿景,因为在任何一个当代大城市中营造一个与地方文化、市民文化紧密相关的公共文化空间,既需要清晰坚定的理念,也需要至少三五年的打磨才能见到结果。以北京为例,前门大街区域从明朝就开始陆续发展出小集市,清朝至民国日渐繁荣,是北京内外城交界之处有丰富地方文化沉淀的地点。但今天当你站在2008年前后因奥运大规模改造的前门大街时,能看到什么?
左手边有杜莎夫人蜡像馆,右手边有星巴克,再往前,老北京饮食老品牌之中夹杂着miniso等快消品牌,更多映入眼帘的则是攒动的人头与杂乱的商铺。我们很难称其为气质鲜明、格调稳定的城市文化空间。相比之下,距离前门大街不远的杨梅竹斜街,在改造之初就请到了日本中生代设计师原研哉策划。在近四五年的街区改造过程中,腾空的老宅院多交由艺术家、设计师进行空间改造。现在,这条在民国时期曾有七家书局、王回回狗皮膏等老字号驻扎的老街,也被注入了鲜活、鲜明的新气质。
在当代中国城市中,杨梅竹斜街这样与地方文化关联紧密的新造文化空间是少数,很多城市还停留在争夺一个地方传说的“真正”发源地的阶段。即便有一个新生的这一类型的空间,我们也需要观察在浮躁的商业社会中,它们是否能在必要的商业盈利与本质的文化艺术气质中摸索到平衡。同时,防止泛滥的复制。所以,对于武汉的《知音号》,我们愿意给出谨慎的期待,希望它成为樊跃所期待的那样,“我们要做新的事情,让它们成为经典”。
如果说,在艺术领域,《知音号》是艺术家敏感地先见和先行,那么换一种视角,它其实回应着城市发展中长期以来我们该去探索的问题。城市大步向前奔跑,它的文化、历史、生活记忆将安置在何处?这是常提常新的问题。我们相信,此时以《知音号》再次抛出这个问题,仍是必要且及时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作者:孔雪;编辑:阿东。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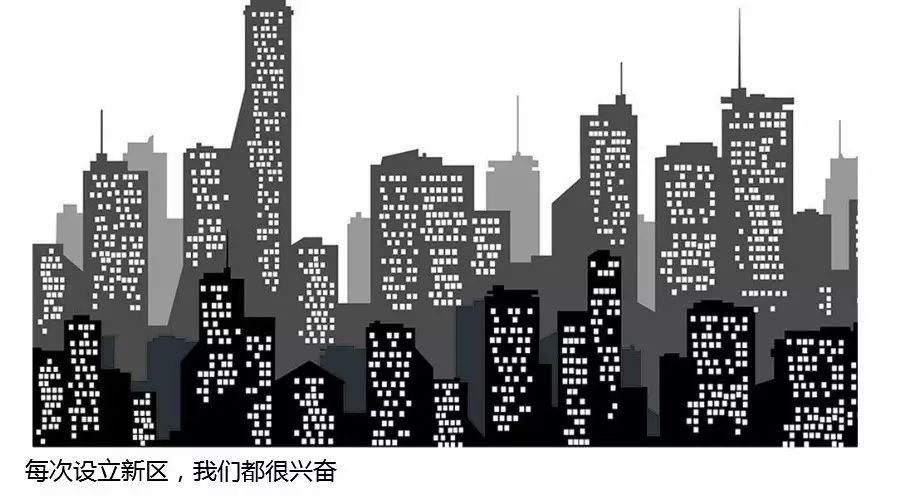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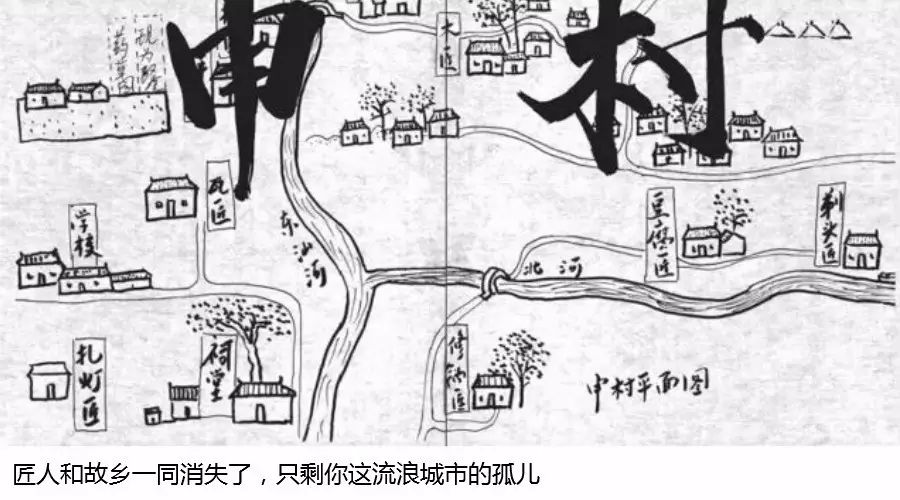
▼
直接点击 关键词 查看以往的精彩~

扫描图中二维码
或者点击“阅读原文”报名“有时”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