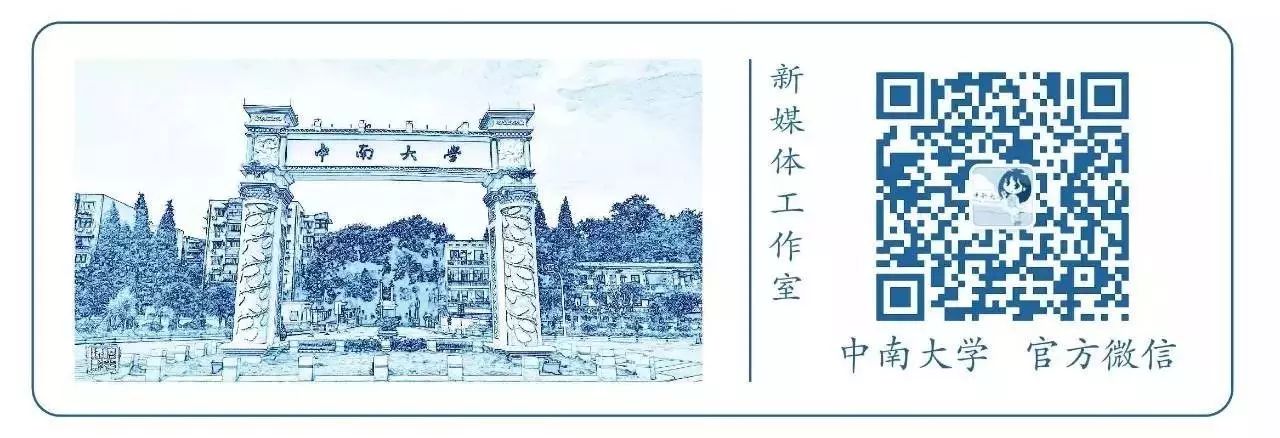到境外走一走、看一看,曾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如今,它不再是官员、企业家、富豪的“奢侈品”,早已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据统计部门发布,仅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国内出境游人数就达600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游客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追逐、争取的对象。
记得“文革”时,若谁家有亲戚在境外,都担心因“海外关系”而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往往讳莫如深。尽管如此,“外面的风光如何”,仍然是当年许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问。
当年,我的好几位中学校友都选择嫁给了“国际海员”。每当她们拿出一些来自国外的罐头之类用品时,总会引来不少人好奇和羡慕的眼神。改革开放初期,又有一些女同学找到了境外的对象,一去不复返。
我第一次出境是在1991年的夏天,目的地是香港。
那年,因就读某高校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班,我得以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交流学习一个月时间。那时的香港,还未回归祖国的怀抱。为了这次香港之行,班里不少同学早早地开始了精心准备。有的托人寻找香港本地亲戚熟人,有的悄悄地去自由市场上换港币(当时还没有开放国际货币兑换),更有甚者,一位中层干部还千辛万苦向单位借了一台摄像机。那个时候,国内也只有电视台才有这又重又笨的大家伙。对我而言,这就算是首次出境了,既兴奋又好奇。
最搞笑的是,怕到香港显得“土气”,我还特意上街买了一件时髦的“国际名牌”T恤——“梦特娇”。同学们一问我价格就笑翻了,说哪有这么便宜的名牌。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假洋鬼子”,只觉得穿着不透气。

我们是从深圳罗湖口岸入境的。当时香港还在英方统治下,海关多是“老外”把持着。我小心翼翼地递上护照,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表情。毕竟是第一次出境,心里难免有些紧张,生怕出什么岔子。一走进香港的联检大厅,我才体会到冰火两重天的真正含义。深圳那边暑气逼人、声音嘈杂不已;这边的空调送来丝丝凉意,人们轻言细语、秩序井然。一出关,我们随即登上了舒适、安静、快捷的九广铁路列车,车子还未到沙田(香港中文大学所在车站),我们入关时忙碌的一身汗水早已收干。
中文大学坐落在新界的半山腰,蜿蜒的山路贯穿整个校园,连通各个学院和运动场馆。登高望远,山峦翠绿,风景宜人。
因是暑期,我们便住在休假学生的宿舍里。培训课程一半是由老师授课,另一半则是参观考察香港的市政、商业和工厂。
我们参观的第一个企业是位于新界大埔工业区的嘉士伯啤酒厂。走进工厂,宛若走进了一家五星级宾馆的大堂,有沙发、吧台,还有免费招待的啤酒和花生(如今湖南的青岛、华润啤酒厂也是如此),这令我们一行人大开眼界、直呼新鲜。我这才知晓,企业除了生产产品,还要有企业文化、企业品牌。
后来,我们又参观了位于沙田的马会俱乐部、中环的股票交易所,以及港岛的太古新城。令我惊讶的是,商场里居然还有用天然冰制成的溜冰场,穿着各式运动服装的年轻人竞相表演,给商场带来了人气和活力。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们只能在水磨石的地面上溜旱冰。
对于我们这帮“穷学生”来说,最吸引我们的,莫过于地处九龙旺角的“男人街”“女人街”。霓虹闪烁的夜晚、繁华拥挤的街道、“灵活机动”的商铺,各式新款服装、箱包、电子产品琳琅满目,让旺角散发出独特魅力,迎接着接踵而至的购物旅客。夜晚,因这里而变得漫长。香港由此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这里的货虽不正宗,但相对便宜,仿真度很高。到香港一趟,总得给家人、朋友买些伴手礼,贵的买不起,我们便只能在这里淘些“价廉物美”的小商品。现在想来,北京的秀水街、上海的华亭路服装市场,与当年的旺角还颇有些相似。
深水埗是香港最老且最贫穷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我竟遇见了一位当年在农场的同事。记得当年,我看她十分娇小、弱不禁风,便安排她在连队的食堂干活。八十年代初,她离开农场嫁给了一位香港海员,此后便再无音讯。故人相见,她高兴万分,一定让我去家里做客。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来到了她的住所。
那是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屋,一幢大楼被“切割”成几百个“鸽子笼”一般的房间,每户大约20至30平方米左右,一个卧室一个小厅,她就生活于此。
一个铁架双人床,占据了半个卧室;一台窗式空调、一台老旧电视、一台锈迹斑驳的冰箱便是家中全部的电器。此时的她,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谈及过去在农场的生活,她对现状似乎已感到很满足。知道我来,她在附近的茶楼订了座,邀我和她的儿子们一起去喝早茶。我原本以为就是喝喝茶而已,谁知这一喝便是早餐连着午餐,桌上只有凤爪、叉烧等几个小吃。到了下午,我实在坐不住了,便起身告辞。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思忖,这应该就是香港的底层生活了。当我们漫步于风景优美的太平山顶时,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豪宅掩映其中,奔驰、劳斯莱斯等豪车不时擦身而过;放眼望去,鳞次栉比的现代摩天大楼填满了整个港岛,维多利亚海湾碧水蓝天、白帆点点。而农场同事居住的“鸽子笼”,成为了香港繁华背后的另一面。天上人间、两个世界。她因离开农场而庆幸,殊不知,又进入了新的社会底层。想到此,我不禁感到惆怅。
在去香港前,我设法打听到一位朋友。他曾是我母校的团委书记,儒雅而机敏,几年前因继承遗产来到了香港。我俩沿着海边散步时,他落寞地告诉我,到了香港后,遗产已被叔伯们分割完毕,第一个星期还接纳了他,第二个星期为他在某企业找了份差事后便撒手不管了。
他望着对岸的万家灯火感叹:这就是东方明珠,在这群星璀璨的灯火中,不知何时有一盏是属于我的。
他的话让我刻骨铭心。
离开香港的前一夜,我冒着蒙蒙细雨,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走上拥挤的街头,最终来到了九龙火车站旧址。古老的钟楼见证着香港百年的沧桑巨变。望着对岸繁花似锦的幢幢高楼,我在台阶上一坐便是整整两个小时,脑海中不断地盘旋一个问题:
同是中国的领土,同是华人的双手,为何香港如此繁荣,而内地此时还如此落后,难道真的是人们所讲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吗?一个连淡水也要靠内地供应的小小渔村,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它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
老实说,那个晚上,我没有得出结论。我只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如今,离我第一次出境已经25年了,中国在这期间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事实,早已回答了我那晚的困惑。改革、开放、心无旁骛发展经济,这就是我们成功的法宝、制胜的“关键一招”。
小平同志曾说,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实践充分证明,小平同志的预言是正确的。我无比佩服和崇敬这位开创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世纪伟人。
摄影 | 郑晓光 鲁凯 胡超群
编辑 | 罗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