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曾经在她的作品里描述乡下多女儿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一家有几个女儿,出嫁后便很难常见面,她们需要看着自己的孩子,守着自己的家,只有在唱野台子戏的秋天,姐妹们才会在从小长到大的娘家重新相遇。
但姐妹终究是姐妹,即便是在通讯不发达的以前一年只见一次,有时候甚至只会红着脸却无话可说,那对彼此的牵挂和关心怕早已融化在血液里,千言万语浓缩在见面时给父母和姐妹们带的礼物里。
在安徽南陵的一个小山村,也有这样一个多女儿的家庭,姐妹一共五个,这搁以前也是很少见的,这五姐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从老四沈书枝的这本《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书中或许可以大概了解。
《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这本书主要记录了五姐妹从小到大的生活,也是家庭生活记忆的回溯。
⒈
情不知所起:
姐姐们的爱一路相随
为了生个儿子,妈妈在生了三个女儿后依旧奋力拼第四胎,在怀上第四胎的时候妈妈肚子很大,依照当时乡下的说法,肚子里的这个肯定是个儿子。
直到双胞胎女儿出生才终于希望破灭,妈妈哭了,奶奶脸黑了,外公外婆也唉声叹气,埋怨着老天的不公。
没有生出儿子在农村是会被人瞧不起的,甚至是自己的父母,尤其是生了几个女儿之后依旧没能生出儿子,就更使得父母或多或少在村里抬不起头,变的敏感自卑。
也因为这事,爸爸有时候在外面喝了酒回来,可能因为女儿们剪了个短发都会大发雷霆。
不是不爱,只是在农村五个女儿的现实被那种一直承继下来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刺痛着。
生活贫困,小孩又多,沉重的生存压力使得父母无暇顾及几个女儿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当姐姐的俨然就是个小家长了。
女孩子家小时候头上容易长虱子,在自家院子里晒着太阳,让姐姐帮忙捉虱子蓖头发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姐妹之间相差最大的是八岁,在刚能记事的时候,大姐已经开始上初中了,遗憾的是,读了三年的初三,大姐终究也未能考上高中。
最后爸爸千方百计地找人托关系才让大姐去芜湖念卫校。
走出了家门,当了护士的大姐依旧挂念家中的妹妹们,经常会带点“稀罕”的东西回来。
有时候是几本书,有时候是一些没吃过的糖果和饼干或者火腿肠,虽然自己的工资也不高,但大姐还是愿意从牙缝中省出些钱来给妹妹们买点东西或者直接寄钱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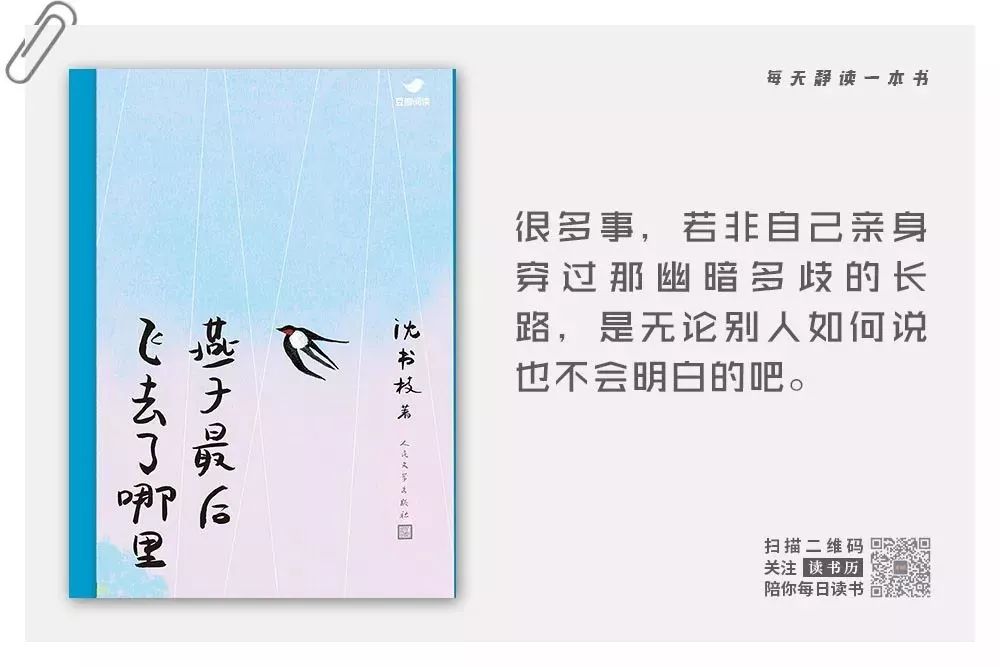
再后来,大姐也开始恋爱了,虽然第一段恋情无疾而终,不过后来大姐还是找到了一个她愿意听从自己内心而非父母之命的姐夫。
虽然没有婚礼,仅仅是去领了个结婚证,自个儿在屋外炒了几个菜给前来看望自己的妈妈和妹妹吃就算是庆祝过了。
二姐跟大姐的情况类似,也是读了三年初三后没考上高中去芜湖念卫校了。
但是跟大姐温厚隐忍的性格不同的是,二姐更耿直,泼辣,容易接纳新事物,融入潮流中。
这点从她跟人的吵架态势和上了卫校后一年回家的装束就能看的出来。
二姐就是二姐,她有不羁的勇敢也有似水的柔情,有刚烈耿直也有忧郁隐忍。
她不甘于像大姐一样只是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护士,中途也换过工作,最后去做了销售,跑业务要拉的下脸,要懂得揣摩人的心思,还要豁的出去,忍受不理解的人的白眼,这一切二姐都忍下来了,高工资就是对她最好的奖励。
那时候她也带了很多稀奇的东西回来给妹妹们,并且非常有远见地在房价还没有开始大幅涨起来的时候在南京买了房,一个人承担着数十万的贷款,为了爱情结婚,却也清贫乐道。
怀孕生子,到辞工作再找到新工作,看似笃定不迫,谁又能知道她的内心也曾惊涛骇浪过呢?
而三姐跟大姐二姐也不一样,她爱哭。
但在欺负妹妹们小不识字,指着书上的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那是她自己的时候,指着课本哄妹妹们说自己还跳过降落伞的时候,在妹妹们被班里男生欺负时立马站出来警告那个男生的时候,她是那么可亲可爱。
没考上高中的三姐就去学做皮鞋,但终究没有坚持下来,兜兜转转,没多久后三姐就结了婚,并顺利怀孕生子。
再后来,为了维持生计,本是厨师的三姐夫谋划自己开家小饭店。
饭店开起来了,生意慢慢稳定下来,看着日子越来越好了,却不曾想,这个时候三姐夫病倒了,并不多久,就撒手人寰,留下悲恸万分的三姐和一个还很小的孩子。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总会喜欢猝不及防地给你开个玩笑,很多的家庭,因为这样玩笑,轰然倒塌。
但即便经历多少的困难和艰难,姐妹之间的情意依旧像那涓涓流水,有着柔情也有坚韧,最终汇入岁月的大海中。
⒉
爱不知所踪:
下雨没有伞的日子里有你相伴
因为是同性别双胞胎,很自然地从小开始就是“出双入对”了,虽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过被展览的命运。
但这种求之不来的特殊的缘分却多少让人羡慕。
这也就使得在做坏事的时候可以结伴而行,“军师”和望风的都有了,“作案”成功率也要高出很多了。
双胞胎嘛,自然是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子剪一样的头发,别问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同样拥有一颗看到更好的东西不肯做出让步的性格,若两个人用的东西都一样,这样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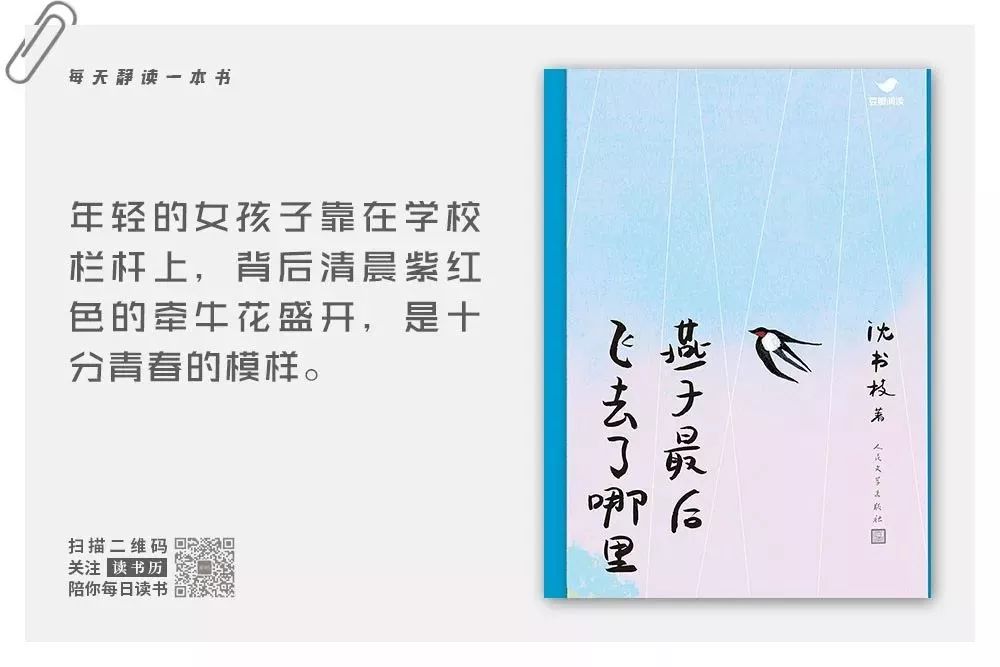
但在生活中哪能无论什么都分的刚刚好呢?
比如堂哥送了她们最新款文具盒,给谁呢?
给谁也不行,最后竟打起来,结果就是文具盒在争执过程中给摔坏了,还顺便打碎了一只开水瓶。
两件一模一样的衣裳,因为领子上的图案有点不同也要因此为谁穿那件公认更好看的而动起手来,简直就是没有一个是省心的主。
及至上小学,两个人就开始坐一张桌子。
那个时候的童年还是很热闹很丰富的,虽然物质条件依旧匮乏。
但孩童时期的纯真和好奇心,使得很多不起眼的东西都会变得好玩多彩,扎小刀,捡糖纸,甚至是热火朝天的全校大扫除都会给她们带来快乐。
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她们也是爱玩爱唱歌。
至于学习,因为家里有一个对于培养孩子考大学极其执着的爸爸,和几个年长能辅导妹妹们的姐姐,在竞争力不算大的学校,考得比其他人高一点的分数似乎也不是很难。
转眼到了初中,因为学校离家远,而只能是靠走着去学校,因此要上学的日子都是天没亮就要出发,偶尔也会出现意外,比如在上学的路上被野狗追跑,把远处黑色人影看成是鬼而吓得屁滚尿流。
再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换过班也被不同的老师教过,有之前小学的校长担任初二时的语文老师,也有性格阴鸷残忍的新校长担任数学老师,还有资格老教的也好的策老师,学业并不顺利,生活也一样。
女生宿舍简陋,人又多,个人清洁变得尴尬而有点难堪,偷盗这种事时有发生,已是见怪不怪。
那时候宿舍大部分的人都处于温饱尚未完全解决的状态。
到了冬天就更难熬了,南方的冬天湿冷入骨,坐在透风的教室,裹着似乎根本不能带来温暖的衣服,手脚经常被冻得发麻,长冻疮也是情理之中的现象。
即便这样还是没能考上高中,生活的艰苦和学业的打击,这些似乎变成了教训加诸在她们身上,也使得那时候的她们更懂得沉默、驯受。
复读了一年之后才如愿以偿考上了心仪已久的高中。
这是一所重点高中,奉行的是一种近乎自虐的刻苦学习方式,且以在教室待的时间的长短为衡量标准。
熬夜大赛就成了全校学生默认参与的活动。
经过初中的大规模筛选,高中生显然要自觉刻苦多了。
每个人心中都自动或者被动紧着一根弦,对大学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许使得她们愿意付出自己当时能付出的一切。
分到文科班后的寂寥,班主任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自作主张地扣下远方笔友寄来的信。
学习到凌晨快两点从教室回寝室还要抱着一两本资料看,做不完的题,看不完的书和考不完的试,孤闭如蛹茧,在黑暗中蓄积力量等到破茧而出的那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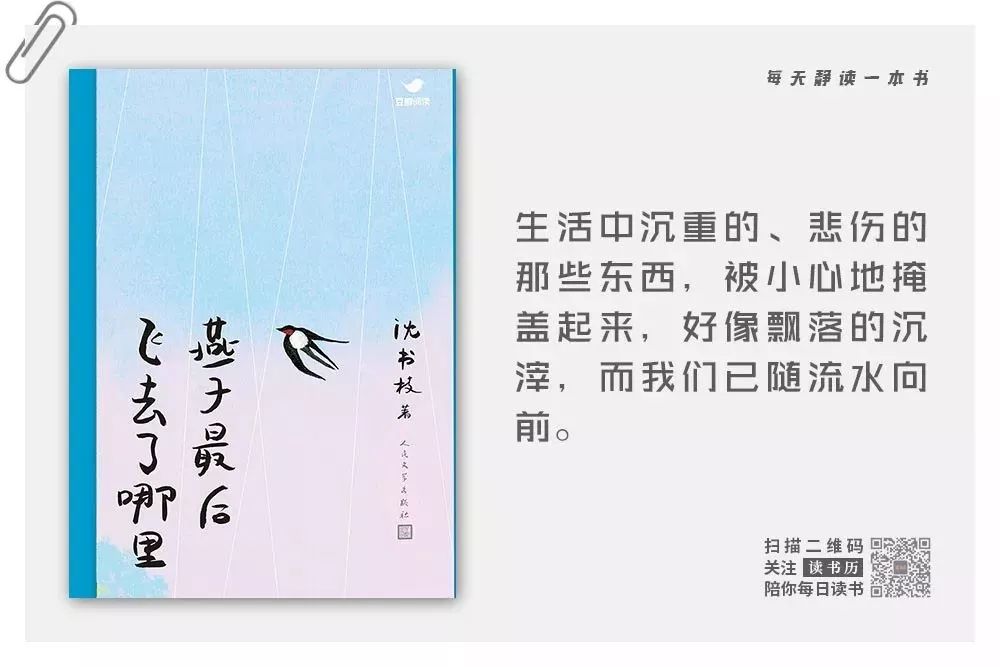
天道酬勤,想实现的已经实现,双胞胎姐妹各自考上不错的大学。所有的付出也已不是徒劳,努力终于是没有白费。
就像,当你在背单词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
你背政治时,太平洋彼岸的海鸥振翅掠过城市上空;
你彻夜刷题时,极圈中的夜空散漫了五彩斑斓。
但是别着急,在你为自己未来踏踏实实努力的时候,那些你感觉从来不会看到的景色会一步步向你走来。
⒊
剪不断的情感枝蔓,爬伸在生命的各个方向
也是在高中的那个时候,因为跟班里的数学科代表总是学习到晚上最后两个相继离开教室,或许是因为刚文科班时,后面同学的刻意介绍。
或许是青春期那敏感的“来自异性的关注必然是爱慕”的观念,亦或是在繁重枯燥的学业压力下,无处安放的荷尔蒙会下意识地窥探,不管怎样,对彼此都有好感是事实。
从慌张羞赧地主动要教书枝数学,到邀请书枝去男生寝室看电视剧,再到两个人在高考半个月前彻夜聊天,那时候说功课,说童年,说未来。
那时候有滚圆的月亮,有凝着露水的狗尾草,还有夏天清早蒙蒙雾气。
那时候有纯真美好的爱恋,有真正的青春的模样。
就在高考放假前一天的晚上,数学课代表的一句“我以前喜欢过你的”表白,因为太过于“别致”而导致书枝的误会,终于随着高考的结束,这段恋情也匆匆地宣告终结。
而妹妹同样有一段类似的关于青春的盛开的情愫,只是最后也是无疾而终。
就像《最好的我们》中说的那样:
那时的他是最好的他,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
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怎么奔跑也跨不过的青春,只好伸出手道别。
至于父母,虽然在当时农村的标准中并不算是“圆满”,因为没生出儿子。
但大姐第一次没考上高中的时候,爸爸让她复读了两年;
二姐第一次没考上高中的时候,爸爸也是让她复读了两年;
三姐读了两个五年级和初三,连最小的一对双胞胎也是读了两年的初三,爸爸“是要他的女儿上大学的”,这在当时的农村的不会读书没考上就出去打工的环境中,显得“另类”。
母亲慈爱温柔又勤快,爱干净会持家,对孩子们及其宠溺,至少在书枝的记忆中是不曾被母亲打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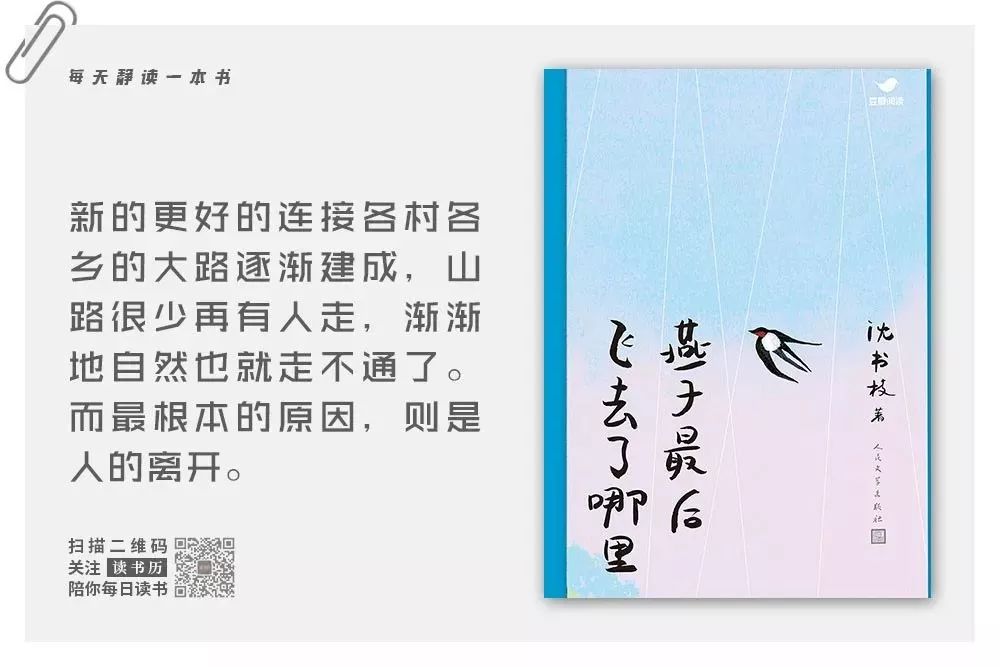
就这样,父母用汗水和爱撑起了整个家,唯一遗憾的就是,生活所迫,母亲因为想多挣点钱,很少在家待过,除了双胞胎姐妹复读初三的那年,那一年是被书枝形容为“漫长灰暗的青春期里难得的光明与温柔”。
只是母亲不辞辛苦到外地栽秧赚钱,在家的父亲仍旧一个人在田里跟耕劳不辍,三个大女儿都已经离家,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在高中住校。
一个人守着昏昏的灯火,看着那高高的屋角,其中的孤苦又哪里是当时的我们能理解能感受到的?
一路走来很是清苦,可那段旧时童年的时光,依旧如同蚌壳深处小小的明珠,在暗夜的回忆里晶晶发亮。
再到后来,父母追随女儿们在城里谋生,而年轻人也离开了这只有倚靠土地和老天才能获得微薄收入的乡村,转而在城市里寻找生活。
至此,山路因为走的少了渐渐地就走不通了,而那曾经连结田畈的被人踩得结实的路也渐次荒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