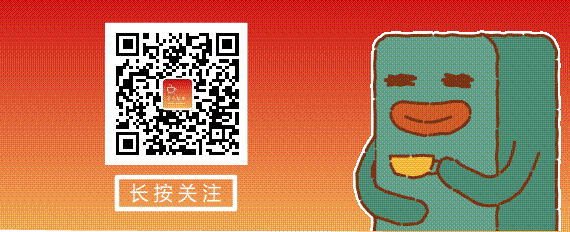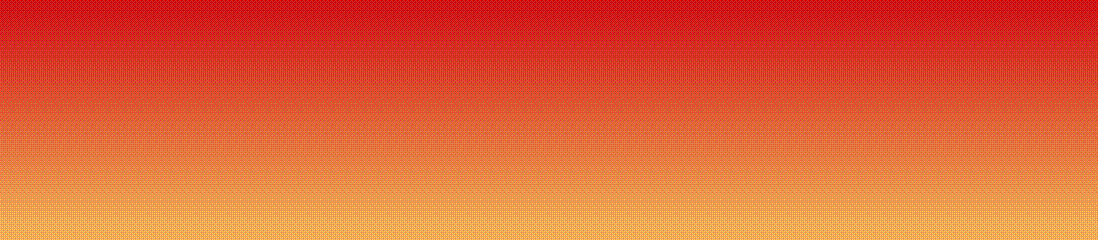
一身合体的海军蓝套西,白色衬衣,棕色的皮鞋被刷得油光发亮,头发朝后梳起,被摩丝固定住,身上还传出若有若无的男士香水味。
等等……这、这是谁?
当我确认电梯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再度疑惑地看着倒影中的自己——不对,我怎么会穿成这样?
——林松
 图源 | PEXELS
图源 | PEXELS
茶 点 故 事 | 现 实 边 缘

我是谁?
我在哪儿?
不知从何时开始,黑暗已经将我包围。我仿佛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坛子,浓稠得如墨汁一般的空气随着每一口呼吸涌入鼻腔,再注入肺部。
一阵强烈的窒息感紧随而至。
忽然,这个“坛子”开始晃动,我看到前方突然闪出一丝光线,如同穿破黑暗的闪电,绽放开来。
“坛子”碎了。光线穿过裂缝,将这个黑暗的空间撕裂成无数碎片。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坐在一辆商务车中,车厢因为颠簸有些摇晃。
“您醒啦?这边在修路,地面敲碎了,晃得有些厉害。”
前方的驾驶座上的司机说,声音有些熟悉。
我感觉头一阵一阵地疼,车厢每晃动一次,都像有人拿着锤子在脑袋里敲打一样。我用力捂着额头,紧紧抵在车座的靠背上,尽可能减缓晃动。
直到过了翻修的路段,车子平缓行驶起来,我才坐直身体,环顾着车厢。
这是在哪里?我要去哪儿?剧烈的疼痛让我一时什么都想不起来。
“林总,昨晚没休息好吗?看你睡了一路。”前座的司机又发话了。
我抬头从后视镜中看到了他的脸,那是一张很普通的中年男人的面孔,前额头发稀少,两道深深的法令纹让他看上去有些严肃。
他叫我林总?
“我们……去哪儿?”我问。
司机从后视镜上看了我一眼,满是疑惑地说:“去公司啊,环球金融中心。”
环球金融中心……我透过车窗看向外面,楼宇飞驰着后退,熟悉的道路让我混乱的思绪慢慢变得顺畅。我想起来了——
我叫林松,28岁,单身,是千万个沪漂一族中的一员,目前就职于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职位是一名小小的程序员。以我不入流大学毕业的资历,能进这家企业,完全是凭借走后门——总经理林柏,是我堂哥。
我现在乘坐的商务车就是我堂哥的车,前排的司机老张,也是他的专属司机。老张知道我和堂哥的关系,所以也一直叫我林总,尽管我只是公司中最小的那一枚螺丝钉。
我想起昨晚堂哥约我去他家喝酒,他因为半年前和嫂子离婚,一直郁郁寡欢,时不时拉着我去他家喝酒。看样子昨晚喝得可不少。
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9:30,糟了!又迟到了!
堂哥一向很准时,他应该早就到公司了。想起主管那张板起的臭脸,我感觉头更疼了。
老张开车很稳,不紧不慢地停在了大楼下,我拉开车门直奔电梯口。
由于上班高峰期已过,只有我一个人在等电梯。进入电梯后,按下28层,电梯门缓缓合上,打磨得光亮的金属门清晰得如同镜子,我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一身合体的海军蓝套西,白色衬衣,棕色的皮鞋被刷得油光发亮,头发朝后梳起,被摩丝固定住,身上还传出若有若无的男士香水味。
等等……这、这是谁?
当我确认电梯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再度疑惑地看着倒影中的自己——不对,我怎么会穿成这样?
作为一个标准的IT男,我向来是一件格子衬衫走遍天下,甚至从未穿过正装,更别提梳理发型和喷香水了。今天究竟为什么我会穿成这样出门?
叮——电梯铃声打断了我的思路,28层到了。
我犹豫了一下,踏出了电梯,低着头走进公司。这一身莫名其妙的装扮让我很不自在,我恨不得立马找个地洞钻进去。
“林总,早。”漂亮的前台姑娘Coco向我打招呼,我装作没听见,快步走向了办公区。
林总?老张叫我“林总”是因为知道我和堂哥的关系,但为什么Coco也会这样叫?她平时可是连招呼都不和我打的啊!
“林总!”就在我打算低调地蹭向工位时,迎面走来一个穿着高跟鞋、打扮干练的年轻女子。那是堂哥的秘书Joanna。
“林总?”她走到我面前,带着美瞳的大眼睛紧紧盯着我,很明显是在和我说话,“我在您办公室等很久了,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材料我放在您办公桌上,现在去谈谈?”
我看着她,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难道就因为我今天这莫名其妙的装扮,导致她们把我错认成堂哥了?虽然我们小时候被很多人说长得像,但长大后的气质却千差万别,基本上很难混淆。
“林总,您怎么了?”Joanna满是疑惑地看着我,“我先去您办公室等您。”说罢,踩着将近十公分的红色高跟鞋走向了办公室的另一头——堂哥的总经理办公室。
我犹豫了一会儿,鬼使神差地抬起了腿,走向了那个办公室。

松柏不分
从我踏进办公室的那一刻,Joanna就开始滔滔不绝地汇报工作:“林总,这是鑫嘉投资发来的合作方案,我们今天必须要确定下来给他们一个回复。另外,上周联系的三家基金公司……”
我站在她面前,只觉得头疼欲裂,她说了足足五分钟,但我一个字都没能听进去,只是不停用力地揉着太阳穴,希望能缓解那阵疼痛。
“林总?”Joanna终于停了下来,她走近我问,轻声问,“您是不是不太舒服?快坐下。”她扶着我坐在了办公椅上,浓烈的女士香水味让我的头疼更加严重。好在办公椅很软,我感觉自己深深地陷在了里面。
“喝水。”Joanna手脚麻利地倒了一杯热水递过来,我接过慢慢喝了一口,感觉疼痛稍微缓了缓。
“Joanna,我……我是林松。”我有些紧张地说出了实情。Joanna平时在公司是出名的冰山美人,能干且有想法,是堂哥的得力助手。
Joanna满是疑惑地看着我,良久才问:“什么?”
“我不是林柏,我是林松。”我重复了一遍。
Joanna注视了我几秒,小声问:“林松是谁?”
我呆住了。虽然我们IT部门和Joanna在工作上交集甚少,但她绝不可能不认识我。
Joanna皱着眉头看了看我,然后噗嗤笑了出来,她坐在了办公桌的一角,低下身靠近我,有些娇嗔地说,“林总今天怎么有这么好的兴致开玩笑?”
说完,她伸手掠过我的下巴,十指停在了衬衫的衣领上,轻轻地整理起我的衣领,然后轻声说:“你看你,出门太着急了吧,衣领都卷了。“
这是第一次有女生靠我这么近,我感觉身体瞬间崩紧,心跳加速,耳朵根一阵发烫。但理智让我将座椅后退了一段距离,离开了她手指的范围。
“我……我没有开玩笑。” 我试着表达清楚,毕竟她是公司少数知道我和堂哥关系的人中的一个,“我是IT部的林松,林柏的堂弟。”
Joanna脸上的笑容慢慢淡去,她一双大眼睛看着我,满是疑惑。良久,她才开口说:“我们公司没有林松这个人,也没听说过您有堂弟。”
Joanna不知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我两眼空洞地看着前方,一时还理不清思绪。
如果说Coco是因为我今天的打扮把我认错成堂哥,倒也说得通,但是Joanna怎么可能认错?
等等……我今天为什么会穿得这么奇怪来上班?我努力搜寻着早晨起床后的记忆,但不知是因为剧烈的头痛还是其他原因导致,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今天记忆的起源就是在老张车中。
昨天下班时,堂哥特别让老张接我去他家喝酒,我依稀记得,堂哥喝了很多,我也喝了不少,然后就没了意识。也就是说,我昨晚应该是在堂哥家过夜的,那么……
突然,我猛地坐直了身体——堂哥呢?
我拿出手机,打开通讯录,通讯录最顶部的名字出现在眼帘——林柏,本机号码:+86185****5573 。
我的手有些颤抖,输入了一串熟悉的号码——那是我自己的号码。
“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电话那头传来冰冷的女声。
为什么堂哥的号码会成为我手机的“本机号码”,而我自己的号码却是空号?我退出通讯录界面,看到手机满是金融类的app。
不!这不是我的手机!但……为什么我可以解锁?
无数的疑云在脑海中浮现。我不安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大,前面是几张黑色的皮具沙发,中间是一张茶几,上面放着一套茶具。墙壁上挂着几幅看不明白的画,后面是巨大的壁柜,柜子中放了很多厚厚的书籍。
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就在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阵敲门声吓了我一跳。
我像小偷一样紧张地看着门口,良久才低声喊:“请……请进。”
门被打开,走进来一个人,是司机老张。
“林总,您的包忘拿了。”老张双手递过来一个深蓝色的手包,放在了办公桌上,他朝我点了点头,准备出去。
“老张。”我叫住了他,看着他的眼睛,低声问,“我是谁?“
老张满脸疑惑,两条法令纹显得更深了,良久才回答:“您是我老板,林柏。”
随着那个名字说出,我耳边响起了重重的耳鸣声,就像一架飞机在耳边徘徊时发出的轰鸣声。我皱着眉头按住耳朵,直到嗡嗡声变小。
老张看着我,眼神中充满疑问。我也看着他,问:“今天,你在哪里接的我?”
“就在您家。”老张毕恭毕敬地回答。
“我出门时也穿成这样吗?”
“是的。”老张点头说,“您平时也穿成这样啊。”
我扭了扭身体,贴身的西装让我感觉很不舒服,老张似乎还在等着我的提问,我想了想,问他:“老张,你认识林松吗?”
“林松?”老张想了想,摇摇头,“没有印象。”
我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空了身上所有的力气,老张似乎还说了什么,但我一句也没听清,良久,才用尽力气说出一句话:“你先出去吧。”
老张点点头,走出办公室,关门的瞬间,他还看了我一眼,仿佛在看一个街头的疯子。
我一动不动地瘫坐在办公椅上,柔软的椅子仿佛要将我深深地陷进去。我拿起老张送过来的包,我有印象堂哥用过这个包。这是一个拉链大钱包,上面印着Prada的logo,我打开钱包,里面放着一叠现金,几张白金信用卡,以及一张身份证。
我颤抖着手拿出身份证,怔怔地看着。
姓名:林柏,出生日期:1989年6月11日。
左边的照片是一张熟悉的脸,左边嘴角有一颗痣。
那是我自己。
这时,我发现我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手表,表盘上刻着iwc三个字母,我叫不出这个品牌的名字,但我肯定,这个手表不是我能买得起的。
或者说,不是林松能够买得起的。
随后我又看到,在我衬衫的衣袖上,绣着两个艺术体的英文字母:LB。
林柏。

交换的人生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和堂哥林柏交换了人生。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代替了他,而堂哥本人却不知所终,曾经的我也似乎从未存在过。或许……是我不小心穿越到了另一个次元空间?
我曾经看过不少关于灵魂互换、次元穿越的小说和电影,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会不会也那么“超现实”,但目前来看,似乎真的发生了。
我不知所措地在办公室度过了大半天,甚至连午饭都没有去吃,直到一阵再也憋不住的尿意袭来,我才走出办公室,直奔厕所。
尽管我一直低着头,但总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我像做贼一般心虚不已,不敢直视任何人的目光。
回办公室时,Joanna在门口叫住了我,她问:“林总,您今天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低声说:“没事。”
Joanna说:“看您脸色很差,要不要让老张先送您回去休息?”
我想都没想就点点头,说:“好的。”说完快速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现在在公司的每一秒都是煎熬,我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奇怪”的地方,离得越远越好。
15分钟后,我坐上了老张的车。
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人生,尽管它很枯燥和苍白,但此时,我却感觉自己的人生突然被架空,仿佛此前的二十多年只是一场梦,而此时大梦初醒,要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
在我的记忆里,我毕业于一所三流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碌碌无为。几年前,父母因为车祸去世,堂哥一家成了我最后的亲人。堂哥让我到他的公司上班,我又继续着波澜不惊的生活,没有丝毫起伏。
而堂哥林柏,从小成绩优异,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之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研,毕业后回国创业,公司发展也非常顺利,几年内便成为中型规模的企业。
可以说,他那华丽的人生,是我这种小人物的终极梦想。而可笑的事,当这种华丽人生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时候,我却陷入了无尽的惶恐和不安中。
车窗外,陆家嘴的高楼大厦飞速后退,宛如我过去二十多年的记忆,冰冷而灰暗,而此时它们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摧枯拉朽,只留一片尘埃。
很快,老张把我送到了堂哥家楼下。我进入电梯,电梯里面装着一面长镜,镜中的我西装革履,仿佛是年轻有为的成功人士。
到达楼层后,我走到门前,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钥匙。我在门前站了很久,忽然想起堂哥曾经提过,这扇大门是可以通过指纹解锁的。
我心中一动,找到了门边上的密码器,慢慢地伸出右手拇指按在上面。
“咔嗒”一声,门开了。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我的心还是狠狠地一沉。
这间房子很大,我赤脚走在地板上,感觉每一件家具都那么陌生,我像个入室盗窃的小偷一般,不敢发出一丝声响。我把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确定家中只有我一个人后,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家里又冷又静,只能听到挂钟秒针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就像幽灵在四周游荡。
我在冰箱里找到了几片面包,狼吞虎咽地塞进了嘴里,塞着塞着,我突然感觉一阵强烈的恐惧将我包围,就好像一个被囚禁了几十年的罪犯被释放,他要面对的不是法律或道德的审判,而是整个人生被架空的孤独。
那种孤独是致命的。
我依稀记得,昨晚和堂哥就是坐在这里喝酒,听他诉说着自己婚姻的不幸。我多么希望他现在能开门走进来,喊我一声“林松”——就算是骂我也没关系。
我呜咽着哭了出来。从记事以来,只有几年前父母过世时我才哭过,而现在,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河水,汹涌流出,完全不受控制。
真正的“林柏”在哪里?而曾经的“林松”又在哪里?我究竟是谁?我不知道。
我的人生仿佛被翻过了另一面,过去的记忆虽然清晰,但却显得那么不真实。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浓浓的倦意涌来,我行尸走肉般走进了卧室,卧室的床头挂着一幅巨大的婚纱照,里面的两人幸福地依偎在一起。
忽然,我心中一动——虽然我和堂哥五官相似,但绝不是一模一样。
我仔细看着那张婚纱照,照片中的林柏左边嘴角有一颗淡淡的痣。我摸了摸自己嘴角边上的痣,茫然地看着照片中的新郎。
婚纱照中的新郎不是堂哥,是我。
良久,我木然地躺在了床上,柔软的床褥把我包围,我侧着身子,脑海中一片混乱。床头柜上放着一些杂乱的物件,几个棕色的小药瓶,一些零钱,还有一包烟。
我想伸手去拿烟,但却发现再也没有力气抬手了,我的脑海中飞快地闪过今天的事,这些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
我……真的是林柏吗?
那么,林松又是谁?

林松是谁?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只是觉得意识逐渐模糊,身体仿佛在柔软的床褥中不停下沉。当我逐渐有意识时,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房间放了一张小方桌,桌上一盏豆大的烛火撑开了很小范围的一片光明。
黑暗中走出来一个人,他缓缓坐到了桌子的另一边,透过烛火我看到了他的脸。
“哥!”我脱口喊出。
堂哥抬头看着我,脸上浮现出一丝奇怪的笑意,他说:“你坐下。”
我坐在了桌子的一端,看着对面的堂哥问:“哥,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她们都把我认成了你?”
堂哥没有回答,只是用双眼紧紧盯着我,忽然笑了起来,说:“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我拿起桌上的烛灯靠近他的脸庞,那一瞬间,我居然无法分辨眼前的面孔究竟是“林柏”还是“林松”!“堂哥”微微一笑,我看到他左边嘴角有一粒淡淡的黑痣。
他是“林松”!那么,我又是谁?
我的手一松,烛灯跌落在桌面,整个房间陷入了深沉的黑暗。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刚刚梦中的场景让我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房中的灯依旧亮着,照得一切都显得有些惨白,我看了看时间,5:38。不知是因为床太软还是什么原因,我只感觉全身都有些酸痛。
起身看了看窗外,才发现整个世界都还在黑暗中沉睡,静得如同一潭死水,看不到丝毫涟漪。
不对……上海的夜色我记忆中看过无数次,但并不是现在这样的。突然,我的心猛地一震!
昨天我直接被老张理所当然地送到了这个家里,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家”并不是这里!我所住的地方,是一间租来的一居室老公房,30平米不到,老旧的墙壁和家具会散发出霉味。绝不是现在这间敞亮又奢华的豪宅。
如果“林松”真的存在过的话,那在那个脑海中熟悉的地址里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痕迹。
我感觉一股血液直冲脑门,心跳猛地剧烈起来,就好像发现了可以拯救世界的秘密一般。
我脱掉衣服在浴室冲了个澡,温热的水柱打在皮肤上,仿佛要冲刷掉掩盖着记忆的尘土。我飞快地洗完,在房中找到了另一套西装,便随便换上了。
走出小区时,天色已经翻白,片状的云朵堆积了半个天空,就像成片的死鱼翻出肚皮浮在湖面,向世人展示着它门曾经的存在。
在这一片富人区,路过的出租车并不多。当我坐上车时,天色已经泛红,昭示着新的一天已经来临。
出租车在空旷的马路上飞驰,二十分钟后,停在了一个老旧的小区前,付完钱后,我飞奔进小区。
“23号……23号……”
我喃喃着记忆中的一个数字,熟悉地穿过小区的道路。当我站在23号楼下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近阴暗的楼道。
楼道中有一阵浓烈的霉味,我快步走向三楼,“林松”住在301,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破旧的铁门和锈迹斑驳的门牌号。
当我站在301门前时,我呆住了。
那是一扇半旧的实木门,门上贴着一个倒福,似乎因为时间太长有些褪色,还依稀能听到房中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不对……和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我忽然觉得身体有些发软,我用手扶住满是铁锈的楼梯间扶手,冰冷的金属让我浑身发寒,我重重地喘着气,楼道间浓重的霉味侵蚀着我的肺,我感觉快要窒息了,我飞快地冲出了楼道,跑出了小区。
也不知过了多久,当我停下来时,站在了一个陌生的路口,我无力地依靠在路边的墙壁上,斑驳的墙壁似乎饱经沧桑,大片黑色的霉斑吞噬了原本的白色。
我努力在脑海中搜寻关于“林松”存在过的证明,然而我惊讶地发现,尽管我拥有那么多年的记忆,却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证明“我”曾经存在过。
或许,林松本来就不曾存在?
晨风带着凉意吹拂过来,我紧了紧身上的西装外套,走回了路口。
现在的我,名叫林柏,毕业于名牌大学,半年前离异,是一家金融公司的总经理。我还有一个不存在的loser“堂弟”林松,我拥有他二十多年的记忆,但昨天开始,他却“从未存在过”。
“林松”就像森林中的一颗树,即便被人砍走,也丝毫不会减退森林的绿意。

存在
当老张的电话打过来时,我已经走过了陆家嘴天桥。老张问:“林总,您今天不去上班吗?”我说:“老张,不好意思,我今天自己走来公司了,忘记和你说。”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少路,当我走到陆家嘴时,双腿已经有些微微发抖。
从天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乞讨者坐在花坛的边上,凌乱的头发结成块,遮住了一半的脸庞,身前放着一个残破的碗,里面有零星几个硬币。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双眼木然地看着路过的行人。
我的心突然微微一紧,在这个诺大的城市,不知有多少个这样渺小如微尘的人物,他们屈服于命运,毫无存在感,直到某一天悄无声息地消失,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意。
我拉开了钱包的拉链——刚才出门前因为考虑到要打车,便顺手带了钱包。钱包中有一叠百元钞票,我也没有细数,全部抽了出来,轻轻地放在了他的碗中。他满脸震惊地看着我,张着嘴,没能说出一个字,双眼却冒出了泪花。
那一瞬间,我也感觉鼻子微微一酸。我匆忙地起身离开,不敢回头,就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一般。我在心里不停地重复:我是林柏,我很有钱,给点钱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
我提前不少到达公司,前台Coco看到我,微笑着打招呼:“林总早。”
我还是不太习惯她对我的称呼,只是微微地点点头,便快步走向了办公区。提前到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是踩着点到公司的。忽然,我的心微微一动,把目光看向了办公室的角落区域——那是IT部门所在。
我记忆中,“林松”就是在那里办公的。
我慢慢地走过去,IT部门只有孙主管到了。记忆中,孙主管一直是严肃地板着一张脸,做事情一丝不苟。孙主管看到我,很恭敬地起身喊了声“林总”,他在公司多年,一直尽心尽力,头顶的头发也因为经常熬夜加班而变得稀疏,但因为IT部门在公司并非核心部门,因此也基本上得不到更大的提升。
离开前,我看了看IT部门的工位牌,没有“林松”这个名字。
或许,林松本来就真的不存在?
当我再一次在总经理办公室坐下时,已经不像昨天那样无所适从了。我翻了翻桌面上的一些文件,全是一些看不太明白的合作事宜,我完全找不到丝毫与之相关的记忆,只好放回了原处。
办公桌边上有一个三层的小柜子,我一一拉开,第一层是一些文件和文具,第二层放了些茶叶、零食,第三层有几包烟和一些药,其中一个棕色的药瓶有些眼熟,我想起昨晚在床头柜上也有看到。
是什么药?我伸手准备去拿,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动作。我像小偷一样紧张地、轻轻地关上了抽屉,喊了声“请进”。
进来的是Joanna,她今天穿着一件贴身的白色衬衣,领口敞开,豪放地露出了事业线,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的短裙,一双高跟鞋让白皙的双腿显得更加修长。
她看着我,柔声问:“林总,今天好些了吗?”
“好、好多了。”我点点头,不敢直视她,但眼睛的余光不受控制地看了看她的胸口。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轻轻笑了一声,走到了我身边,笑着说:“你昨天真是吓到人家了。你看你,衬衫又没理好。”说完伸手帮我理了理衣领。
我被她亲密的举动和语气吓了一跳,急忙将办公椅退了一段距离,她“啊唷”一声,一个重心不稳,跌坐在我身上。
一阵浓郁的香水味将我包围,我一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心跳如雷,不知所措地呆住了。
Joanna在我大腿上坐稳,双手绕住了我的脖子,在我耳边说:“你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到底怎么了?”
她吐气如兰,吹得我耳根痒到了心底,而胸前也被她柔软的胸部紧贴着,一时间只觉得自己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Joanna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
她还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只感觉到她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我的脸庞。
忽然,一阵冰凉的触觉从我脸颊上划过,我侧眼望去,看到了她无名指上的那枚戒指。
我的心猛地一震,突然想起——Joanna已婚。
我感觉自己像被人当头泼下了一盆冷水,瞬间清醒了不少,我用双手把她推开,说:“Joanna,别这样。我……我……”
Joanna站稳,满脸疑惑地看着我,然后轻叹了一口气,说:“你的状态还是不太好,我昨天帮你约了汪医生了,等一下让老张来接你过去。”
“医生?”
Joanna点点头,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离开了办公室。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物,尝试着做了做深呼吸,缓解自己依旧亢奋的情绪。刚才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和女性有那么亲密的接触——尽管作为“林柏”的我,应该在半年前还离过婚。
我感觉一注暖流从鼻孔中流下,我流鼻血了。
窘迫地处理干净后,老张来敲门,说送我去什么汪医生那里,我问也没问就和他走了,出办公室时,我感觉Joanna在看着我,但我却没有勇气和她对视。
坐上老张的车后,老张问我:“林总,您今天上午怎么自己来公司了?”
“我、我随便逛了逛,就直接来公司了。”我随口撒了个谎。
“哦?到哪里逛呢?”老张向来都比较健谈。
我想了想,说:“德平路。”那是我今天天微亮时去的地方。
老张笑了笑,说:“是不是找回忆?你们年轻人都喜欢干这事,我记得您以前就是住那里吧?”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老张,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我以前住哪里?”我重复着他的话。
“我听您说过的。”老张继续说,“也是您年轻有为,几年不到就有了自己的大房子,要知道上海多少小人物拼死拼活一辈子,也走不出那租来的30平米的老公房。”
原来我以前真的住过那边!难怪我记忆中总觉得那里才是“家”,而今天上午看到的模样,也确实和记忆中的有些不同。
为什么那么久远的记忆,我却感觉这么熟悉而清晰呢?
老张还在说着什么,我看着窗外,完全没有听进去。我想起刚才Joanna亲密的举动——很显然,她和我之间有着一层不可告人的关系。
尽管我已经将这层关系忘得一干二净,但依旧有一股浓浓的羞耻感油然而生,我在心底默默地唾弃着那个自己。
不多时,老张将车停在了一栋大楼下,我回过神来,问:“这是哪儿?”
“不是来见汪医生吗?”老张一脸惊讶地看着我,“Joanna说帮你约好了的。”
“汪医生?”我这才想起此行的目的,“汪医生是谁?”
老张从后视镜里看着我,清晰地吐出一句话:“您的心理医生。”

恩它卡朋
坐在我身前的女性留着及肩的长发,年龄在二十五六岁,五官精致小巧,她朝我微微一笑,露出一个深深的酒窝。
“汪、汪医生?”不知为什么,我开始紧张起来。
“你一般叫我Jessica。”她双眼紧盯着我,说,“Joanna跟我说了你的情况,我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还在用那些药?”
“什么?”我完全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Jessica眉头微皱,她看着我,慢慢地说:“你告诉我,你是谁。”
这个问题把我难倒了,我看着她,良久才回答:“林……柏?”
Jessica说:“林先生,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我摇了摇头。
“OK。”Jessica咬了咬嘴唇,唇色变得更加鲜艳,她沉默了半晌,说,“半年前,你因为抑郁症在我这里治疗,当时你的情况很严重,我给你开了抗抑郁药物的同时,在你情况缓解之后,药物治疗也暂停,但你自己又开始私下服用药物。”
“要知道抗抑郁药本身的副作用只在呕吐、头晕之类的生理反应,但是辅助药物珂丹也有可能引发心理上的副作用——致幻。”Jessica轻声说着,双眼时刻注意着我的情绪变化,“只是我也没想到药物的副作用会这么强。”
也就是说,我是因为抑郁症长期服用药物引发的副作用,才会导致现在的“混乱”?
Jessica轻叹一口气,继续说:“珂丹就是我之前说过的恩它卡朋片,作为抗抑郁治疗的辅助药物,副作用通常不会那么明显。“说完,她起身从办公桌上拿出一个棕色的小药瓶,刚在了我身前。
这种棕色药瓶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床头柜上,一次是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你的情况可能是因为长期大量服用,加上心里原因导致短暂性失忆……或者,或者……“Jessica忽然不说下去了。
“或者什么?“我问。
Jessica轻叹了一口气,说:“部分患者会因为精神及药物副作用的双重压力之下,导致记忆混乱,分裂出一个新的人格。就是所谓的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我重复着她的话。也就是说,林松本来就不存在,是我因为抑郁症而分裂出来的另一个人格?
Jesica点点头,说:“那个人格可能是他隐藏了自己想要逃避的现实而生出来的,会混杂他以前的记忆,所以格外真实。但不要担心,如果是因为药物影响的话,保持隔断药物一段时间,会慢慢恢复的。“
慢慢恢复?也就是说,当“恢复“之后,我现在这个”人格“——林松,就会彻底消失。
我感觉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瞬间分崩离析,如同在宇宙中破碎的一个星球,化为无数尘埃,飘荡在黑暗的空间,找不到出路。只是,这样一颗星球的消失,也不过是为宇宙添加几粒微尘而已。
就像消失的“林松”,不会有任何人发觉。
Jessica看着我,认真地说:“林先生,我不知道你从哪里买到的处方药,但是请你务必记住,一定不能再吃药了。“
我点点头,不知为何,忽然感觉浑身发冷,我搓了搓手,问:“我是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Jessica说:“你的心思缜密,心理干预作用不大,但是目前来看,和你的婚姻的失败有很大的关系。林先生,我此前建议过很多次了,请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暂时离开这个会让你回忆起不快乐的城市,修养一段时间,这样对你的病情会有很大的帮助。”
“去哪里呢?”我实在想不到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放松。
“出国旅行散心,或者回趟老家看看父母——这对你恢复记忆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父母?”我想起几年前出车祸的父母亲,摇了摇头,“他们去世了。”
“去世?”Jessica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你确定?”
被她这么一问,我反而不太确定了。我努力搜寻着脑海中关于父母的回忆,忽然想起,去世的是“林松”的父母,而我真实的身份是林柏,林柏的父母一直健在。
“我可能……记错了。”我回答。能将父母的生死记错,这点让我感觉很羞愧。
Jessica却很宽容,她微微一笑,说:“林先生,你在这个人格里面将父母设定为双亡,说明你内心可能在逃避父母。或许,他们也和你的病因有关,我非常建议你回家和父母相处一段时间,对你的病情肯定有利。或许……还能知道您致病的真正原因。”
我点点头,Jessica继续说:“我接下来会去一趟法国见一见我的导师,我会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或许他能有更好的办法帮助你恢复。”
我呆滞地不知道回答什么,只能连说几声谢谢。
Jessica笑着说:“那今天就到这里吧。离开前,还请结算一下这几次的费用。”
我跟着Jessica来到结算处,从包里随便抽出一行白金卡,收银员刷卡之后将pos机递过来,说:“请输入密码。”
密码?我再次紧张起来。我清楚地记得“林松”所有卡的密码,但林柏的银行卡密码又会是什么呢?
Jessica很显然看出了我的窘迫,微笑着说:“或许……试试你的生日?”
生日?我拿出包里的身份证看了看,输入了890611六个字。
支付成功。
我苦笑了一声,Jessica也笑了,她笑得真好看,脸颊边上露出深深的酒窝。

丢失的记忆
两天后,我回到了老家。
父母的样子还是“林松”脑海中的伯父伯母,而我现在还处于林松的人格,导致我每次看到他们都想喊伯父伯母。
而奇怪的是,父母对我也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亲密,我和他们之间似乎隔着一道墙。但他们还是很关心我,为了我的病情着想,让我多看书而少接触网络和电视,还带我去小时候常去的地方“寻找记忆”。
在这个陌生又温暖的家中,我度过了漫长的一个月,这个月,Jessica给我来过几次电话,询问我现在的状况。而公司那边,我在临走前硬着头皮把工作授权给了公司的几名副总。
我慢慢接受了自己是林柏的事实,而在父母的帮助下,也确实感觉慢慢找回了丢失的记忆。而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我究竟为什么抑郁,而又为什么会和父母间有层无法穿透的“墙”?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妈妈在房间偷偷抹眼泪,我悄悄地走过去,发现她在翻着相册。妈妈看到我来了,把相册合起。
“妈,你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妈妈说着,把相册放回了柜子中,“小柏,你快去睡觉吧。”
“睡不着。”我坐在了妈妈身边,这些天,我刻意和父母保持亲近,想要打破那层隔阂,“妈,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妈妈叹了一口气,说:“你现在这样,都是怪我。当初你和小莹结婚几年没有小孩,我和你们吵了好几次,你就一直对我和你爸不冷不热的,去年过年时在家小莹和我在家大闹了一场,结果没多久你们就离婚了,然后你就得了这病,真是造孽啊!”
原来如此!那一刻,我终于知道了自己得抑郁症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林松”会父母双亡——因为我和小莹离婚是父母与她争吵引发的,而又因此导致我患上抑郁症,因此我在内心深处对父母有抵触。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在“林松”的记忆中会父母双亡,以及为什么我这一个多月以来总觉得与父母之间有一层隔阂。
“妈,都过去了,没事了。”我轻轻拍了拍妈妈的肩膀,妈妈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似乎还不习惯和我这么亲近。
我伸手从柜子里拿出了那本相册,笑着说:“妈,你给讲讲我小时候的事吧,我很多都记不起来了。”
我翻开了相册,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熟悉而又陌生。妈妈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表情有些异样。
相册记录了我从小到大的成长,翻到最后,是我和小莹的结婚照。当时的我们都很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当时我也很开心,照片里白皙的面孔透着光芒。
“当时的妆也太浓了吧!”我打了个哈哈,想要缓解气氛,指着婚纱照中我自己的脸,“和现在太不一样了,连我脸上的痣都遮掉了。”
妈妈很勉强地笑了笑,我内心叹了一口气,尽管我很努力地想要缓解我们之间的关系,但似乎并没有凑效。或许需要时间吧。
我把相册收起,跟妈妈说了晚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时,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包裹着我,我身上的汗毛竖起,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我将被子紧紧地裹住自己,不去在意那种奇怪的感觉,强迫自己快点睡着。
啊,真希望我能快点恢复记忆啊,毕竟我的人生这么华丽、这么灿烂。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沉沉地睡去,梦中听到了夏天草丛的蛐蛐声,就像孩童时代吹出的口哨,又像由远而近的警车鸣笛,尖厉而刺耳,充斥了整个梦境。

尾声
法国,尼斯。
Jessica穿着比基尼走在蔚蓝海岸的沙滩上,那是由一粒粒白色石子组成的沙滩,干净而温暖。
远处,林柏正看着两只大白鸽争食,他拿了一粒石子扔过去,鸽子噗啦啦飞走了。
Jessica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了林柏,林柏抚摸着她的手臂,柔声问:“喜欢这里吗,汪大医生?”
“喜欢。”Jessica将脸贴在他的背上,忽然笑了笑,说,“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他?”林柏轻蔑地笑了一声,“现在,恐怕在牢里了吧?”
Jessica说:“你也真是厉害,能够打点那么多人。”
“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林柏一个转身,把Jessica抱在怀里,轻轻咬着她的耳朵说,“宝贝,最重要的是还有你谋划和帮助。”
Jessica看了看远方湛蓝的天空,笑了起来,脸上露出深深的酒窝,她说:“你是没看到他怀疑人生的表情……也真是可怜啊,他真的以为自己精神出问题了呢。”
林柏从沙滩上捡起一粒石子放在掌心,说:“他就像这小石头,丢进海里,也丝毫不会影响这整片沙滩。”说罢,他用力将石头扔进海里。
“也是,好歹他还享受了一个多月你的华丽人生呢。”Jessica的笑容在阳光下显得更加明艳,“话说回来,能被你这样利用,也算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了。”
林柏用手指挑起她的下巴,低声说:“能被你这样评价,是他最大的荣幸了。”
“你说,他会被判多少年?”
“至少……也是终身监禁吧?毕竟侵占资金一个多亿呢。”林柏说完,忍不住笑了出来,Jessica也笑了,两人依偎在一起,沐浴着地中海阳光。
*本文为通缉令13号文件榜首文章
作者 | 小狸奴
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本命武侠,爱好悬疑,偶尔情感。
___
故事续杯
马的马得马
关注茶点故事,点击“茶点图签”,
进茶点故事会领取丰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