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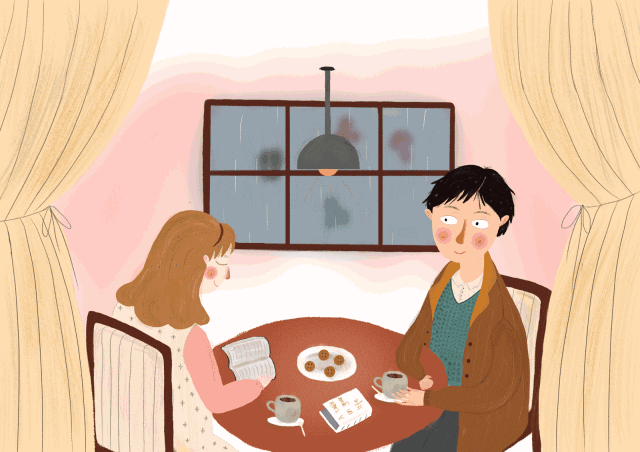

这两天,微博上一组数据触目惊心。
日本第一季度2万余人孤独死。

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今年1月至3月,日本有2.1万人在家中孤独死去,其中65岁以上老人为1.7万人,占总数近八成。
并且根据预测,日本全年65岁以上的“孤独死”人数或达6.8万人。

作为数一数二的长寿大国,日本老人的长寿却仿佛成了一种噩梦。
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那你有想过,我们的晚年生活又会是什么样?
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公园唱唱歌,练练八段锦?
是行动迟钝、头发花白,在幽闭的老房子里过着独居的生活?
又或是六、七十岁时还在四处打工,为自己积攒一笔养老金?
人都会慢慢变老,尤其是当看到体检报告上的红色箭头越来越多,还有身边太多养儿不防老的无奈后。
很多人的养老焦虑,开始提前了。
如何有尊严地老去?成了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难题。
 一种新型的
这是2019年,南京市政府率先推广的一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年轻人利用碎片时间为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例如陪诊、陪聊、代买菜、打扫卫生等等。
这些服务时长会被记录、存储下来,等未来自己老了需要帮助了,就可以换取相应时长的养老服务。
在@一条拍摄“时间银行”的视频中,23岁的陈馨怡,便是其中的志愿者之一。
高二那年,她的母亲和爷爷相继因病离世,见过了太多生命的无常后,她毅然决然加入“时间银行”。
她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担心自己万一将来不在奶奶身边,那就积攒多一点的服务时间,在未来“转赠”给卧床的奶奶使用。
于是一有空闲,她为半失能的老人理发、助洁、按摩、测血糖、量血压等等。
人到老年,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和被遗忘,无人关心,一无是处。
但在“时间银行”里,最常见的还是,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
詹宁辉今年62岁,她帮扶过的老人近百位,79岁的芮祥云便是其中之一。
芮祥云有一儿一女,长大后都分别离开了家,在外工作。
于是自从2010年丈夫去世后,芮祥云成了独居老人。
不仅常年与孤独为伴,还要忍受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折磨。
直到她遇到了詹宁辉,不仅给她送饭、陪她拿药、看医生。
有时候在外面犯低血糖,走不动路,只要一个电话,詹宁辉便会赶来载着她回家。
而对詹宁辉来说,自己现在身体健康,还有大把空余的时间。
对高龄老人的陪伴,既充实了当下的生活,也为自己储存起一份未来的免费服务时间。
这几年,“普通人要攒够多少钱,才能体面养老?”“存款100万不敢退休”的讨论,越演越烈。
然而当养老焦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压力,对普通打工人来说,“时间银行”无疑算得上一种投入最少、回报最高的养老方式。
这种以时间换时间,以服务换服务的模式,也给很多人带来新的思考。
一位老人坐在监控下的门槛,也许是预感自己将要离世,她手托着腮发呆,随后掩面哭泣。
根据我国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2.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4%。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的养老模式不再适用,无数现实告诉我们,大部分孝心抵不过现实。
多少子女,因为工作根本顾不上父母,在工作和现实之间,有心无力。
再加上,作为父母,我们也不忍心在养老的问题上拖累子女太多。
在矛盾与纠结之中,越来越多人探索出了各式新潮的养老观念。
在福建资国寺里,有一家新奇的佛教养老院,最低200元就可以入住。
老人们住在里面,既可以一起参加早晚课念经诵佛;也有师父教他们打太极、八段锦。
平时大家也会为寺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扫地、拔草、种菜等等。
但寺院养老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在于,设立了“生命关怀助念团”。
鼓励大家给临终的老人念经,陪他聊天,子女也围绕在床前。
这样的临终关怀,让逝者走得体面,也不增加别人的负担,生死两安。
杭州一位80岁的汪奶奶,邀请24岁的年轻姑娘媛媛,住进自己家里。
媛媛不需要交房租,只需要下班后陪汪奶奶说说话,照应彼此生活。
对媛媛来说,刚毕业的她省下了高额的房租,而汪奶奶也得到了想要的陪伴和看顾。
或是一群三观相近、生活能自理的老友聚在一起,过一种互相照应的集体生活。
在英国一个社区,26个大龄女性因为丧偶、离婚或未婚等原因,聚在一起共居。
平常一起看电影、做瑜伽,种果蔬,每隔一段时间还会一起聚餐。
老人们每天像普通学生组团去上课,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广东一位89岁的江敏慈奶奶,在老年大学学习拼音,学习电脑,学习视频制作。
目前,我国也在不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探索出了更多新潮的养老观念,有更多养老福利政策出台。
但说句实话,不管你想以何种方式养老,都避不开两个现实的问题。
人到老年,弯腰驼背、半口无牙不说,年轻时身体积累的坏毛病也开始显露出来,各种慢性病如影随形。
而有慢性病的人也更容易失智失能,到这时,养老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手头没钱,就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的底气,即使有儿有女,心里照样没有着落。
每个人都会老去,谁到老年都有说不清的事,解不开的题。
一种新型的
这是2019年,南京市政府率先推广的一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年轻人利用碎片时间为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例如陪诊、陪聊、代买菜、打扫卫生等等。
这些服务时长会被记录、存储下来,等未来自己老了需要帮助了,就可以换取相应时长的养老服务。
在@一条拍摄“时间银行”的视频中,23岁的陈馨怡,便是其中的志愿者之一。
高二那年,她的母亲和爷爷相继因病离世,见过了太多生命的无常后,她毅然决然加入“时间银行”。
她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担心自己万一将来不在奶奶身边,那就积攒多一点的服务时间,在未来“转赠”给卧床的奶奶使用。
于是一有空闲,她为半失能的老人理发、助洁、按摩、测血糖、量血压等等。
人到老年,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和被遗忘,无人关心,一无是处。
但在“时间银行”里,最常见的还是,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
詹宁辉今年62岁,她帮扶过的老人近百位,79岁的芮祥云便是其中之一。
芮祥云有一儿一女,长大后都分别离开了家,在外工作。
于是自从2010年丈夫去世后,芮祥云成了独居老人。
不仅常年与孤独为伴,还要忍受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折磨。
直到她遇到了詹宁辉,不仅给她送饭、陪她拿药、看医生。
有时候在外面犯低血糖,走不动路,只要一个电话,詹宁辉便会赶来载着她回家。
而对詹宁辉来说,自己现在身体健康,还有大把空余的时间。
对高龄老人的陪伴,既充实了当下的生活,也为自己储存起一份未来的免费服务时间。
这几年,“普通人要攒够多少钱,才能体面养老?”“存款100万不敢退休”的讨论,越演越烈。
然而当养老焦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压力,对普通打工人来说,“时间银行”无疑算得上一种投入最少、回报最高的养老方式。
这种以时间换时间,以服务换服务的模式,也给很多人带来新的思考。
一位老人坐在监控下的门槛,也许是预感自己将要离世,她手托着腮发呆,随后掩面哭泣。
根据我国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2.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4%。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传统的养老模式不再适用,无数现实告诉我们,大部分孝心抵不过现实。
多少子女,因为工作根本顾不上父母,在工作和现实之间,有心无力。
再加上,作为父母,我们也不忍心在养老的问题上拖累子女太多。
在矛盾与纠结之中,越来越多人探索出了各式新潮的养老观念。
在福建资国寺里,有一家新奇的佛教养老院,最低200元就可以入住。
老人们住在里面,既可以一起参加早晚课念经诵佛;也有师父教他们打太极、八段锦。
平时大家也会为寺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扫地、拔草、种菜等等。
但寺院养老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在于,设立了“生命关怀助念团”。
鼓励大家给临终的老人念经,陪他聊天,子女也围绕在床前。
这样的临终关怀,让逝者走得体面,也不增加别人的负担,生死两安。
杭州一位80岁的汪奶奶,邀请24岁的年轻姑娘媛媛,住进自己家里。
媛媛不需要交房租,只需要下班后陪汪奶奶说说话,照应彼此生活。
对媛媛来说,刚毕业的她省下了高额的房租,而汪奶奶也得到了想要的陪伴和看顾。
或是一群三观相近、生活能自理的老友聚在一起,过一种互相照应的集体生活。
在英国一个社区,26个大龄女性因为丧偶、离婚或未婚等原因,聚在一起共居。
平常一起看电影、做瑜伽,种果蔬,每隔一段时间还会一起聚餐。
老人们每天像普通学生组团去上课,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广东一位89岁的江敏慈奶奶,在老年大学学习拼音,学习电脑,学习视频制作。
目前,我国也在不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探索出了更多新潮的养老观念,有更多养老福利政策出台。
但说句实话,不管你想以何种方式养老,都避不开两个现实的问题。
人到老年,弯腰驼背、半口无牙不说,年轻时身体积累的坏毛病也开始显露出来,各种慢性病如影随形。
而有慢性病的人也更容易失智失能,到这时,养老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手头没钱,就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的底气,即使有儿有女,心里照样没有着落。
每个人都会老去,谁到老年都有说不清的事,解不开的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