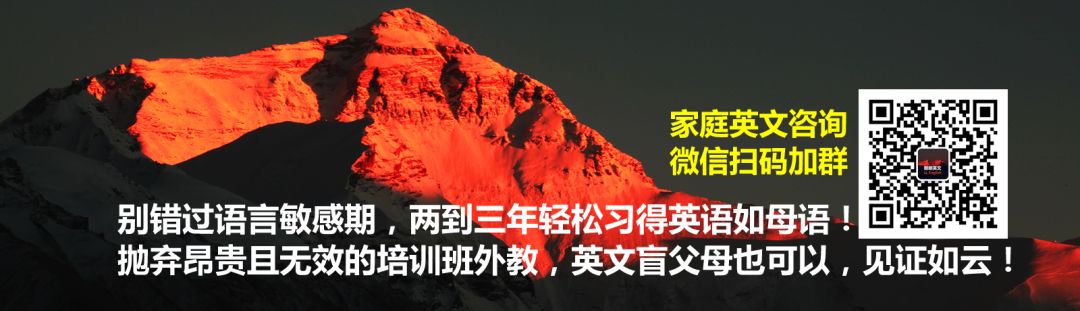
小编的话:
同一片蓝天,同一座城市,我们在抱怨生活和享受生活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关注到他们——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的未来。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他们发不出声音,因为他们不懂这个信息时代。他们就像是一群无声无息的机器,日日夜夜跟随着这个城市运转,永不停歇,直到生命枯竭......
因为家庭贫困,又没有什么特长技能,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他们只能每天拼命地卸货。这张照片更像是一尊底层民工的群雕作品。

这是某地钢厂附近的农民,他们没有什么特别技能,都是普通的农民,农闲时到钢铁厂做临时矿粉装卸工。
卸一吨矿粉6毛钱,一人一天最多的时候能卸300吨。每天能挣近200来块钱,总之,比种地挣的多。

工人们正在大车上卸货。

赤膊卸货的工人。

一位工友的后背上布满了汗水留下的痕迹。

这些卸货的工人,年纪最大的已经60多岁了,因为家庭贫困,又没有什么特长技能,为了家庭他们只能每天拼命的卸货。

水壶里的水看着有点污浊,炎热的夏天工友们身体的盐份会随着汗水快速的流失,为了保持体力大部分工友会在水壶中放些盐巴。

卸完货以后,一位工人在一个污浊的水坑里洗脸降温。

一帮工人卸了半天几百吨货,每人能分到几十块钱。

工人把挣来的钱放在塑料袋中保存着,以防汗水把工钱弄湿。

工友的“黑脚”和工鞋。

一位工人在展示他的双手,在一次装卸货物的时候,手指被割掉一节。

工人们的合影,这里有几位已经去世。

在北京北三环外的一个住宅小区深处,藏有一群特殊的“居民”。这是一个包工队租下的民工宿舍,是用冷库改装的简易工棚。100平米挤了50个人的集体宿舍犹如一个大集市,用布帘子遮挡床铺,形成各自的私密空间。
这个工棚并没有像其他民工宿舍一样与市民隔绝,而是与居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区,但因为脏乱的环境与阶层的差距,他们与居民交流甚少,一种无形的疏离感笼罩着这个空间。工棚内外是两个世界,他们每天早出晚归,跟周围人几乎没有接触,这100平米的小圈子就是他们的生活。

北京北三环外,清晨一位刚起床的民工,点上了一根香烟。

北京北三环外,民工难熬的起床。每天清晨七点钟必须准时上工,而五六点钟起床对于这些十九、二十出头的年轻民工来说却是最难熬的时刻。

北京北三环外,工人在厕所洗浴。工棚四五十号人只有一个小小的厕所,里面没有淋浴设备,只有冷水,满面尘土民工们回来连个澡都洗不上,只能接盆冷水,擦擦身子。

北京北三环外,照照镜子,打扮一下自己。

京北三环外,工人们中午开饭了。每天中午开饭的时刻是最热闹的,从一大早忙碌了一上午的民工们,早已是饥肠辘辘了。争先恐后地端着硕大的饭盆去打饭,食量对于城里人来说简直有点惊人,吃四五个馒头是很平常的。只是时下,肉价已经十几块一斤了,饭菜里少见的是荤腥,最常见的菜式是西红柿打卤面和土豆丝就馒头。

北京北三环外,打过饭以后,民工们多与自己相熟的,三五成群地坐在工棚里或是工棚的附近一起吃饭。

北京北三环外,休息,玩会儿斗地主。

北京北三环外,劳累一天可以睡了。一间屋子里挤满了四五十个每天从事重体力劳动,且没法洗澡的工人,空气中定是弥漫着“可观”的味道。还好大家白天劳动都很累,容易睡的着。

北京北三环外,中午躺在床上休息的工人。

北京北三环外,年轻的民工会像孩子一样在一起玩乐打闹。

北京北三环外,工棚里部分民工的合影。

在浙江义乌市一个小镇里,散落着一批家庭作坊式的纺织品工厂。每到上班时间,一群学龄前的孩子就会跟着父母来到车间。
年轻的父母们舍不得将孩子留在老家,便带着孩子出来上班。 这些孩子虽然不像“留守儿童”那样长年见不到父母,却面临着父母无暇照看的尴尬。
虽然工厂车间存在各种安全隐患,但他们的父母也别无选择——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没人照看。送到学前班,又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学费,他们负担不起。

浙江义乌某纺织工厂,三名孩子在墙角的布料堆上打滚嬉戏,他们的父母正忙着干活。

浙江义乌某纺织工厂,一名母亲带着还没断奶的孩子来上班。孩子饿了,坐在工作台上大哭。

浙江义乌某纺织工厂,年轻的母亲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给孩子喂奶。边上的工友也伸手抚摸孩子的头部,帮忙安抚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