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今天想不出推送什么主题,
所以一直拖延到现在才发…
不过,其实也跟下班路上买了个冰激凌吃有关,
(好像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
因为有句话说得好:
每天下班后购物就会有好心情,是因为逃离职场回家的途中,我们走进市场,在那里可以忘掉自己是谁。或者说,在这里能感知“真正的自己”。

这话可不是我随口瞎说的,而
是来自真正的学术著作哦:
西方的经济人类学,或日本
的中世纪史研究都发现,
市场,曾是与现世秩序“无缘”的“公共世界”,是“乐土”之一。
假如严格禁止下班之后的“血拼”会怎样?
购物狂说:
下班不顺路去市场转一转就活不下去
。
那么,若将人与神圣领域切断又会如何呢?
19 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
涂尔干
说:倘如此,
人就会因丧失能量之源而死去
。
而除了个人的悲剧下场之外,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和国家又会怎样?
现代社会,就是在
关系不断被金钱取代的“大道”上狂奔的社会。在自己种菜吃,四邻互分互享的社会,因作物与服务不在市场中交易,
GDP 就会降低
。只要种的菜不是吃而是卖,也不再与邻里分享,大家都到外面就餐,
GDP 就会上涨
。
较之在家里和睦相处,到游乐园吃喝玩乐,购买礼物,并为获得所需金钱而挣取劳动工资,GDP 会更高
。
最
后:
人,不与“超越
自我之境”相联通,活着是很痛苦的。
好啦,说正经的。上面这些话真不是我瞎说的,而是整理自日本当代重量級社会思想家
小熊英二
作品
《改变社会》
第四章
《何谓民主主义》
中的
《祭祀与音乐的世界》《王、祭祀与市场》《涂尔干的“自杀论”》《超越自我之境》
这几个小节。
应该说,这本
《改变社会》
是小熊英二用来讨论
“今天的日本到底在发生什么?所谓的改变社会到底是指什么?”
等严肃社会话题的,但有趣的是……就是读起来很有趣啊……
以下与大家分享还是出自
《何谓民主主义》
中的一段,读完之后,您大概能明白,之前美国新任总统在宣誓就职后,对媒体报道
“这届人民不行”
(现场观礼人数大大少于上一届总统就职典礼)而大发雷霆了……
对了对了,在上周四的
王澍
老师文
章
《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点
击标题可以回看)下面留言的朋友很多,而且质量很高,觉得很欣慰。公布下获得好基友之一
浦睿君
提供的
王澍老师作品《造房子》
的四位幸运读者:
R's、王梓煦、方羽夕、Sailing
。老规矩,还请发来您的真实姓名、地址、邮编、手机号。
重要的是“群情激奋、万众沸腾”
文|
小熊英二
译|
王俊之
摘自|
《改变社会
》
- 声明:如需
转载先请私
信联系
-
简单类推虽为学术禁忌,但古雅典公民大会所呈现的应该也是这样的情景。这里的军刀,既是作为民兵集合时佩带的武器,也是成年男性或一家之长的象征。即便是今天,剑、玉、镜等仍在日本天皇家世代相传,王子成人后授之以魔剑的故事也很常见。也就是说,持有此刀的人,拥有参加大会的资格。
此外,公民大会也是一项宗教活动、节日盛典。所以,神职人员一定会出现,也一定要在神殿前举行。在欧洲的市和区,中心必有广场,广场周围也必有教会及政府。在政教合一的“政务”之所,所有人集汇于一处。因田间村落没有娱乐,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还是与亲朋好友久别重逢,欢聚叙旧的地方。
进而,大会虽有争论,但重要的不是将对方辩倒,而是要“争”得所有人欢欣雀跃。热闹之后当然会有个结论,但若只为收集个别意见,那就毫无特意汇集于一处争论的必要了。像舆论调查一样,在纸上或邮件里打钩划叉,收上来就行了。
就像日本今天的议会,既然“争论”也不过是个形式,舆论调查的方式反而更有效率。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非要唇枪舌剑一番不可呢?究其原因,虽易于理解为交换意见非常重要,但实际就是若非如此,“大家就不认同”。
那为什么论战一番“大家就认同”了呢?因为,议会中有了“我反对!”“我这样想!”的激烈争论,现场就热闹了,就要举手表决。在这里,不是将选票丢进投票箱,而是以当场呼啦啦举起手来为好。有了这一“仪式”,就不是收集个别意见,而是宣示神圣的“民意”。一旦体现出这样的“民意”,就会认为这是“超越了个别意见”的“神意”的降临。所以,要在教会或神殿前举行这一点就很重要,大家也会认同并服从。接下来就成了大团圆,以看热闹的方式参与的女人、孩子也同饮同唱,携手起舞,参与到这一“民主主义”之中。
至此,古希腊公民大会为何要在神殿前举行,雄辩术(rhetoric)为何受到重视,等等,也就多少能理解了。
在此,论辩先按下不表,一起来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游行示威。游行示威,日本称之为 DEMO,既是 demonstration(游行示威)的 DEMO,也是 democracy(民主政治)的 DEMO。而其词源,则是古希腊语的 demos(民众) kratos(支配),即现代语境中的民众力量people's power。
对people's power来说,重要的是全体参与者的高涨情绪。即便是人数一样的游行,一支队伍生机勃勃,另一支只为拿到按日支付的补贴,得到大家认同的程度自然也不同。所以,可以说,活泼开心、意气昂扬,这才是游行示威的本来面貌。
那么,为什么游行示威中蕴含着改变社会的力量呢?即便是10万人的游行,也可能被认为“不过是一群怪人”,“不过是比例代表选区一人当选的人数”。但是,尽管人数不多,一旦被认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的意见”,“他们的呐喊也表达了我的愤怒”,其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就完全不同了。这与是否打出“负责任的政策性替代方案”基本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很多人。有时,哪怕只是一个人的行动,一张照片,一首短诗,也能产生莫大的影响。远在古希腊时,诗人就曾被视为神的意志与民众意志的“代表”。所以,政治家才会惧怕诗人。如现代日本的政治家,最终最为在意的,也是“后世史学家会如何评价自己”。
当然,这里所说的诗人,也不是为“自我表达”而吟。若仅是自我表达,就未必能打动他人。
但将在后文中介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在现代社会,因“个人宗教”,即“必须尊重个人”这一集体意识的形成,个人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若是基于这一理论,自我表达之能打动别人,要么是因其自我尊重的姿态让他人产生了“自我尊重”的共鸣,要么是表达者将“现世幸福”或“世俗”尽皆抛弃,彻底践行“自我表达”,完成了对“现世之我”的超越而令世人动容。
辩论的意义
至此就能明白,所谓“民主主义”或者说“合法性”,并不是单纯的“大家投票即可”。民意并非数量所能代表,人们不会只因票数就会认同。
比如,即便是现代日本,报纸等经常叹息“议会审议气氛沉闷”,“选举死气沉沉”。可为什么审议、选举就非要气氛热烈?审议在严肃的气氛中按程序进行,选举中没有暗箱操作,候选人A最终以多少票当选,又有何不可?为什么不热热闹闹地折腾一番,大家就不认同呢?
对此,现代思维是这样解释的:选举气氛若不热烈,投票率就会下降,就由一部分人来决定代表了。而若审议中没有激烈争论,政策、法案中的问题就得不到充分的指正。所以不折腾就是问题。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若只为指摘政策、法案中的问题,召集专家指摘就行了,人数少议论更为彻底不说,几百号门外汉议员堆到议会里又能议论出什么结果?既然如此,也没必要投票,更不需要议员,直接让专家们集中管理国家事务,最多只要履行“民主主义的程序”就可以了。
到底是现代社会,没人明目张胆地如此宣示。但是,去翻翻外交官回忆录,你就会发现真有人这样想。外交官与外交部官员使七十二般变化、费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谈成的条约,达成的共识,却被啥都不懂、突然半路杀出的外行议员或首相给彻底搅黄,或就在签字生效前一个月,爆发了无知民众的反对运动,于是前功尽弃。这些记录中,不乏令提笔者扼腕叹息之事。专门研究外交史的学者,因读的都是这类书,有时也会被这一立场同化。
现代思维认为,因专家会为自身利害所动,所以也会成为问题。那么大家都去投票,或只要把投票率提上去,人们就会认同吗?学校的班长推选投票率高达100%,可学生们未必会接受选举结果。
由此看来,重要的还是要有一番激烈的争论。有了激烈的争论,参与的热情就会高涨起来,就会感觉是“大家一起决定的”。也可以说是“大家一起干的”。没有这个“大家”,没有“也有我一份儿”的感觉,人们就不会认同。也就是说,所谓热烈的争论就是营造一个“大家”,一个“我们”。
如此想来就能明白,“示威不如投票”“不如去游说政治家”等想法非常狭隘。当然,有靠投票和游说才能运转的东西,所以投票和游说也确有其存在的必要,但若仅有这些,政治就会越来越无聊。
并且,即便去投票或游说,社会也往往不为所动。社会要动,就只有一种情况,即被选或被游说的政治家,真被视为“我们的代表”,而该政治家的决定大家又跟随其而行动的时候。当民众不再认同并跟随其行动时,就只能依靠金钱或利益维系了,但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陷入不认同者越来越多的恶性循环。
祭祀与音乐的世界
那么,要将神的意志示于尘世,要与神圣世界沟通,又该怎么做呢?
方法之一便是祭祀仪式,也就是“政治”。若由“代表”聚于一处举行,这就是代议制。也就是说,将民意这一肉眼不可见之物,以人类的方式呈现于世的人,就是“代表”。
并且,在举行祭祀仪式的“政务”之所,音乐、表演剧等也不可或缺。音乐是将尘世不可见之物呈现于世的重要方法。在印度尼西亚,皮影戏非常受重视,这是因为,皮影戏在“反映”和“代表”真实世界方面,被认为远在现实世界之上。正如大家所知,在古希腊,戏剧也很繁盛。
若世间万象不过是神的语言的重复与再现,那么,展现诸神世界更为出色的戏剧也就成了“真实世界”。如此尘世,也就不过是戏剧上演的“真实世界”的重复和再现。所以,在有这一社会共识的国家,若上演推翻政权的戏剧,会被视为比游行示威还要严重的反政府行为,而上演一方,也将戏剧视为重要的社会运动。
作为其他方法,也会请诗人、巫师,让神的意志降临尘世。成为诗人和巫师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人类学、宗教学的调查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看法是,俗世中最无用的人,能与神界沟通。
因俗世为劳动与家庭的领域,所以,俗世中最无用的人,就是既无劳动能力又无生育能力的人。比如,瞎眼的婆婆、初潮前的少女等,经常会在各种仪式中司以通灵之职。平时无用的笨蛋,以意想不到的超凡力量与智慧救全村于危难的事情,在民间故事中也经常出现。因这样的人不能自食其力,所以,一般是靠他人“布施”为生。
一言以蔽之,该意见认为,不脱离俗世,就听不到神界的声音。所以,要做和尚,就必须离开经济与生育的世俗领域,即 oikos(也就是家庭)的领域去“出家”。因女性很难逃脱生殖的必然,圣职者就多是男性了。可以认为,圣山禁止女性进入,月经中的女性尤被视为禁忌,也是源于这一认识。
至此,我们就能明白,在古希腊,为什么会将 polis 视为“自由与永恒的领域”,而将 oikos 视为“必然与无常的领域”了。polis 的世界,即脱离了“私”的利害关系的神圣的“公”的领域。在这里讨论公共事务,唱诗赋曲,表演戏剧。就人类学等迄今探明的范围而言,人类,若不在某处与此一领域相通,似是活不下去的。或许因为,若只有必然领域,人们会过于痛苦吧。
于是,越接近神圣的自由领域的时间,人们就越加重视,越接近这一领域的人,地位也就越高。在古希腊,没有劳动者了不起的价值观。劳动者是低贱的,从事劳动的奴隶也无法进入 polis 的领域。即便在近代,依然认为劳动者没有学习时间,搞不懂政治,所以就没有参政权。但相对于这一解释,可以认为,是仍将劳动视为俗世无常领域的无聊之事而已。
在古希腊,劳动是最为卑下的活动。而与 polis 相关的统治则更为高贵。地位更高的,这就是日译为“观照”
(佛教中指以智慧直击事物本质;而美学中则对应英语、法语中的 contemplation ,指面对审美对象时比理论思维更为深邃的直觉。译者)
的人类活动,即无关于现世经济、政治的思想探索。从事这一活动的一般认为是哲学家,但对东方人来说,说是和尚可能更好理解。
20世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犹太人,美国政治理论家,原籍德国,以极权研究著称。译者)
在《人类的处境》一书中,以古希腊思想为基础,将人类行为划分为“劳动”“工作”与“行动”。这里的“行动”虽是上面所说的统治,但较之于躯壳式政党政治或行政事务,阿伦特所重视的是政治参与、政治活动等。考虑到古希腊是直接民主主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阿伦特不但高度评价19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
(指二战以后,美国黑人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其高潮发生于1960年代。译者)
,就连她本人,也有逃离纳粹统治,在法国投身反法西斯运动,并亡命美国的“行动”经历。
而汉娜所说的“工作”,则是指能长留于世的神殿、碑塔等的建造。哲学家、公民大会等听授神的意志,并施行将之体现于世的统治,但作为将神的意志体现于人世的行为,神殿及艺术作品的建造、创作等,地位也要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劳动与家务的成果是吃了就没的无常之物,但神殿却会矗立数百年甚至几千载。但是,地位最高的,还是从事卓越的“行动”,而被诗歌万世吟咏。即便刻写诗文的石碑消失,其本身也会永世流传。
(完)
本文选自

《改变社会》
[日] 小熊英二
|著
王俊之
|
译
日本当代重量級社会思想家作品,中央公论新社新书大奖第 1 名。
社会会改变吗?又如何去改变?投票,选出议员、政党,通过法律……这一切不过是诞生于 18 世纪至 19 世纪的近代代议制民主主义思维,若死报不放,思路未免狭隘。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在回答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今天的日本到底在发生什么?所谓的改变社会到底是指什么?而这本书,就是要从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或思想的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
如您对这本
《改变社会》
感兴趣,试试
长按下图二维码
或戳文末
阅读原文
即可买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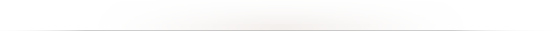
上
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
stphbooks
”添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