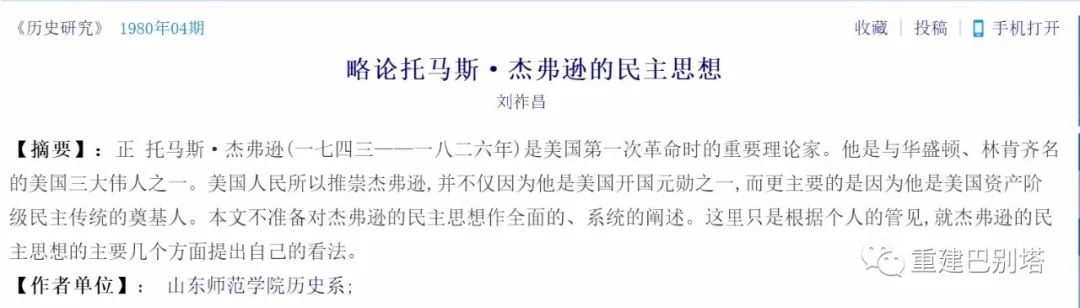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是美国第一次革命的重要的革命理论家和代言人之一。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与华盛顿、林肯齐名的美国三大伟人之一。美国人民之所以如此推崇杰斐逊,并不是因为他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而是因为他是美国民主传统的奠基人,他的民主思想始终是美国人民争取进步的推动力量。
本文不准备对杰斐逊的民主思想作全面的、系统的阐述,因为一则是篇幅所限,二则是外国特别是美国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已经作出大量的工作。这里只是根据个人的管见,就杰斐逊的民主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加以初步的探讨和论述。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多加指正和批评。
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对压迫者的无比仇恨
对人民群众抱什么态度?这是杰斐逊与当代美国资产阶级政客特别是联邦党政客之间的重要分水岭。
联邦党领袖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轻视人民、仇视人民方面要算最典型的了。他辱骂人民是“野兽”,说人民群众没有统治能力。[1]他曾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大言不惭地宣称:“一切社会都分为少数人和多数人。前者是富有的,出身名门的,后者是人民群众。……人民狂暴而变化无常。他们的判断和决定很少是正确的。因此,应该使前者在政府中享受一个显著而永久的地位。他们会制止后者的不稳。只有这样一个永久性的团体才能抑制民主的轻举妄动。”
与汉密尔顿相反,杰斐逊对人民群众有无限的信心。首先他深信普通人民的善良和判断能力。1813年1月13日,在致约翰·梅利什的信里,他写道:“他(指华盛顿——引者注)和我之间的唯一意见分歧在于:我对于人民的天赋完善和判断能力,比起他来,有更大的信心。”[2]他主张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因为他相信人民群众有自治和管理国家的能力。[3]1823年10月31日他在致科里的信里表示:“人民,特别是当他们受到适度的教育时,是公众权利的唯一可靠的保管人(因为他们是唯一正直的),因此应该参加统治,担任他们胜任的职务”。[4]在给法国重农学派尼摩尔的信里他写道:“我们两个人都爱人民,但是你把它当作幼儿加以爱护,没有保姆你是不相信他们的,而我则把他们看成是大人,他们统治自己我是放心的。”[5]在他看来,普通人民的常识比起贵族的偏见更值得依赖。只有那些想利用政府权力剥削劳动人民来肥己的人才有理由害怕人民。他说:“我就不害怕人民。为了继续保持自由,我们应该依靠的是他们,而不是富人。”[6]
杰斐逊也承认人民群众有时也会偶然犯错误,但是他们“决不是故意的和怀有推翻政府的自由原则的有系统的、坚定不够的目的。”[7]他还认为即使人民有欺诈行为,那么这种欺诈行为所引起的弊害,也要比“人民的代理人的自私所造成的弊害更小。”[8]针对一些人关于人民愚蠢和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的谬论,他发问道:“有时据说人在管理自己方面是靠不住的。那么他在统治别人方面是靠得住的吗?”[9]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总比少数人的意见更合乎正义。[10]
联邦党人要求让“有财产、有原则的”资产阶级贵族分子管理国家,但是杰斐逊对于富人抱轻蔑的态度,他说:“我从未见过人们的正直随着他们的财富的增加而有所增加的。”他还认为所谓“上等人”是扩大社会正义的主要障碍,过去之所以愚昧,是因为过去曾被拥有财富有原则的绅士所操纵,他们使政府远离人民,掠夺纳税者,并且从事战争,造成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他认为即使承认人民是野兽,那么野兽的政府也比过去的主人与奴隶关系为好,更何况人民并不是野兽。[11]
在广大人民没有受教育并且被视为“劣等人”的美国开国时期,杰斐逊能够对人民的能力和品德有无限的信任,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事。对于人民大众无限信任的另一方面,便是他对压迫者的无比仇恨和蔑视。
首先,杰斐逊对于专制君主及贵族僧侣的专横跋扈是深恶痛绝的。他在寓居欧洲期间,目睹广大劳动人民在国王和贵族教士的折磨压榨下的悲惨情景,这更加深了他对于封建压迫者的仇恨。1786年8月13日他在给乔治·威思的信里写道:“……在这里(法国——引者注),尽管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土地,天底下最好的气候,最善良的人民,最快活可爱的性格,然而我可以说这样受自然嘉惠的人民,却被国王、贵族及教士(而且只是被这些人)折磨得悲惨极了。”[12]更使他气愤的是,他发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欧洲君主往往是些白痴。他说:“路易十六是一个愚人……西班牙国王是一个愚人。……葡萄牙国王……天生就是一个白痴。丹麦国王亦是如此。……普鲁士国王……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都和猪一样……这些动物变成没有思想和体力衰弱的人;每一个世袭君主经过几代之后都会如此。”[13]他又指出:“即使从这一天起一直到最后审判那一天止产生于我们共和制政府的全部弊害,与这个国家(指法国——引者注)在一个星期内在君主制下面所蒙受的苦难相比,后者也会大得多。”[14]他进一步指出:“在统治的借口下,他们(指欧洲封建统治阶级——引者注)把他们的国民分为两个阶级——狼和绵羊。”在法国,“每一个人不是铁鎚就是砧石”(意即不是压迫者就是被压迫者)。他又说:欧洲封建统治阶级就是“食人的动物”,“对于欧洲政府及掠夺穷人的富人,我不能用更柔和的字眼”。[15]
杰斐逊特别憎恶基于世袭特权的贵族等级制度,认为这是人为地造成的不平等。他说:在欧洲封建等级制度下面,“人的尊严在人为的差别中丧失了,在这里,人类分成高低不等的几个等级,在这里,多数人在少数人的压迫下受痛苦。”[16]他不但仇恨封建统治者,而且也仇恨一切形式的暴君和压迫者。他从内心里痛恨拿破仑,因为他认为拿破仑是蹂躏人民自由的专制独夫和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杀人魔王。他在许多文件和书信中严厉谴责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有时说他的统治是“军事暴政”。[17]有时说它是“无原则的疯狂的暴政”,[18]或者“军事冒险家的篡权。”[19]因此,他坚决反对在美国建立独裁制度的一切企图,他警告说:万一在美国出现个人独裁的暴政,一切为了争取自由而参加独立战争的人,都“一定会感到困惑和沮丧!”[20]他痛恨暴君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在自己的图章上刻上了如下的格言:“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21]
应该指出:杰斐逊之对君主制的深恶痛绝,主要是早年的事,到了晚年他稍稍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君主制是最可取的政府形式。[22]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对压迫者的无比仇恨的立场,是杰斐逊全部思想的基础,也是他的民主思想的出发点。
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革命权利
自然权利学说早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就被提出来了,经过17世纪英国平等派思想家、资产阶级新贵族思想家(特别是约翰·洛克)以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发扬,到18世纪末已经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了。在独立战争前夕,自然权利学说也在美国广泛传播,并且深入人心。
按照这个学说,在成立政府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他们只是服从“自然法则”,而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一切人都享有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是生来就有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自然权利学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非同小可的革命,因为它的锋芒是直接指向中世纪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大胆的否定。众所周知,在专制制度下面,人们是不平等的,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而贵族和僧侣却高高在上享有很多的特权。统治阶级草菅人命,任意践踏人民的自由,人民不但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且也失去了独立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23]
但是自然权利学说一出,就像一颗重磅炸弹一样,从理论上摧毁了专制主义存在的基础。这是因为,按照这个学说,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是自由、平等的,而这些权利是大自然所赋与的(或创世主赋与的,意思完全一样),而不是人世间哪一个权威“恩赐”的,也不是人民从统治者那里乞求来的。正是因为它是自然所赋与的,所以它是不能被剥夺的,也不能让渡给任何人。因此,自然权利学说一下子提高了人民的地位,承认了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更不是任何统治者手中的“刍狗”。正是这个自然权利学说被杰斐逊全盘接受下来了。
杰斐逊早在1770年就公开说过:在自然法则下面,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24]这是他关于自然权利的最早的言论。后来到1774年他在他所提出的《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这个文件中又谈到自然权利,他指出:人们的权利“来源于自然法则,而不是他们的国家元首所赐予的。”[25]但是只有到1776年在他所执笔草拟的《独立宣言》原稿中,他才对自然权利学说作了正面的阐述:“我们认为下面这个真理是神圣的和无法否认的:人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和独立的,因而他们都应该享有与生俱来的,不能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6]
杰斐逊的这句名言显然脱胎于约翰·洛克的学说,因为洛克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都被自然赋与某些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及财产权利。但是杰斐逊却没有照抄这个公式,他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阐明了自然权利学说,更重要的是他用“追求幸福”的权利去代替洛克的“财产权利”。用“追求幸福”的权利取代“财产权利”并不是简单的几个字的问题,而是在一个带有原则性的大问题上他与洛克分道扬镳了:洛克站在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立场上竭力维护私有财产制度,而杰斐逊则突破了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而把广大人民的渴望和要求反映到自然权利学说中来。这样一来,他就赋与自然权利学说以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学说。
在发表《独立宣言》之后,随着时代的前进,根据斗争的需要,杰斐逊又一步一步地充实了自然权利的内容。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杰斐逊正在任美国驻法公使。当时他的老朋友拉法叶特为法国国民议会起草了一部“人权宣言”,在草稿里拉法叶特在列举人民的自然权利时,把“财产权”加了进去。当他向杰斐逊征求意见时,后者建议把“财产权”删掉,另外加上“生命权”、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的权利、发挥个人才能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抵抗压迫的权利。[27]在另一个场合,杰斐逊还强调,“选择他认为最能给他以舒适生活的那种职业”,也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28]这样,杰斐逊不仅继承了前人关于自然权利的学说,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它,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其摆脱了资产阶级局限性,而更带有人民性。而且,他是第一个把自然权利学说写进官方文件中的人。但是,杰斐逊并没有停留在自然权利学说上面,他以自然权利学说为出发点,进一步发挥了人民主权论的思想。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里,在列举人民的自然权利之后,紧接着便指出:“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29]这就是说: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最高主权者。这样,他就言简意赅地表述了人民主权思想。当然,人民主权思想也不是杰斐逊首创的,它的历史和自然权利学说同样悠久。但是,杰斐逊却有他自己的贡献:第一,他把这个思想用朴素的语言写进《独立宣言》这个重要的历史文件中去,使其成为指导美国人民和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一句话,杰斐逊把人民主权的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了。第二,他使这个学说的内容更具体化了。1793年他写道:“我认为组成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的一切权威的来源;他们有靠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代理人来处理他们公共事务的自由;有撤换这些代理人的个人或他们的组织的自由,在他们愿意的任何时候。”[30]这里,他不仅重申人民主权思想,而且讲明人民应如何行使主权。1820年,他又写道:“我除了人民自己以外,不知道有任何一个社会的终极权力的安全的保存者;而假如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不足以使他们用健全的辨别能力行使他们的管理权的话,补救之道并不是把它(指权力——引者注)从他们手中夺走,而是用教育去改进他们的辨别能力。”[31]这里,他又指明了人民无力行使主权时的补救办法。
杰斐逊不仅对于人民主权学说作出了以上贡献,而且他还是终生忠于人民主权学说的,1824年苏格兰人达维德·休谟发表文章攻击“人民是一切公正政权的源泉”的原则。当时,杰斐逊以垂老之年,愤怒地斥责了休谟,他问道:“这个背叛自己同胞的学术界败类(指休谟——引者注)如果不到社会上大多数人中间去寻找公正的权力的来源,那么他到哪里去找呢?它来源于少数人吗?或者来源于这些少数中间的个别人吗?”[32]
人民主权思想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推翻了中世纪以来盛行的“君权神授说”,把国家权力的来源从上帝手中转到人民手中。杰斐逊之大力宣传这个人民主权思想,是他的不可泯没的功绩之一。
以自然权利学说及人民主权思想为基础,杰斐逊又深入地论证和发挥了关于人民的革命权利的理论。在他看来,既然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既然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那么一旦政府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侵犯人民的权利并且开始压迫人民的时候,人民就理所当然地有权利举行革命或起义来推翻这样的政府。
杰斐逊关于人民的革命权利的思想,首先发表在《独立宣言》里。他在这个《宣言》里宣布: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如果遇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个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当一个政府在一个时期开始实行的一连串的暴政和倒行逆施(并且一成不变地追求同一个目标)表明它决心要把人民放在绝对专制权力的淫威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且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33]
这样,杰斐逊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布人民有革命的权利,他们有权利用革命手段推翻压迫人民的政府。当然,人民革命权利的思想也不是杰斐逊首先提出来的,在早于他一百年前,洛克就提出了这个思想,但是杰斐逊第一个把这个思想写进官方文件里,并且在美国人民反英斗争方兴未艾之际宣布了这个思想,这就使这个理论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对于激发美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力来说,起了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
在独立战争结束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特别是在谢斯起义失败后,杰斐逊不仅捍卫了这个思想,而且还热情洋溢地歌颂革命。他写道:“让他们(指人民——引者注)拿起武器吧!……在一两个世纪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自由之树必然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灌溉。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的肥料。”[34]他又写道:“……我们的确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单凭理性而不流血地改革政府的美好的榜样,并且以此而自豪。但是世界太受压迫了,所以不会从这个榜样中得到好处。”[35]
由于杰斐逊有了这个思想,所以在1789年震动全欧的法国大革命轰然爆发后,他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法国人民的英雄业绩。1793年1月3日他在一封信里毫不含糊地表示同情法国人民在雅各宾党人领导下废除君主制的划时代的伟大举动,并且赞许了巴黎人民镇压反革命的行动。他虽然为一些无辜者死于革命者之手感到惋惜,但他同时又指出:“全世界的自由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果,曾经有过用如此少的无辜者的血赢得的奖品吗?我自己的感情由于这个事业的某些殉难者而受到挫伤,但是我宁愿看到半个世界遭到破坏,也不愿它失败;即使每个国家在保存自由时只剩下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也比现在更好。”[36]他在欢呼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也为法国大革命进行辩护。1793年1月3日他写信谴责威廉·肖特,因为后者曾“责难法国雅各宾党人的举动。”[37]
杰斐逊之所以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因为他看到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宣布的原则,也在法国胜利了。他写道:“在美国进行的诉诸人权的行动,也在法国开始了,而且在这方面法国走在欧洲诸国的最前头。”“我认为法国政府的成功的改革,保证了欧洲的普遍改革及现在备受暴虐无道的统治者折磨的欧洲人民的一个新生活的开始。”[38]
杰斐逊不但强调人民的革命权利,而且还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在谢斯起义失败后,他不但指出人民定期举行暴动的必要性,而且认为人民之有反抗精神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培养和发扬这种反抗精神。他写道:“……但愿我们每隔二十年发生这样一次起义。”他认为定期举行暴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民可以通过暴动来警告统治者:人民是不可侮的,这样就会使统治者有所顾忌,不敢为非作歹,不敢继续侵犯人民的自由。[39]他又写道:“我喜欢时常发生一点儿叛乱,它好像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40]在谈到自由制度时,他写道:“我宁肯喜欢会引起危险的自由,也不愿意有平安无事的奴隶制”。[41]杰斐逊关于反抗精神的言论,可以说是发展了关于人民的革命权利的理论。
杰斐逊这些大胆的言论,在当代美国资产阶级社会里真可谓“惊世骇俗”的了,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许多人的反感。甚至他的传记作者约翰·马士也认为他的这些言论是“愚蠢的”。[42]但是,这里应该弄清两个问题:
第一,杰斐逊虽然主张人民有举行革命或暴动的权利,一再歌颂革命,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暴动的煽动者。约翰·马歇尔的传记作者把杰斐逊说成是一个人民叛乱的煽动者,是对事实的歪曲。杰斐逊的传记作者马隆的见解是正确的,他认为杰斐逊有关革命或暴动的言论,一般都不是直接对人民群众讲的,而是私下对统治阶级人物讲的(往往是私人通信),他既没有号召人民起来暴动,更没有直接领导人民起来暴动。[43]谢斯起义时,他正在法国。
第二,杰斐逊到晚年已不再坚持革命的权利的思想了,而且公然反对过火的革命行动。他这个态度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特别显著。他在1815年2月19日致拉法叶特的信里写道:法国共和主义者不满足于建立君主立宪制,而要求实行更进一步的改革,“……法国国民接着所蒙受的苦难及罪恶,都来自共和主义者这个改革的错误;来自他们和你本人及立宪派的分道扬镳……结局,用他们所取得的有限制的君主制换得了罗伯斯庇尔的无原则的、血腥的暴政以及波拿巴的同样无原则的和疯狂的暴政。”[44]1817年杰斐逊又强调了这一点,他在致法国朋友马尔布阿的信里写道:“当我在1789年末离开法国时,你们的革命,在我看来,是在有能力的正直的人们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们的疯狂,其他人的恶德”等等“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可悲的时期。”[45]到晚年,杰斐逊在自传里又写道:“我们应该把[法国]王后幽禁在一个修道院里,使她的权力不致为害,并且把国王放在他的位置上,授以有限的权力,我相信这个权力他是会按照他所理解的程度老老实实地行使的。这样就不会产生招致一个军事冒险家(指拿破仑——引者注)的篡夺的王位空虚,也不会有机会使这些穷凶极恶的行为蹂躏世界诸国并且毁灭它的几百万生灵。”[46]因此,菲利普·方纳教授认为杰斐逊“并没有对‘过度的民主’(亦即过火的革命行动——引者注)感到不愉快”,[47]是不合事实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但是,不管怎样,杰斐逊所宣扬的革命的权利的思想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夕世界广大地区人民在封建专制的暴政下呻吟的时候,杰斐逊之关于人民的革命的权利的呼声,的确起了发蒙启聩的作用,它不仅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而且也推动了欧洲及拉丁美洲的革命。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认为“在独立宣言中宣布的与生俱来的、普遍的革命的权利的观念”,是美国对于人类文明的十大贡献之一,而且是首要的贡献。[48]这个说法虽然未免有些夸大,但是也说明了一定的真实情况。
社会经济改造方案
杰斐逊不但以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平等为己任,而且也梦想建立一个社会上和经济上相对平等的、没有剥削的、以小农为主体的社会。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他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方案:
(一)铲除“人为的贵族”,用“自然的贵族”取而代之
杰斐逊本人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他最看不起贵族。他认为当代美国的贵族是以门第和财富为基础的,并且称他们为“人为的贵族”。他说:这样的贵族“既无道德,又无才能”,是社会上的蠹虫,是“政府里面的败类。”[105]这种“人为的贵族”之存在,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因此,他要求铲除这样的贵族。为此,他提议采取以下几种措施:第一,废除嗣续限定法;第二,废除长子继承制。他认为实施这两项措施将从经济上打击“人为的贵族”,“砍掉人为的贵族之根”。弗吉尼亚之废除这两种制度,就是他努力的结果。他曾得意地说:在整个独立革命中,没有任何改革比弗吉尼亚之废除除嗣续限定法及长子继承制更为重要的了。但是实际上如贝林所指出的,嗣续限定法和长子继承制从来都没有在北美生根,甚至在潮水地带的弗吉尼亚也是如此。在土地价廉和容易取得土地的地方,这种法律上的限制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因而在革命期间及革命后在法律上废除嗣续限定法及长子继承制,并未起过多大的实质性的作用。而且,在这以前,北美地广人稀的条件就已经判决了它们的死亡。[106]其实,在南方,为了砍掉贵族之根,更有效的办法是消灭种植园奴隶制度,而对于这一点杰斐逊似乎没有认识。
在杰斐逊看来,铲除“人为的贵族”,任务只完成了一半,他还主张另外培养“自然的贵族”来代替“人为的贵族”管理国家。在他眼中,所谓“自然的贵族”便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说:“我认为最好的办法,便是……让人民去自由选举,把自然贵族选出来,而摒弃人为的贵族。一般说来人民会选出真正德才兼备的人的。”[107]到1813年他又表示:“如果我们自己的公民的道德、物质状况使他们有能力选出德才兼备的人去管理自己的政府,并且每隔不长的时间就重新举行选举以便使他们有可能撤免不忠诚的公仆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108]
(二)消灭贫富悬殊现象
杰斐逊反对财产上的极端不平等现象。1785年10月28日他在致麦迪逊的信里指出财产上的“这种极大的不平等的后果给广大群众带来那么悲惨的生活”。他说:“无论何时在任何国家出现荒废土地及失业的穷人,这就说明财产法扩展到侵犯自然权利的地步。”[109]他看到富人对于穷人的掠夺,感到痛心疾首,并且认为这是人吃人的现象。[110]1785年秋他在法国枫丹白露由于亲眼看到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而伤感不已,并且敏锐地看出: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是造成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111]然而,他又“感到平均分割财产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主张采取温和的措施:“让它的分割与人心的自然感情联系起来进行,静悄悄地缩小财产上的不平等。”[112]他提议采取下述几种措施:第一,实行累进所得税:“豁免财产在某种标准以下的一切人的税,而按几何级数向财产在这个标准以上的人征税”。第二,把未开垦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人。[113]1776年他向弗吉尼亚的代表大会提议,凡土地财产不及50英亩的人,都应该无代价地分到50英亩的土地;土地财产在50英亩以上的人则无权分到土地。他同情在边远地区的“占地人”,他赞成把西部国有土地分成小块无代价地分配给他们,而不是卖给他们,并且希望这些贫苦的劳动者在分到土地后,不必向州政府缴纳地租。他反对政府把国有土地赠送已经拥有大量地产的人。[114]但是,杰斐逊的这个主张只停留在口头上,当他在1800年任美国总统后,他并没有实行这个主张。1804年他所颁布的土地法虽然降低了西部国有土地的出售条件,还可以分期付款,但距离无代价分配土地还是很远的。
(三)建立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
杰斐逊对于上升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抱很大的反感。在英国的旅行,使他亲眼看到英国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蒙受的种种苦难。而且,他还看出,资本主义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大多数人陷于赤贫和破产,“把社会上大多数人变成贫穷的自动机器。”他认为商人在市场上*买贵卖,这个职业不可避免地导向狡猾欺骗,并且通过投机、阴谋及操纵造成大量财富的集中。[115]因之,他很自然地要求美国避免资本主义灾难。按照他的想法,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灾难,应该在美国建立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他希望美国人民“既不从事商业,也不从事航海业,……我们全体公民都将是农民。”他说:“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公民在工作台旁劳动,或者手摇卷线杆。……让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吧!”[116]
在杰斐逊看来,美国得天独厚,有条件成为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他说:“在欧洲,土地或者被开垦出来,或者被封锁起来不让耕种者染指,因此,不得已只好依靠制造业来维持其过剩人口。但是,我们却有大量土地在吸引农民去耕种”,因而美国的“全体公民都去从事土地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117]他之所以希望美国成为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还因为他感到自由平等的和独立的农民是政治民主的最好的基础,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将破坏民主政治的基础。他相信生产方式之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性格。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当我们拥挤在大城市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将和欧洲一样腐化下去,而且和那里一样互相残食。”他还认为,在工业社会,工人依赖于资本家,而“依赖会产生奴性及贪财心理,扼杀道德的萌芽,并且为野心家的阴谋准备适当的工具。”他说,“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的其他阶级的总和与农民的总和之间的比例,是不健康的部分与健康部分之间的比例,并且是衡量它的腐化程度的晴雨表。”[118]他又说,“工匠阶级是罪恶的勾引者,是一个国家的自由会借以被全面推翻的手段。”相反地,一个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则会培养人民的善良的品德,从而对于民主政治的巩固发展大有裨益。他用最美好的词句去歌颂农民的美德。1785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耕种土地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是最为生气勃勃的、最独立的、最有德行的人,他们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且用持续不断的纽带和它的自由及利益结合为一体。”[119]
其次,杰斐逊认为从经济角度来衡量,农业也远比工业更为优越,因为前者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比后者更多得多。他说,“最能增进国民财富的是可以诱发农民勤劳的大量未垦土地呢还是制造业?主要应该考虑这样的事实:农民把劳动用在土地上,会使土地自动增加大量的东西:每播一粒小麦于地上,就会生出20、30甚至50倍小麦,相反地用在制造业上面的劳动却不会增加新的东西。几磅的亚麻在他手中只会生产出几个本尼威特(英国金衡单位,等于1.555克——引者注)的花边。”[120]但是,如马隆所指出的,杰斐逊之喜爱农业社会而讨厌工业社会,更多地基于道德的政治的理由,而不是基于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的理由。[121]
不言而喻,杰斐逊的思想带有重农主义色彩。他研究过重农学派的许多著作,与法国重农学派尼摩尔交往甚密,因之重农学派对他发生影响是很可以理解的。[122]但是必须看到:重农学派思想中的反民主倾向是他所反对的。比如,重农学派主张私有财产(首先是土地财产)是社会构造的基础,因而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应该与财产多寡相适应。杰斐逊就反对这个观点。他在批评尼摩尔为南美共和国所草拟的宪法草案时,就尖锐地指出社会构造的基础应该是人民的社会契约,订立契约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要求,因之社会的一切成员在国家形成及统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他质问重农学派道:你们抹煞了没有土地的人的地位,而没有土地的人正是构成自古以来的社会的多数。
不过,总的说来,杰斐逊关于建立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的整个想法,是乌托邦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条件下,要想维持这样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要发生分化,必然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他对于工业、农业的看法,对于工人、农民的看法,也有主观唯心主义偏见。特别是他夸大了小农的品德,歪曲了工人阶级的形象,更是不对的。
但是,杰斐逊到晚年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在拿破仑战争中,中立国船只遭到掠劫,使欧洲工业品无法运到美洲来,这就使得他认识到美国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他在1816年就开始了这个改变,他说:在拿破仑战争中,“海盗行为蔓延于陆地和海上,……在这个国际之间秩序混乱的情况下,我们有上千只船被掠劫……这样,我们就完全被从海上排挤出来。……为了独立,为了生活上的舒适,我们就应该自己从事制造。现在我们应该把制造业者放在农民的身旁。……我们是制造自己的生活用品呢?还是不这样做而依靠外国的意志呢?现在反对国内制造业的人,一定是或者希望我们降到对那个外国(指英国——引者注)依靠的地位,或者让我们赤裸着不穿衣服,并且和野兽一样靠穴居生活。我不是这样的人;经验告诉我:制造业现在对于我们的独立及舒适的生活都很重要。”[123]
诚然,美国应该工业化到什么程度,是否让它发展到超出本国需要之外并且与外国竞争的程度,他还不太清楚。但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则是“关心人民的生活及幸福”,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对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态度:他对于工业化的估价,不是按照资本家的帐目表,而是按照社会的帐目表(亦即人民的幸福)来衡量的。[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