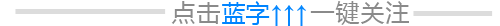

经公众号“中国国家历史"(微信ID:zggjls)授权转载。
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人饱受病痛折磨,甚至被病魔夺去生命,类似情形在时人的各种记录中颇为常见。战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严重损害了知识人的身体健康,营养不良造成的抵抗力下降,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的出现。而为了谋取更多生活资源,知识人大多从事兼职,繁杂的工作负担也会导致各种疾病侵袭。此外,战时恶劣的卫生医疗条件也是造成大后方知识人患病,甚至于病亡的重要原因。战时大后方知识人的病痛和死难反映的是战争条件下特殊的生存状态,从中可以体认到战争对于人基本生存权利的侵害。
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由于日伪的严密封锁、战争的消耗、自然灾害频发,以及政府经济上措置不当等原因,大后方的经济条件日益恶化,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尤其是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依赖薪金生活的公教人员,其中就包括战时迁到后方的知识人群体。战时大后方知识人生活状况恶化的表现之一,即遭受病痛的折磨,其普遍性与严重性远超出我们的既有认知。
全面抗战爆发,大学即开始内迁,颠沛流离的生活让知识人开始体验到战时生活的残酷性。大批人口迁移,使得疫病的流行成为知识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西迁途中的清华教师浦江清,在其日记中记有,“凡至建阳者皆病。至是于君病痢,朱君寒热。”“屯溪至建阳六人中,江、于、詹、朱皆病过”,差不多记此事的同时,浦江清本人亦患疟疾。西迁同行的六人中有五人患急性病症,可见当时知识人少有人能免于疾病的侵袭。
抗战时期冯至一家也是饱受病痛折磨。1938年秋,冯至的夫人姚可庢疑似因息阿米巴痢疾注射埃米停过量而昏迷十天,险些丧命。1939年5、6月间,冯至陪同济大学校长赵士卿到海口考察校址,感染回归热,回来后不久即发病。据姚可庢回忆,“6月27日,他忽然发烧,三十八度八,可是情况特殊,烧有增无减,人特别痛苦,神智昏迷。我赶紧把唐哲医师请来,他看不像普通感冒,立刻抽血化验,结果是回归热,原来回归热病菌在他体内潜伏了三个多星期”。后由医生为其注射—种治梅毒的特效药,卧床休息了两个星期,才渐渐康复。除了这次得回归热以外,“后来恶性疟疾、斑疹伤寒、背上疽痈等有名堂的疾病,都连接不断地光顾他,他一关一关地闯过来了。可是他发高烧甚至昏迷不省人事时,那种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冯至的女儿冯姚平也是常受疾病侵袭。“她得过百日咳、猩红热,出过麻疹,至于伤风感冒,更是家常便饭。一般说来,出过麻疹,便有免疫性,不会再患,可是她竟患过三次,一次比一次重。”姚可庢甚至到了谈“病”色变的地步,她在回忆中写道,“他们父女在昆明轮流得过多种传染病,我的日子总是战战兢兢地过着。每逢我走过昆明大西门。我总是本能地不敢向左边看,因为那边有家棺材铺,横放着几口棺材,我偶一瞥见就毛骨悚然”。

燕京大学
战时担任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曾在回忆中提到燕大教职员的病状,“陈寅恪先生双目失明,这不但是陈公的痛苦,亦且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此外,韩庆濂先生以健康情况,辞职离校。包贵思女士以健康情况,提前回美休假。赵人隽先生入院开刀,这是人所共知的消息。其他病痛,大家都是得忍就忍,报喜不报忧。所以无法确计,只可臆测。以笔者本人而论,曾患疟疾,又患瘟热症(Typhus)一场,住院调养了相当时日,幸获康复。笔者另外胆囊结石,不时作痛。又背骨错节(成渝路上颠簸过度),坐卧不宁”。可见当时燕京大学教职员受病痛困扰的普遍。
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回忆也有对于战时病痛之苦的记录,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从岗头村搭一辆马拉的两个轮子的板车去西南联大上课,马惊跳起来,把我摔下车的路旁。因为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差不多一个月。内子阮冠世本来便连病了几年的,因为又担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来。脉搏微而快,有时数也来不及数。身体太弱了,医生看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天城里北京大学的办事处的金先生下乡来,看看是否要预备后事了。幸而冠世挣扎过去,病卧了几个月,到了冬天,费好多事,借了一辆病车,从岗头村送她到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住了两个月,总算回过一口气来”。又说:“现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象那时我们孤单单地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

西南联大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被病魔夺去生命,这种情况亦不少见。据武汉大学的统计,自1938年4月迁校乐山到1940年年底为止,不到三年,学生因病死亡者就达五六十人之多。其中仅1940年9月19日至10月底的50天内,就有五位学生相继死亡。到了1943年暑期,在短短一个月内又有七位女学生相继死亡。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4月至1943年8月的五年内,武汉大学相继有近百名学生死亡。许多才华横溢、学有专长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萧君绎等人被贫病夺去了生命。

竺可桢
武汉大学的情况在大后方高校中并非特例。1939年10月16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总理纪念周报告,“初述校中状况,谓暑假中不幸讲师陈大慈及学生俞锡南、李秩西等三人(病故)。"1944年10月1日,竺可桢等来到浙大所在的贵州遵义“老城南门之棋杆山,即民国卅一年四月间葬张荫麟处也。由魏春孚领路,山上几成为浙大员生之墓地。在此葬者除荫麟而外,有最近以nephritis肾炎病死瑞安人蔡煜,去年夏以脑膜炎去世史地系杨曦,两年前在江中溺毙之工学院徐正书,及苏元复之舅文学院杨树衡,系海宁人。同事之眷属有樊君穆之子樊永疆及史地系吴贤祚之母亲”。可见战时浙江大学师生亡故者之多。
抗战时期恶劣的生活条件严重损害了知识人的身体健康。抗战后期的大学教授们要用相当于战前8~10元的待遇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无奈之下就只能靠“消耗早先的积蓄,典卖衣物及书籍,卖稿卖文”,以至于出现“营养不足,衰弱,疾病,儿女夭亡等现象。换句话说,经常的收入不足,只有消耗资本,而最后的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了”。持续的战争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一种消耗,而物资消耗之后,接续的就是健康和生命的消耗。战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就曾感慨道,“战争给予人类破坏的力量是愈来愈深入、广阔,民族健康的破坏到现在,也真到了惊人的程度”。
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陈达在谈到抗日战争对自己的影响时,就提到,“不说别的,单讲我国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刚是四十有零的壮年。而今白发频添,精神渐衰;虽尚非是老者,但体力、毅力与记忆力,已远不如当年。抗战不是使我衰老的原因,因没有战争我亦是要衰老的,但抗战确实催我衰老,使我衰老得更快。”可见战争对于人的生理机能的消耗是常态社会下难以想象的。
1945年夏天,当吴组缃见到时年才47岁的朱自清时,对他的衰老感到异常吃惊。吴组缃见到他时的印象是这样的,“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样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瘦削劳倦之态……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凸露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这颇为真实地反映了战争对于人的消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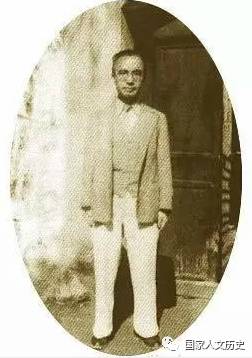
经历过抗战时期艰苦生活的朱自清先生
战时普遍性的生存必需品的匮乏,造成知识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的出现。而为了糊口,大学师生多四处兼职,以谋取更多生活资源,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也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
首先出现的往往是因营养不足造成的各种健康问题。梅贻宝在谈到战时燕京大学生活时,提到“抗战时期至少需要两种抵抗力:一是抗敌,需要决心;二是抗穷,需要体力根底。1945年生活指数上涨到1600倍,而教员薪金调整,升到100倍。换言之,教员的购买力降到6.3%。结果当然是营养不良,疾病丛生”。费正清在一份“清华问题”的信件中也提到,“这里不必浪费笔墨去描写大学教授们如何住在空无所有的阁楼上,卖书典衣,欠了一身债,患了营养不足所导致的疾病”。
由于生活艰苦,营养不济,学生中出现贫血和面黄肌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1940年7月武汉大学对男生进行体格检查,全校学生1363人,男生数量1237人,其中男生营养不良者144人,占男生总数11.64%,男生当中营养中等者916人,占其总数74.05%,营养比较好的男生177人,仅占男生总数的14.31%。
因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是学生生病的主要原因。据观察,西南联大的学生“营养不良,弱不禁风,烦躁不安。患病以后,恢复健康的时间是其所在年龄正常情况下所需时间的两倍”。“学生易感疲乏,毫无活力。每次学校开会时,总有少数人因体弱无法坚持到会议结束。”“学生体质下降,学术水平也随之降低。早上七点钟上课,学生看起来疲惫不堪。白天,没精打采,无力解决摆在面前的问题。他们的悟性和记忆力也在下滑。”
营养不良的影响是慢性的,但长期积累会产生不良的后果。1943年5月,在访问联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之后,费正清写道:“他最近一直头疼,不想走远。他的妻子和三个小男孩都晒得黑黑的,看上去很健康,但瘦得厉害。她说她怕冷,对小病已经没有抵抗力了”。
在战时的艰难生活中,大学师生为谋生计,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养家糊口。正如西南联大助教鲁溪所言,“到了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时,那末在校外兼差就成了唯一自救的办法”。但兼职过多,繁重的工作负担同样严重损害知识人的身体健康。

钱端升
王力曾谈及战时文人生活的压力,称,“不幸地很,那些卖文为活的文人却不能不忙着做文章;尤其是在‘文价’的指数和物价的指数相差十余倍的今日,更不能不搜索枯肠,努力多写几个字。在战前,我有一个朋友卖文还债,结果是因忙致病,因病身亡。在这抗战期间,更有不少文人因为‘挤’文章而呕尽心血,忙到牺牲了睡眠,以至于牺牲了性命。"
1943年8月16日,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陈达在昆明近郊的印刷厂校对户籍调查示范报告,回来的途中,突然感到头昏,站立不稳,下公共汽车后,其“坐木箱上,目光昏黑,头不能转动,特别向左转,左颈头部下两寸许有核一,大如扁豆,浮于肤面。手足稍麻,惟未失知觉,三刻钟后略有汗,渐清醒”。病发一小时后,陈达又乘公共汽车回寓,后经过医生诊断,认为是神经衰弱,用脑过度。陈达为此特向学校请假,在家养病,后得以逐渐恢复。
除了物质生活的匮乏造成的营养不良或工作压力造成的健康损害以外,战时恶劣的卫生条件及医疗条件,也是造成大后方师生患病,甚至于病亡的重要原因。
战时武汉大学学生的体质检查中,发现学生有痧眼病的非常多,而患痧眼病很大程度上跟卫生条件的恶劣相关联。据战时曾到大后方高校考察的李约瑟记录,当时“学生们住在糟糕拥挤的宿舍里,并且遭受着肺结核一类疾病的严重侵袭。因为缺乏洗涤设施,沙眼一类的感染非常普遍”。
在联大读书的学生走幸田曾详细描述战时他们的住宿条件,从中可以想见当时学生住宿的卫生条件之差。“初夏一来,跳蚤臭虫就都在你身上找出路。有的人据说是有‘福气’,虽然在几面围攻之下,仍然可以长睡不醒。我却实在没有那本领,而住在我上床的刘君,就更不堪其苦,一夜里他要爬起来好几次,拿着电筒四面搜巡红黑道的吃血者。而白天,跳蚤好像专门跟他做对,一下跳在他的鞋尖里,一下又出没在他的大腿上,四处都是痒嗖嗖的,捉又捉不到,打也打不得,于是弄得来一天到晚跟跳蚤打交道。”
除了恶劣的环境和卫生条件容易致病外,患病后,糟糕的医疗条件对于知识人健康保障也非常不力,无论是药品还是合格的医生在战时都是极其稀缺的。
如果医疗保障能够跟上,一般的疾病都可以治愈,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据吴宓日记记载,某日,其头痛甚,似疟。后“服熙赠Aspirin一片。入眠,发汗,遂愈”。浦江清在西迁途中也曾患疟疾,在王君处得奎宁二片服之。夜睡甚美,病霍然已释。此为幸运。并称“余一日而愈,可夸也”。
但战时各大学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都异常紧缺,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医疗需要,由此造成一些疾病得不到及时防治,甚至出现师生病亡的现象。据记载,1940年武汉大学平均每天有40多人患疟疾,而校医室每天只有十支奎宁注射剂,致使当时武大师生患疟疾的死亡率愈来愈高。
由于日伪的封锁,以及实际需求量大,战时药品的价格不断抬升,从而造成医疗成本高昂。费正清在访问西南联大时,听清华教授鲍勃·温德说,梅贻琦月薪不足600元,而宴请费正清等人的费用不下1000元。“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够换回这1000元。”由此可见当时药物的紧张,以及价格的高昂。

黄子卿
很多知识人为治病而变卖财物,甚至生活必需品。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曾有一首诗,可以作为当时教职员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首诗的前面有一段序文,“三十年(1941年)秋,疟疾缠绵,卖裘书以购药,经年乃痊。追忆往事,不禁怆然”,全诗共有四句:“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虐,既典征裘又典书。"其大意是蒸饭的甑子都已积了一层尘土,肚子却无法填饱,躺在病床上,心里充满了惆怅,百无聊赖时拿起杜甫的诗,又觉得诗虽好却赶不走病痛,为了治病和维持生计,只得典当皮衣又卖书籍。
当然,除了药品缺乏以外,医疗条件的有限,特别是医生和相关医疗设备的缺乏也是病人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的重要原因。校医室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曾出现过因校医误诊而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甚至病亡的事件。“这起死亡事件突显出当地的医疗水平无法与昆明相比。接触性感染病毒四处横行,许多学生因为喝了受污染的河水而患上消化病。校医是个胖子,心地善良,外号‘蒙古大夫’。他用红药水治外伤,用阿斯匹林治内伤。最后来了一名从德国来避难的犹太医生,但只缓解了一点点医疗危机。"竺可桢也曾在提到,“抗战以后,医术人员异常缺乏,因前线需要是项人才,而后方医生因环境关系,业务因而发达,大率不愿入机关服务”。故而学校能得到合格的医生非常不易。
浙江大学史地系的张荫麟1942年7月发现小便有血,后经贵阳中央医院诊断,结论是“慢性肾脏炎”。10月20日,学校请来遵义的中西名医会诊,但仍束手无策,于是学校决定派张其昀驰赴重庆延医,事有不巧,张其昀因途中翻车事故,4天后才抵达重庆,当即请医官金诵盘同乘专车来遵。然而为时已晚,张荫麟已经亡故了。张荫麟的病,重庆的医生能否治愈是一回事,但山高路远,延请战时陪都重庆的医生之难,竟未能在其病亡前赶到,亦可见疏散到内地的大学医疗条件之艰苦。

费正清
作为对比的是享受较好医疗条件的美国在华人员,费正清曾记述,“到1943年4月间,我又无端的染上了痢疾,渐渐变成慢性的,且久治不愈。美国海军医生对此束手无策。当我于5月间再次访问昆明时,获准住进陆军后方医院治疗。那里有一群活泼的女护士,精心护理美军伤病员。院内不时放映电影,席间还供应冰淇淋。没有谁能治好我的病,但是当我回到重庆,注射了一个疗程的德国针剂,竟然把我的痢疾治愈了”。当时中国很多知识人家庭受痢疾的折磨,最后一病不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这种少见昂贵的针剂。梅贻宝也曾提到,自己罹患多种疾病,“幸而不久能赴美报聘,两次入院,手术治愈”。亦可说明医疗条件的重要性。
战时大后方知识人所遭受的病痛折磨,当然是由于战争造成的,而且其影响甚至可能是极端的,很多知识人被病魔夺去生命,没有等到抗战胜利之时。区别于我们以往从国家层面所强调的,战争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和破坏以及军事、政治、外交层面的影响,通过本文所关注的知识人在战时的病痛和死难,可见战争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侵害。
坚守孤城4天半直至全军覆没:如果没有这场保卫战,就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大捷
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写到:“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为大明帝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禁军勇卫营四处灭火,仍难挽明朝灭亡结局
作为帝国武装力量的明军问题重重,明末崇祯皇帝最不能忍受的是将领的日渐跋扈。为打破内外交困之局,崇祯需要一支忠诚敢战的军队,大明帝国最后的禁军勇卫营应运而生。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Q&A | 为什么青岛啤酒那么有名?
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一次省港两地交流会上说了一句话“外国人认识中国通常有两种途径,一个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青岛啤酒。”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点击图片,查看所有往期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