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整理自播客“看理想时刻”(看理想app)
第5期:如何面对年轻朋友的离去?我们对生命的交代是什么?
☞ 文末“阅读原文”可直达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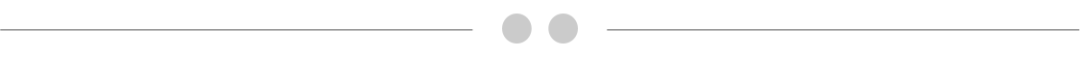
01.
生活在别处的意义危机
dy
:
前两天看到您分享一个月内有五位中青年学者因病逝世的消息。周末的时候,我也得知一位理想国的前同事——编辑苏本因为恶性肿瘤去世的消息。我跟苏本其实不算特别熟,但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很震惊。
最近我在看《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其中说到有一位女士,她跟心爱的伴侣准备结婚并且得知自己怀孕了,就在感觉美好人生即将展开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可能只有一个月或者很短的时间存活。治疗一度非常顺利,眼看看癌细胞都消失了,但是没过多久,她又查到得了另一种更罕见的癌,这一次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我看到那个故事是在得知苏本的消息之前。我那时想,如果我的生命被告知只剩一个月或者一年,我会去做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多跟家人相处,多和朋友聚聚,想要环游世界,或者辞掉工作,去做些更想做的事情——这很符合现大家对工作的普遍认知,觉得工作阻碍了我们去做更想做的事情,虽然它是为了挣钱必须要做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在工作里也投注了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也不会因为工作就耽误想去做的事,所以我会有一点疑惑。如果我突然被告知死期将近,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迫切想要去做的事情;如果不工作,我会空掉;如果继续工作,好像也不太对,别人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卷,或者可能我会有别的遗憾。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探索,这个想象让我觉得有一些虚无。
之前夏夏和王芳老师录了一期节目谈“空心病”的问题。我在想自己是不是也有“空心病”?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更早地去追问生命意义的问题,所以想到这个事情才会感觉陷入一片空白?
成庆
:
关于死亡的问题,从表层来讲,我们常常觉得死亡可怕,是因为觉得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被否定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多带着这种想象和期待——“我要过我想要的人生”。
很多人觉得不得不做的工作没有意义,生病以后觉得生命有缺憾,一定要通过旅行或者陪伴家人来建立这种意义感。这背后的逻辑,正是要证明自己这一生的存在是圆满的、有价值的。更深层的心理或者说潜意识,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最担忧的——“我”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冲动,来自于要证明、确认自我的存在。
你不觉得,每个人在世界上做很多事情的动力,是为了证明自己吗?比如说,获得更好的工作,赚钱,出名,甚至帮助一个人,背后更深层的意识,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有时候还不一定是要证明“我很行”,即使在玩游戏或者刷剧的娱乐中,潜在的意识也是要证明自己存在。当然,这是比较哲学的讨论,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时刻都能体会到这种蠢蠢欲动,随时都想要抓取什么,这样的起心动念,无非就是要证明自己存在。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有本很有名的书叫《思想录》,它是格言体的,我很喜欢。里面有一段,讲有个赌徒每天都去赌博,有时候输钱,有时候赢钱。虽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输钱,但是假如别人要给他一笔钱,让他不要去赌博,大部分赌徒都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因为他们并不在乎输钱,他们忍受不了的其实是无聊感。无聊、空虚的背后,正是人根深蒂固的、来自于生命本源的动力或动机——必须通过做些什么,来确认、证明自己的存在性。所以人害怕空虚,忙起来反而没那么焦虑,闲下来却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生命空虚、意义匮乏——很多人的解决方式就让自己动起来,或者做些什么。
回到死亡,我们一般的、表层的讨论,其实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快到生命末端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把大量时间都投入到某个方面——比如工作和事业,就觉得还有很多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感到愧疚,想要弥补,或者环游世界,或者陪伴家人……其实你不过是在这个时候感到生命不圆满、不满足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去做那些事情就能解决你对死亡的恐惧了,这只是慌不择路的一种自我安慰和弥补罢了。
即使你做了一些事情,也没有能够真正地回答这个问题: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在现有的认知框架里,有没有可能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应该从更深的观念、思想的层面,甚至宗教的层面,去讨论生命的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生命意义的危机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讨论这些话题,包括我在佛学节目里有几讲关于生死的讨论,还有和袁长庚老师的讨论等等。你不觉得,现有的大部分对死亡的讨论,都有点像安慰剂吗?——你感到难过,我就给你提供一个大家比较能接受的备选方案,让你得到一丝抚慰。然而比较残酷的一点是,大部分人对死亡的恐惧感或许能够得到少许的安慰,但是对于根本的认知问题却还是不会去触碰。为什么?因为它涉及一个深层的问题,也是今天我很想谈的一点:佛教对我们生命存在的终极解释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刚才讲到人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其实意义是被每个人自己设定的,所以会有高低不同的意义、目标。有的人想要出名、赚很多钱,有的人想要环游世界,有的人就想做个普通的职人,开个小餐馆……意义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而设定的,那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意义呢?佛教认为,没有绝对的意义。
之所以会出现意义的危机问题,是因为你对当下生活、生命中的一切产生了一种疏离感,你不满足,想要逃离。比如工作了很久以后,你会对那份工作感到厌倦,觉得无聊、空虚。就拿“看理想”来说,你们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可以向大家传播一些观念,但是你做久了之后,尤其没看到你想要的反馈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这个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
从佛学的角度来说,意义问题产生的那个断裂点就在于:我们想要离开当下。因为人就是会对重复的,或者看不到及时反馈的事物感到不满,他会开始想象过去的时光很美好,或者向往未来的时光很美好。但你会发觉,人一旦瞻前顾后,就会出现意义危机,他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体现在过去或未来的,所以有的人会怀念过去,觉得当年做的那些事情才是有价值的,有的人会向往未来,觉得一定要做某件事情让生命变得有意义。
其实,佛教认为这些都是妄想。存在本身是你对当下现实生命的观照,而不是去妄想在另外的时空得到一种更终极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意义问题的产生来自你在当下认知的错误,才会想要离开当下。想要离开当下,是因为你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觉得那是无聊、没有意义的,所以你无法安于当下。
我们很多人是把意义当成了目标,但是你为什么会设定一个目标?是因为你认为幸福的获得、更好的人生存在于别处。比如说,我们从小学就开始进入应试体制,家长、社会都会期许你好好学习以后,未来能读好高中、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赚很多钱……都是以未来许诺你意义,对不对?你可能按照这个步骤活到 30 岁、40 岁,也过得蛮顺利的,但是你会发现意义问题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尤其当下的中国社会,主流的认知是一种永远生活在别处的价值观,灌输给你的是一套“等到未来某个时刻你就会好了”的想象——未来你有流量、有权力、有财富了,你的生命就有了意义。这套价值观,奠基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基础上,导致我们永远生活在别处。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永远不会觉得每天去课堂的时光是美好的,不会觉得周围的同学、老师的一举一动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妨做个比较,虽然日剧里有些小确幸、夸张的成分,但是日剧有个特色——它会比较关注一些日常场景、微表情、微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比如课堂里同学之间的非常细微的情感表达。当一个人能注意到生命的细微情绪、周边环境的细节时,他是在当下的,他能体会到当下时空中的一切。在这个时刻,他生命的意义不在别处而在当下,他不是为了以后要读上北大清华而让此刻变得有意义,他观察到当下的那一切本身就具有意义。
所以大家经常听到要“活在当下”的说法,这其实有佛法的意味,却经常被鸡汤化。如果不活在当下,就会产生严重的意义危机,我们永远会找另外的东西来证明“我”存在的价值。好比当你做节目的动机是一定要得到未来的正反馈时,你就会陷入纠结、焦虑,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一种当下感。
 《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
我经常有这种体会。讲课的时候,我只是关注同学们在现场的反应、表情、状态,而不是非要证明自己讲得好不好,一定要他们听或者正向反馈。我只是这样讲,讲完就过去了。这就是活在当下的感受——我只需尽力地体验当下的一切,相应的结果自然就会呈现,我就不会再去别处寻找意义。也就是说,我讲课这件事情的价值,不是靠别人给我想要的反馈来证明的。这样一来,才能解决刚才你讲的这种认知悖论,否则,你恐怕永远都处在“生活在别处”的胡思乱想之中。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生病以后觉得应该要环游世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环游世界厌倦了,不是又会感到意义匮乏?人永远会有这样的意义匮乏感、不满足感,要么怀旧,要么妄想未来。但是也有人遇到这样的危机时会有更为开放的心态:他去旅行的心态,是充分地体验旅程中的一切,他不会追问:“我为什么会得病?”因为他感受到未来不可把控的时候,反而能比较理智地接受未来的不确定,更重视去把握生命当下的体验;当他只是如实地去体验生命的时候,反而不太会有等待死亡或者恐惧死亡的烦恼,变得非常自由——这种自由感就来自于他对意义危机问题的克服。他并不是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旅行上,但是他的认知在旅程中改变了。
当你不去过多地考虑用另一种可能性,或者另外的场景、时空去填补自己生命的缺憾,而是单纯地活在当下、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反而那种意义的危机感自己就消除了。佛教的理解是,你只要充分地体验当下生命的一切,不再去寻找另外的意义,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02.
死亡是断灭、虚无吗?
dy
:
我之前说,在听老师节目的时候,我到“观生死”这个部分就停下了,前阵子又听了,但是我可能并不觉得自己会有死亡焦虑。听老师的节目以后,我了解了如何跟死亡和解,如何比较平常心地去面对。但是我会想到“未知死,焉知生”,当我跟死亡和解了之后,或者说我能比较正式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对生命的意义本身产生了怀疑。
如果我的生命还剩一些时间,我或许会继续工作,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样选择去环游世界、体验,那是因为我把生命意义附著在工作上了吗?还有一种说法是“向死而生”嘛,如果我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我会珍惜地、好好地去过每一天。但是我之所以怀疑自己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规训,或者被隐隐地诱导说,人不应该放这么多精力在工作上。因为我还没有办法像成老师这样,比较open自己去更多地感受生命当下的东西,比如天气、温度或者其他的人、事、物,所以如果生命只剩很短的时间,我会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成庆
:
可能这个思维逻辑是因为你有一个价值排序,你会预设某个东西是最有价值的。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到底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一旦有了这个想法,很多人会迅速聚焦在某些事情上,比如陪伴家人,但事实上,这样就真正解决了意义的焦虑感吗?未必,因为作为有限的生命,每个人的价值排序都不是那么固定的。可能他陪伴家人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生命还在延续,或者恢复健康了,他的价值排序又会变化,是不是?所谓的最高价值/目标,并不是稳定的、绝对的,而是随着你当下的生命状态不断变动。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识到,所谓意义、目标也好,做什么事情来证明人生有意义也好……像这些观念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射而已——那只是你在当下的时空环境下,或者用佛法的概念来说,在当下的因缘下,你内心投射出这样的需求要满足,觉得某件事很有意义,但过了一段时间,因缘变化了——包括环境的变化、心境的变化,你又会投射出另外的意义、目标。人就是这样不断在变换意义、目标,却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点像猴子,抓了一个苞谷又丢掉一个苞谷,永远如此。因此,这样的解决方式虽然在某个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佛教认为它并不彻底。
我们刚才讨论了,佛教认为要活在当下。有人会继续追问:虽然“活在当下”缓解了心理上的意义焦虑感,但是如果从更大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命通往何处?我们从哪里来?往何处去?在这个层面上,佛学的生死观里有一些概念很有趣,比如说六道轮回、佛国净土。现代人一般会认为这只是一种宗教的描述,很难相信。我们先不论六道轮回、佛国净土存在与否的问题,佛教关于死亡更为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它认为人类的生命是不会被死亡中断的、永远延续的。
所谓延续,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比如说,我这辈子是这样的性格,这么一个人,这个生命/灵魂就这样延续到下一生。佛教不是这个意思,它讲的是我们生命的存在类似于一种信息的结合体——用专业术语来说叫做“业力”,死亡之后,随着那种信息的表现方式改变,就呈现出不同的生命状态。我们这一生从小孩到长大、成年,再到衰老,生命形态、观念不断地变化,那小时候的你是不是你?是你又不是你。把这延伸到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以后到下一个生命状态的转变,也是如此——下一期生命和这一期生命的关系就是,那是你又不是你。
经典里面有一种解释,我觉得特别有趣:人的死亡,就像用一盏蜡烛点燃另一盏蜡烛;后面的蜡烛和前面那盏并不一样,但是它们又有关联,因为是第一盏蜡烛点燃了第二盏。这个比喻描述的是,我们的生命是无限流转的,生生不息,永远延续的,但是生命会随着业力展现出不同的形象和表达、不同的生命状态。佛教讲“六道”,其实就是六种不同的表现形态。佛教的生命观,是站在一个更超越、更高的维度,来看我们生命的现实——人是在无尽地流转、轮回,并不因为这一期生命结束就中断了、没有了。
当一个人认为生命只有一世、一期的时候,他很容易产生虚无感,这很麻烦。佛学称之为“断灭论”。人无论做什么,背后都有着强烈的生命动机——我要证明我存在。享乐也好,认真工作、成名成家也好,获得权力也好,都是为了有存在感,用欲望、贪心来证明自我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有时候看到所谓的贪官贪污了几个亿,也会觉得很无聊,因为那些钱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也不敢拿出来用,只能藏在家里。其实他背后的心理动机就是靠这种外在物质的获取来证明他的意义跟价值,这是靠贪心来去维系的。
所以,很多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一辈子用来证明自己存在的那一切都要化为乌有了,就会产生极度的虚无感,这其实是从“有”滑向“无”的认知断裂,一种有—无的二元论。即使是很有生命热情的人,面对死亡也可能变得非常焦虑,因为他害怕自己会消失。如果一个人相信生命只有一世,就很容易陷入强烈的虚无主义,有时候还会怀疑这辈子做这么多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因为反正最后都会消失。
有些人会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像儒家讲“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思维逻辑其实是把个体生命的意义问题扩展到更大的集体范畴,比如一个文明、一个人类群体,或者是国家、民族。他们把个人的生命意义建立在群体的、更大的价值上,来缓解焦虑感。中国人过去还有一个解决方案:通过生育后代、家族传承,来缓解死亡焦虑。老年人觉得将来总有后代给自己扫墓,用这种方式来缓解人死了好像就消失了的那种虚无感。
然而,这些方式对佛教来讲都不是彻底的解决方案,顶多只是一种缓解。有的人可能借由这些方式,以相对平和的状态走完这一生,但佛教认为这仍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回到刚才讲的,佛教认为生命是无尽流动的,永远不会消失的,每一次生命都会随着因缘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子,这一世变成这样,下一世又变成那样。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佛教并不焦虑生命会消失,而是更为关注这种生命的轮回是不自主的——我不知道下一次我会去哪里?会不会更好?佛教徒在临终的时候,大多不会担心自己的生命化为乌有,而是更关注这种不确定性。
这正是佛教关注的重点——我能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命?所以很多佛教徒希望能死后能往生佛国净土;藏区的人会搭很多石头房子,那是一种很朴素的死亡观,他们觉得这一生搭了石头房子,下辈子做人就会有福报,他们是在为下一生做准备。汉族的儒家传统,则是把死亡的焦虑转换成家族的意义问题,或者转换为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抱负。而佛教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对生命有更深入的理解。
如果你不从更高的维度去理解生命,就很容易陷入这一生注定会结束的虚无感之中。所谓“结束”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你不去想清楚,就必定要面对死亡时的焦虑感、虚无感。我觉得,“信念”在这个问题上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就算你无法真正地理解清楚,但至少你有某种信念,就能安然面对。例如说,我相信生命会延续,但是如果你要我给出证明,我没办法证明。
这有点类似于宗教的意识体验,我自己相信,却没办法用这个体验来让你相信。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靠某种信念度过的,就看你是否相信生命如一条无尽的长河。
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常常深陷在自己现有的认知架构里面,想要跳脱出去拥抱另一种生命观的时候,就会遇到层层的阻碍。现在的中国人普遍相信人死灯灭,觉得生命只有一期,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唯物主义的生命观。另一些人可能会朴素地相信,人死后还会有,但是这种朴素的相信可能很模糊,没有形成坚定的认定或信仰,那么他在生命末期的时候,观念很容易摇摆,仍然会感到害怕。
所以,如果当代的中国人想要突破现有的对死亡或生命的认知,就需要有意识地一层一层清理自己对生命的认知的架构,才可能去触碰到我们刚才讲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把那个根本问题想得很清楚,或者不能以某种信念去相信、面对,那么你刚刚提到的这么多问题、心理上的纠结,就会一直不断地重复。但是麻烦的是,这个问题不是别人给你提供了答案就能解决的。很多思想资源,也只能成为你的一个助力,没办法成为你自己对生命的答案。
03.
“我”存在的价值
和对自己生命的交代
dy
:
老师刚说的“证明自己”,这一点我很有共鸣,也很同意。我所在的这个行业,可能更接近于老师说的那种士大夫精神的感觉,觉得我要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东西,让它们流传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哪怕我的生命停止了,但它们还是生生不息的。就像我们在纪念那位前同事的时候,也会把她编辑的身份放大。但是,这样的追求是不是也是一种执念?它好像有很正向的一面,但是又好像把生命意义绑定在一个具体的事情上面。
包括老师说的那些中青年的教师、学者,他们或许是被学校的各种制度要求,或者也有自己的心愿、追求。我也有我的追求,有追求会让我更加有生命的动力,但是又好像变成了佛家说的“执念”。老师在某集节目里也说过,一旦起了普度众生的念头,那也是一种执念。
成庆
:
对,回到你讲的这个思维逻辑,如果人需要一个外在的标准来衡量“我”的价值的话,就永远会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刚才讲纪念那位同事,包括我们在高校学术圈有这么多中青年教师离世,其实问题并不是我们认为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其实是自我指向的。
假如我早逝了,我的生命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是我自己才能回答的。我可能这辈子写了几本书,写了几篇文章,但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意义的焦虑感,我只是随着因缘做这些事情,做完了,生命结束了,这些事情就过去了。当我没有那种“要证明我的生命有意义”的需求和认知的时候,我的意义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我们在纪念某个朋友、熟人的时候,往往都在投射自己的焦虑。一个人去世,我们要怎么证明他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他所做的一切都罗列出来,他发表了多少论文,主持了多少课题,贡献了多少学术成果……这样就觉得他过得很有成就、很有意义。
我觉得,这其实反映出我们内心对意义的理解偏差。假如一个普通人没有这些成就,他去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评价呢?难道你会觉得他的生命没有意义吗?当然不是,但我们常常拿外在标准去衡量。所以,我们看他人的死亡或生命的意义,其实最后指向的是,我们对所谓生命意义的问题,究竟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的,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清理、思考的。
比如有大学的同事、同行早逝,我没办法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死亡,但如果他们是盲目地内卷而陷入到这个体系里面,我会觉得他们可能缺乏一个跳出来看自己生命价值的维度。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被体系绑架的感觉,但是人有一种觉性:我知道什么东西把我绑住了,我会寻找从观念上或行为上跳出来、解开束缚的方法。
就像在大学里面,我会有一种要自我边缘化的自觉,因为我对这一套运作机制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它会让我去做很多事情,可能超出了我身心能承受的范围,而且并不一定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或者有助于学术发展,而只是一种体制的空转。那么我会判断、反省自己在什么程度上能做,而不是一味地被这个体系裹挟。所有的一切,如果有个标准的话,就是你对自己的生命状态、对当下的身心状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没有清醒的觉察?
所以,看到这些中青年的朋友们、同行们离世,我不是看他们的著作或者研究成果,去评价他们这一辈子有没有价值。如果说我有一个标准的话,我希望他们在走向死亡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淡然的、接受生命结局的状态,这才是对生命更为透彻的理解、领悟和超越。
如果一个人能坦然接受这一世的命运,以一种很平静、安定的状态去面对生老病死,那么他去世时是三十岁还是六十岁,其实是平等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你对生老病死,你对当下的身心、生命的状态,有没有一种自我觉察?你有自我觉察,才能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更高维度的理解,你就不再是以外在的标准来衡量生命的价值,而是你自己对生命要有所交代。
我临终时对自己生命的交代,就是我对死亡的认知,我内心是恐惧、害怕,还是能够安定、自如地对待。我死了以后有多少人讲我做过哪些事情,写过哪些文章……这对当事人来讲毫无意义。如果说它有意义的话,从佛教的角度来说,比如佛陀圆寂,留下的文字能启发别人觉醒。但是你会发觉,我们留下的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启发人家觉醒,反而让人更加迷惑。
我们很少反省,教育真正的目标、价值到底是什么?要把人引到何处?我们教的很多的学科、观念,会把人引到比较偏执的方向或者充满迷惑的生命状态里面。我们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或者传授者,应该要自我反省:这套观念会把这些愿意听你讲话的人——学生也好,听众也好,导引到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如果你对教育的目标、方法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那么你所做的那些工作,可能在你去世后也能存续、发挥作用。
就像很多古老的经典,到今天仍在持续地在引导人们反思,让生命导向更好的觉悟、觉醒的状态。我觉得这反而是更有价值的,而作为学者发表了多少篇 C 刊,出版了多少著作,这样的目标和意义相对来说是非常有限、脆弱的。
所以,回到你前面的问题,面对朋友、同龄人或者比我们更年轻的死亡,我们要反省的是自己对死亡投射出来的认知。你其实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要靠一个外在的东西来衡量人生的价值?其实这个问题应该由逝者自己来回答,在最后那一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只是没办法向别人表明而已。最后这个问题就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了,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答案,外在的评价终究是镜花水月吗。
dy
:
所以,我们纪念她时说她是一位值得被记得的编辑,其实是在投射自己的某种相似的追求或者生命意义。
成庆
:
对,可能她生命的最后,更想念她的亲人或者多年的朋友,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所以,我们表达对一个人的哀悼,大多是在投射我们自己的观念。
04.
不悲不喜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