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60多年的发展,欧盟走到了十字路口,内外交困、危机重重。作为多极化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柱之一,欧盟何去何从引发广泛关注。欧盟各国特别是法德两国都在讨论和探索欧盟的“改革”之道,但要找到“改革”途径,必须先了解造成欧盟危机的内外因素。

欧盟陷入危机的成因
欧盟的建立是时势造就的。把欧洲各国组成统一的“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的政治主张,在欧洲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但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这种理想在战前根本无法想象。二战结束后,德国分裂,欧洲分裂,世界进入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洲虽不情愿但不得不受制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超级大国”这个词是已故德国前总理阿登纳在其回忆录里首先使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集团对峙,使得欧洲成为“冷战前线”。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科技发展、生产和资本走向国际化,西欧难以适应当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要求,因而欧洲共同体与欧洲一体化呼之欲出。
1957年3月,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政府首脑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又称《罗马条约》),条约经六国议会批准,于1958年1月1日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欧共体”)正式成立。《罗马条约》的主旨是取消欧共体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1958—1968年间,欧共体内部的关税壁垒逐步取消,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4倍。欧共体还在1962年制定了一项共同的农业政策,确定对农产品的共同担保价格体制,维护欧共体成员国的农业利益。可见,在欧共体成立之初,其经济发展之势如朝暾初露,生机勃勃。在欧共体经济发展的吸引下,从1973年开始,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相继加入。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作为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欧共体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得以提升,获得了发展的历史机遇。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给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贸易额超过6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两倍。经济全球化以取消关税壁垒、发展自由贸易和建立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为基础,欧共体在这方面的经验起了示范作用。
欧共体领导人因势而为,雄心勃勃。1991年12月的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于1993年1月1日生效后,欧共体华丽转身为欧洲联盟,即欧盟(European Union)。在经济方面,欧盟主张建立拥有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并分别于1993年和2002年启动欧洲统一大市场和统一货币欧元;在外交和安全方面,欧盟主张实行包括共同防务政策在内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欧洲的声音;在体制机制方面,欧盟建立了各级行政机构,分别是欧洲理事会(即欧盟首脑会议)、欧盟理事会(即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委会)和欧洲议会。
尽管如此,试图几年之内实现欧洲一体化的理想方案和实践明显操之过急,这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第一,欧洲一体化的目标“高、大、全”,严重脱离现实。
经济、政治、军事、安全一体化乃至建立“欧洲合众国”是美好愿景,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逐步实现。但是,由于当时的欧盟领导人错误估计了形势,改革步伐迈得太大,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且留下了不少隐患。
第二,欧盟扩张速度过快。
同上述意图和思路相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共体以及此后的欧盟扩张过快,南下地中海沿岸、巴尔干半岛,东扩至波罗的海沿岸,包含原东欧地区,直至乌克兰,成员国迅速扩大至28个(英国脱欧后为27个),而且打破了最初制订的严格入盟条件,造成联盟内部东西矛盾与南北矛盾加剧。
第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分离。
成立了欧洲中央银行,使用统一货币欧元,但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没有统一,也没有建立协调机构进行调解。
第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欧债危机,虽然主要是欧盟国家内部政策失误造成的,但同美国“转嫁危机”和向欧洲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关。
近10年来,欧盟国家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难民问题难以协调,经济复苏乏力。欧盟各国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甚至影响中产阶层收入,引发劳工和弱势群体的不满。

欧盟的艰难“改革”之路
内忧外患之下,欧盟领导人惊呼,欧盟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不实行改革,必将四分五裂。但是“改革”路在何方?
2017年3月欧委会主席容克在《欧盟未来的白皮书》中,对欧盟未来提出五种设想(以下简称“设想”),但只是老生常谈,并无新意,而且也未指明“改革”的方向。设想提出之后,在欧盟内部引起激烈争论,其中最主要的争论点是“多速欧洲”理念,这一理念在欧盟内部已经争论多年,从未形成共识。欧盟改革步履蹒跚,前路漫漫,荆棘满地。
第一,方向不明,路径不清。
欧洲一体化进程由盛到危,转折点是1992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领导人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判断失误,错误地认为冷战结束是西方的全面胜利。当时欧洲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实现了难得的繁荣。因而欧盟领导人作出了加速欧洲经济、政治、军事、安全一体化的顶层设计。这一决策是后来欧洲一体化发展产生种种弊端的根源。如今,欧洲一体化陷入困境,制度上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欧盟各成员国也难以接受推倒重来,因而“改革”出路究竟何在,谁也说不清楚。
第二,进退两难,改革举步维艰。
自1993年1月1日《欧洲联盟条约》生效以来,欧盟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3—2008年,第二阶段是2009年至今。在第一阶段,欧盟兴旺发达,欧元坚挺,有取代美元之势。但由于欧盟扩张速度过快,导致欲速则不达,欧洲一体化难以继续推进,也难以退回到《欧洲联盟条约》生效之前的状态。实际上,2017年容克重提“多速欧洲”理念,是有退半步之意,但由于欧盟内部分歧严重而难以为继。根据“多速欧洲”理念,欧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将在一体化方面先走一步,这遭到了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实践“多速欧洲”理念将会使这些国家沦为欧盟二等国家。这是之前欧盟过度扩张结下的“苦果”。
第三,意见相左,改革难以启动。
在英国脱欧之后,德国和法国成为欧盟“核心国家”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年轻气盛,一上台就提出“重振欧洲”的口号,建议欧盟在各个重大领域做出政策调整和改革。他提出要建立欧盟统一防务体系,在2020年前拥有一支共同干预部队;建议欧元区统一预算,设立欧元区财政部。德国总理默克尔老成持重,她认为,应从欧盟现实情况出发,稳扎稳打。马克龙提议的改革方案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达成共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难以实现。德法两国对欧盟改革的意见相左,使得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运转失灵,改革难以启动。
第四,政局不稳,改革乏力。
欧盟改革的最大障碍是部分成员国政局不稳。2017年被称为欧洲的“大选年”,荷兰、法国、德国、奥地利、捷克等国先后举行大选,民粹主义、极右势力崛起,迅速走上政治舞台,反欧盟力量骤增,持疑欧、反欧立场的反建制政党影响力大增。2018年,欧盟创始国之一意大利的大选结果也不例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2017年是欧盟成立60周年,欧洲多个城市发生了反欧盟、反欧洲一体化的大规模游行,说明民粹主义风潮在欧盟内部已有相当规模的民意基础。
第五,恐袭问题和难民问题造成欧洲国家社会不安定。
社会安定也是改革的重要前提,恐袭问题和难民问题严重影响欧盟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来自中东、北非战乱地区的大量难民涌入欧盟成员国,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难以预计的各类社会问题,还造成了恐袭隐患,使得近年来欧洲恐袭频发,而欧盟各国在反恐问题上缺乏有效措施,也没有形成共同反恐体系,应对乏力。由于力主接受向欧盟成员国强制摊派难民,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盟内部备受责难。
第六,英国“脱欧”,谈判艰难。
2016年6月,英国经过公民投票决定退出欧盟。2017年3月,根据欧盟《里斯本条约》第50条关于退出欧盟的条件,英欧启动了谈判程序,谈判应在两年内,即2019年3月29日前结束谈判。英欧谈判涉及的多个关键问题,一是“分手费”,经过5个月的艰苦谈判,双方在2017年底基本取得一致;二是关于英欧未来贸易关系框架的谈判,双方在2018年11月已就协议草案的核心内容达成一致。但该草案在英国国内争议巨大,目前没有得到英国议会的支持,同时,英国议会工党成员、英国脱欧影子事务大臣凯尔·斯塔莫表示,如果议会不支持欧盟的英国脱欧协议,那么工党可能会对首相特蕾莎·梅投不信任票。
第七,特朗普动作频频,欧盟疲于应付。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先后退出多个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将欧盟与中国和俄罗斯并列说成是美国的“敌人”,对产自欧盟的钢铝加征关税,其一再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行为令欧盟国家十分不安,也给跨大西洋联盟造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痕。特朗普在伊核问题和巴以冲突问题上的作为,使中东陷入更大的动荡之中,直接影响到欧盟的战略与安全利益,这是欧盟不愿意看到的。2018年7月25日,特朗普同欧委会主席容克举行会谈,随后发表美欧联合声明,称美欧之间将启动“一种为实现双方共赢的有力的经贸合作”共同致力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共同市场”。但这更多的是一种缓和双边关系的政治表态,事先没有经过认真协商,重大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敲定。这一声明也遭到了欧盟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强烈质疑,法国制造业相对弱势,又是农业大国,一旦向美国全面放开市场,法国经济必将受到冲击。
(作者系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甘冲)
(平台编辑:邓长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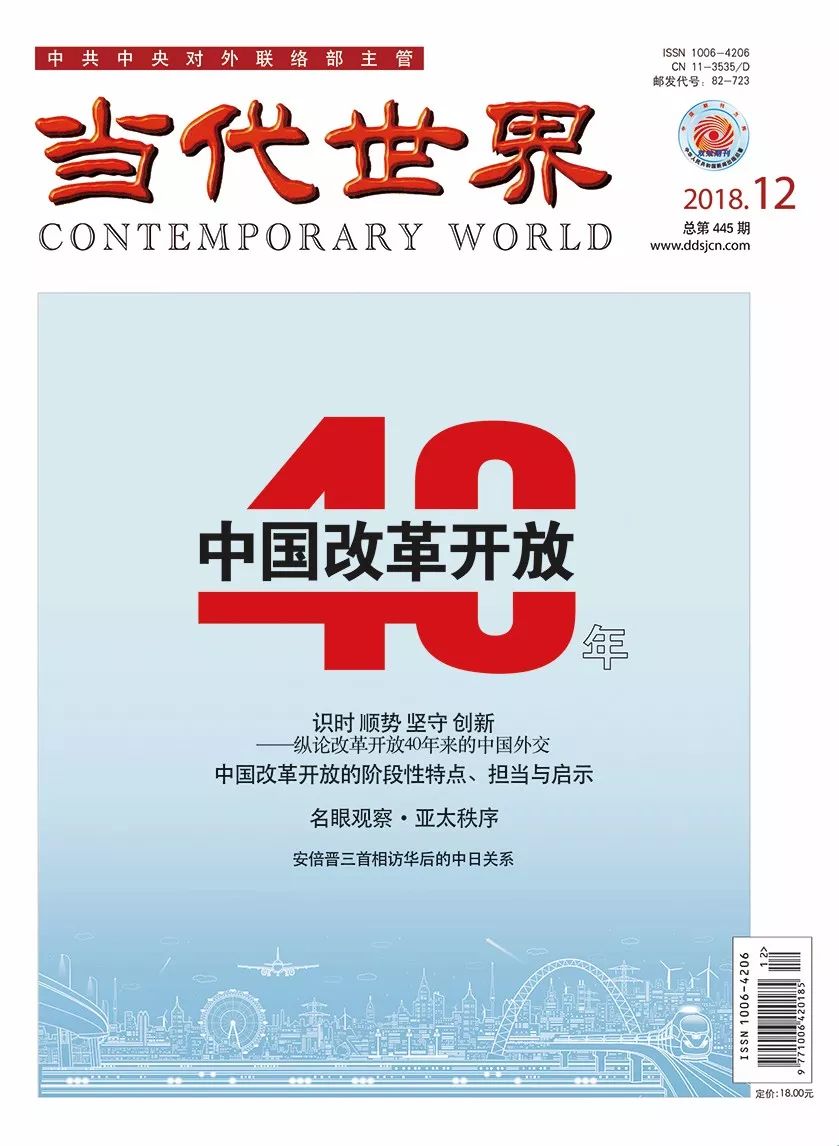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研究国际问题的必读期刊
《当代世界》杂志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月刊,每期均通过专门渠道呈送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参阅。杂志依托中央外事机构,荟萃众多知名国际问题专家,以海内外国际问题智库丰富的人脉和信息资源,权威解读和传播中国故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深度剖析国际关系和世界政党政治的演变和发展,聚焦世界热点难点,全方位、多角度评析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最新发展趋势,是广大读者特别是领导干部和国际问题研究人员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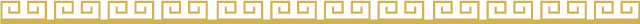
长按二维码,关注当代世界!
与您分享最权威的国际时政文章!

【中文刊】
18元/期,216元/年
邮发代号:82-723,国内统一刊号:CN 11-3535/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4206
【英文刊】
80元/期,320元/年
邮发代号:80-270,国内统一刊号:CN 10-1398/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6-1596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中联部(100860)
订购电话:010-83908408
投稿电话:010-83909012/8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