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朋友问我写“大视野”是不是很辛苦、能不能坚持,因为每一篇都比较长,而且基本上还是偏宏大的命题。是的,不容易,有挑战。不过,两年里能写出上百篇“大视野”,有一个原因,是坚持行万里路。
理论和思考并不是灰色的,只要能被生活之树滋养。
最近几个月去了欧洲三次,德国、英国和法国各一次。在全球经济中,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是美国、中国、日本之后的四到六名。从政经角度看,它们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欧洲历史上战乱频仍,一直有“统一梦”。因为英国,统一始终存在离心力;因为德国,统一始终存在向心力;而法国往往决定历史的钟摆更偏向哪一方。至于德意志精神,英格兰风度,法兰西文化,在世界上也有很深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德英法三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为8.64万亿美元,不到中国的80%,而1978年,仅前联邦德国的经济总量就是中国的3倍多。我们常常说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诚哉斯言!
三次欧洲之行,虽是走马观花,但累积起来,由彼及此,还是有些想法可以和大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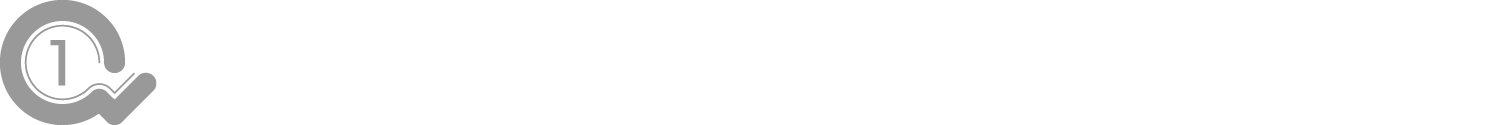
“漆器艺术的摇篮”
上周,我作为课程主任和一批商界精英参加“天链知识”组织的德国访学团,去了德国5个城市的10家公司、机构,感受到德国公司在创造高价值方面的韧性和创新能力,也感受到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促进就业与投资的服务态度。但最触动我的,是在西北部城市明斯特(Münster)的漆器艺术博物馆。

明斯特有30万人口,其中五六万是大学生,城市有几十万辆自行车,被称为“大学城”和“自行车之都”。我们去的漆器博物馆(The Museum of Lacquer Art),源于两个收藏家的爱好,后由化学巨头巴斯夫汇聚资助,20多年前对公众开放。这里不仅有东亚、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2000多件漆器艺术品,也是漆器研究中心,有几千本相关书籍。我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漆器艺术的精深,也第一次知道
1.3毫米的厚度竟然可以漆上上千层。
“中国是漆器艺术的摇篮”,讲解员说。博物馆收集的时间最早的藏品是公元前450年的中国墓穴的陪葬品,一件带盖的容器。这里还有秦朝的酒卮,元朝的雕漆盘,宋朝的盏和重瓣菊式盘,乾隆年间的题诗雕漆碗和九龙雕漆宝盒。一个明万历十五年的五爪金龙柜,原是宫中物品,流出来后把金龙的一只爪子磨掉,四爪不代表皇帝了,这才运出国境。

| 战国时期的中国漆器
日本漆器在唐代高僧
鉴真
东渡之后起步,但青出于蓝,工艺更为复杂,有种工艺是在未干透的黑漆上喷撒金粉银粉,让光泽的漆面和金色之间交互作用,沉静中跳出惊艳之美。
16世纪中期,葡萄牙、荷兰的远航商人把中日漆器运到欧洲,成为欧洲人倍加推崇的奢侈品。由于漆树在欧洲难以成活,海运又很耗时间,漆液很快会干掉,所以欧洲人开始研发自己的配方,用油、树脂和粘合剂造漆。刚开始,欧洲的漆器模仿东方的造型、纹样和工艺,延续了差不多200年,18世纪才开始脱离东亚模式,创出自己的风格、技术,表现独特的主题如神话和英雄。
伊斯兰漆器艺术早于欧洲,是11世纪末开始的,多用在书封装帧、漆笔盒等器物上,博物馆展示的伊斯兰漆器的主题多是葡萄树、花、夜莺等等。博物馆认为,
印度、波斯、土耳其的漆器是东亚和欧洲之间的桥梁。

同行的朋友说,中国的好东西都在大英博物馆和类似这里的地方。我去伦敦时专门到大英博物馆参观,自然有同感,但这一次,我想到了一些新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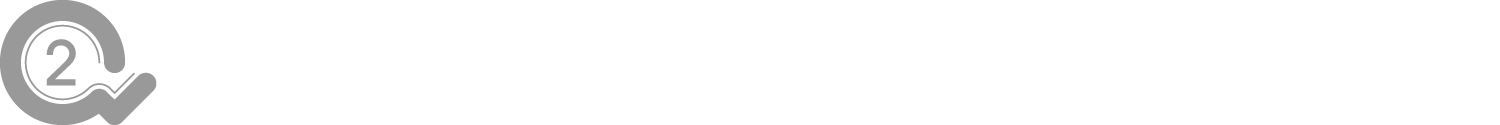
重新为世界建立标准
首先我想到的是,
一个国家的强盛,最重要的标志是为世界建立标准,也就是让世界高度认同你的产品和服务,有高价值,有亲和力。
中国曾经为世界建立过标准。16到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对中国茶叶、丝绸、陶器、家具、漆器等的追捧,就像今天中国人对爱马仕、拉菲、百达翡丽、宾利、保时捷等等的追捧。那时,以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内核的中国器物(made in China)是欧洲的奢侈品,中国“三件套”——茶叶、瓷器和丝绸是最强势的商品,其地位远胜于今天的iPhone、德国汽车、法国化妆品和意大利男装。
那时伦敦的茶叶店和欧洲国家的杂货铺,“中国新茶上市”是最具刺激性的告示,谁能更快地运来中国茶叶谁就能在商业中获得优势
。竞争甚至推动了造船和航运技术,飞剪船(Clippers)的发展就是证明。
从商业文明角度看,中国不仅产品卓越,而且商人的商德良好,在对外贸易中守信用,按合约办事,还会慷慨地将产品赊销给资金乏力的外商。美国第三任总统
杰弗逊
曾说,
“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在一切有关生活便利方面是显著的,欧洲比较近代的几种艺术的源流,却已消失在蒙昧的时代之中”。
由于中国器物价格昂贵,欧洲包括后起的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中长期逆差,英美最后是以鸦片作为武器。
埃里克•杰•罗林
在《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中指出,从1784年到1814的30年,近300只美国商船向广州航行了618次,新英格兰的花旗参、夏威夷群岛的檀香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海獭几乎绝迹,燕窝、鱼翅、玳瑁、海参也险遭不测。即便如此,两国贸易还是
逆差,
中国不仅是“欧洲白银的坟墓”,美国白银也有去无回。
为扭转不利,在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
塞缪尔•肖
(Samuel Shaw)的建议下,美国船只开始携带鸦片进
入中国。因为英国垄断了印度产的鸦片,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在土耳其找到鸦片,进入中国后被叫作
“金花土”
,虽然质量不如印度鸦片,但因为便宜很有市场,美国迅速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对华鸦片贸易国。为保护走私,“鸦片飞剪船”(Opium Clippers)还配备了重武器,如大炮和枪支。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made in China的生活方式曾是那样引领风气,如果英美不用鸦片这一“阴招”完全无法和中国竞争。这就是高价值产品的威力。
对于鸦片贸易的不合法性,美国政府也承认,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第23款指出,
“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
近代工业化时代之后,中国逐步落伍。今天“中国制造”的面貌虽然大为改观,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成为物美价廉的象征,但其总体上的地位和十七、十八世纪时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茶叶、瓷器和丝绸远不能相比。我在南通听说当地造的顶级红木凳子,17万元一个,令人咋舌,但专供爱马仕之后,价格竟然超过50万元,谁有品牌溢价不言而喻。日本、德国今天的陶瓷和漆器制造,在材料、工艺和设计上有不少创新,精益求精,在国际市场反而比中国产品昂贵很多。
中国真正拥有定价权和话语权的产品屈指可数。

不过,当我在明斯特的漆器艺术博物馆伫足时,我对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前景并不悲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经济复兴后必然带动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力提升,重新建立世界标准并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民粹主义不可取,但中国文化的精粹、国粹的发扬,可能水到渠成。
在德国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2000年刚来的时候,德国电视里播的中国还像是清朝的中国,而现在,原来非常大众化的中餐已经有高档化迹象,在柏林阿德龙大饭店的中国餐厅,一只北京烤鸭的售价是400欧元,德国人很喜欢。这是正面的
“原产地效应”
,即随着“中国”这一原产地的实力和形象的攀升,贴上中国商标、具有中国特质的产品的对外影响力越来越强,越来越积极。
再有二三十年,当中国的发展更加均衡,公共文明(比如公厕文明、垃圾处理文明、公共场所礼仪文明)普遍提高一大截,软实力更强,产品质量更好,
我相信中国会有一些产品和服务会被世界看作美学和时尚的象征,甚至重现历史上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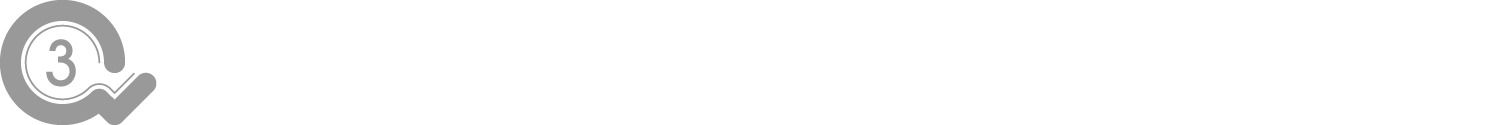
虚怀若谷才有真正复兴
在漆器艺术博物馆,我想到的另一问题是,我们展望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的复兴,绝不是鲁迅先生所说
的“我们的祖上比你们阔”的那种精神安慰,以及凡中国的都是好的、“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的那种胜利法。
拿漆器艺术来说,中国确实是摇篮,但日本、印度、阿拉伯、欧洲后来都发展出有自己风格的艺术,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最后都看不出中国的痕迹,而好像是一片森林中的不同树种,各有所长,它们有些树种甚至比中国的还好看,还有生气。所以
我们很难说,世界漆器艺术的中心就是中国,一部漆器史就是中国漆器向外界的辐射史。
而近年来关于民族、地理、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研究都证明,
“中心-边缘”的文明扩散论往往不符合历史事实。
今天我们头脑中的疆域好像都是固定的,哪里是中心哪里是边缘往往由政治话语确定,但今人脑子里的地图和历史上真实的地图一样吗?不一样。比如我们认为云南是中国的边陲,但历史上云南也是一个中心,是印度文化、藏文化、汉文化交织冲撞的中心。
中国历史不是由一个中心写的,而是由无数地方的创造共写的。
这中间当然有某些区域在某些时间向外部进行文化扩散的一面,但更有相互影响的一面,也有异域“反客为主”的一面。中心和边缘是相对的,关系是流动的,有时是互融的,互相转化的。而
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强大的吸收消化能力,她不向外拓殖,但能吸收外力、进而化之。所以有学者说中华文明是一种
absorb
的文明,也就是说吸纳力特别强。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重要的开放。1843年上海开埠,是
被动开放
,当时上海人口数量只有20万,在全国城市中排第12,并不领先,但由于上海从内河时代走向海洋时代,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各种资源源源不断而至,到1900年人口跃居全国第一,达到100万。第二次开放是改革开放,是
主动开
放
,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城市是1980年正式建立特区的深圳。预计深圳将在2038年左右超过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经济城市,也就是说,一个边陲渔村可以用不到60年的时间成为全中国城市之最。
上海和深圳在它们开放的那个时点都不是中心,但后来都成了中心。而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中心,比如王朝之都,今天都“泯然众人矣”。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当时空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时代坐标发生重要位移后,会为新中心的快速形成提供机遇,而自以为是的中心,固守陈旧中心思维的中心,不再吸纳、不再变革、不再进化的中心,很快就会被后来者超越,甚至边缘化。
漆器艺术的演进给我的启示是,
世界文明的创造是多路径探索的汇合,每一种探索都构成了文明的来源。在不同时点上,发展或有先后,但最终不会定于一尊。正如我相信中餐的国际地位会逐步提高,但日本料理、法国大餐、意大利美食也仍将各领风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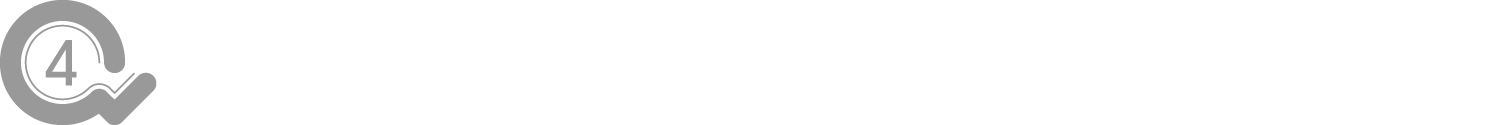
开放的市场与互动的价值
我们这次在德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有的跨国公司如工业4.0的领先者FESTO,其中国区总经理专门飞回德国介绍情况,让我们看了最先进的4.0生产线是怎么运行的。他们当然不是“活雷锋”,而是看重中国市场,FESTO一套4.0设备的引进要一两千万欧元,用于培训和教学的模拟微型设备也要五六百万欧元,附加值很高。
德国1/7的就业靠汽车产业,汽车业最依靠的就是中国市场,有人说“没有中国市场,德国经济会崩溃”。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恰恰是要更加开放。更开放,就有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只要引进来,就有外溢效应、人才效应,外企获利,中国的得益会更综合和长久。我们要努力让中国成为八面来风的世界风口,千万不要有八方来朝的心态,何况我们很多方面还有不少差距。就是要对全世界的好东西、高技术、人才、各种模式(包括教育、医疗、文化等)开放,让他们因中国市场而受益而发展。只要和世界最先进的东西同行,又有强大的学习消化吸收胃口,我们就有更大可能去满足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