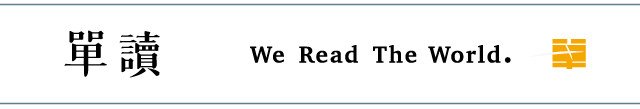
【单读访谈】是单读的固定栏目
,
我们将定期在单读微信公众号和单读
App
更新单读编辑部的访谈文章。在表达方式急速更新换代的今天
,
单读将重新探索高质量的访谈。
作为台湾著名文化人,詹宏志有着多重的身份,是编辑、出版人,也是电影制片人、唱片公司和互联网公司老板。这一次,詹宏志以旅行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借他的新书《旅行与读书》出版之际,单读主编吴琦再次专访他,谈他在不同角色变换中的心理状态,以及在潮流更迭中的坚持与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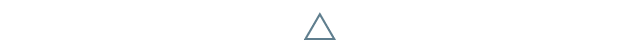
詹宏志:要分析这个社会,得你们自己来了
吴琦
三年前,曾在一场台北的大雨中,拜访过詹宏志老师。
通过侯孝贤、杨德昌、罗大佑、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人的大名,我才慢慢知道他,他的名字总是出现在书的内页、唱片的角落、滚动的电影字幕里。他是这些著名作者的同代人,是他们亲密的朋友,也是那时崛起的台湾创作重要的推动者。
听说他读书无数,记忆力惊人,和传说中的情形一样,穿过层层叠叠的书架,我才在他办公室里一个逼仄的空间里见到他。那时他已经是互联网公司的管理者了,在新技术的浪潮下再一次开风气之先。但我顽固地拉着他谈书、谈电影,没有料到互联网经验此后会在内地抹平一切。
八十年代,他对于台湾社会的判断就曾准确地点中社会的命门,看到经济起飞的情势之下人们内心的空洞,一时畅销无数。杨德昌电影里的叛逆青年,陈映真小说的那些在摩天大楼里工作的白领,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的同伴,成为我们自己,而詹宏志的人生轨迹,也成为我们的寓言。跨入 21 世纪,内地在电子支付、网络购物领域的步伐已经超过台湾,整个社会的焦虑也达到了新的强度。当年,正是类似的振荡,撕开了台湾社会的口子,在深渊中,鞭策出那一代人的创作。

詹宏志是这一切的见证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自己的幕后身份、读书人的位置、知识的作用——这些我们依然纠结的命题,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在北京重逢,许多旧事重提,唯有一件是新的,那就是时间。他谈起自己的衰老,许多事情力不从心,也有一些,不愿提起。
尽管崎岖缱绻,时间终究是线性的,在我们之先的台湾经验与台湾教训,还是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事情正在往同一个方向发展。詹老师的过人之处和遗憾之情,除了诉诸记忆,似乎再没有其他更确切的托付了。
我记得在台北时他说起自己从乡下进城时,行李中专门带了一把“扁钻”——压扁的长铁钉,作为自己的防身武器。临行前母亲吩咐他两件事: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千万不要写文章,仿佛唯有如此,自己的孩子才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技术、资本、欲望加速奔流的年代,我们的武器是什么?詹老师笑笑,不愿再解答我更多的问题了。
吴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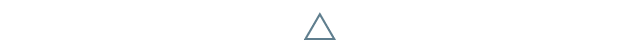
好的编辑是理解作者的意图,然后充分表达它
单读:
《旅行与读书》这本书的后记里提到您对全书做过比较大的修改,我想问被删去那一部分主要是怎样的内容?
詹宏志:
大部分是讲旅行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的进展,旅行的多种形式,比如军队的移动是军旅,采集动植物是自然学家的旅行,和尚跑去取经叫做学问僧,有的为了知识而移动,有的为了财富,还有作为教育形式的旅行,把旅行作为训练自己的一部分。我曾经写过蛮多跟旅行理论有关的文章,讲人为什么去旅行,旅行带给他什么样的结果,还有历代的人怎么看待旅行,写的时候也会举些例子,有的是历史上有名的游记里面的段落,有的是我自己的经验,所以论述里面有一点故事。我也写了一些自己的游记,那是以故事为主,偶尔也有一点论述,延伸出来的议论。当时我把这两类的文章放在一起,我的小孩看了之后给我一个建议,说这显得有点性格分裂,而且看起来你对这个书没拿定主意,他建议我不要这么杂,要单纯一点,后来我就把理论性的东西都拿掉了,剩下的以游记为主。
当然我有点惶恐,我自己并不是真正厉害的旅行者,只是一个有点书呆子气的旅行者,如果完全没有理论的部分,我也觉得怪,后来留了一篇文章做附录,其他被我拿掉的十多篇文章,文章有长有短,都是比较接近这样的风格。
单读:
从作者自己的角度,删掉这一部分会觉得可惜吗?
詹宏志:
当然,那是我兴趣的一部分。未来也可能找一个方式,重新来编辑它。现在出的这本《旅行与读书》大部分是旅行记录,尽管文章长短有别,体例有别,但环绕着一个人的旅行的感受,好像还成系统,但当它变成理论文字的时候,这么分散就好像不是一件好事,可能要更有结构性。那些文章现在看起来结构性不强,是各自独立的议论,长短也不一,也许我需要补充一些东西,才适合把它编成另外一本书,这看缘分了,我总觉得一本书到它成型的时候,自己会告诉我。
单读:
一边是故事性的叙述和自己的经验,读者容易看得懂,另外一边是知识性的、议论性的写作,可能大家未必看得明白,您写的时候会注意这个区别吗?
詹宏志:
写作时候的我跟做编辑的我有一点不同,做编辑的我当然得去考虑和读者之间沟通的问题,而作为写作者的我,当然想的是忠于题目本身。题目要求的门槛是高的,能读的人少,有时候也不可避免,哪怕是我现在作为附录的这一篇,其实也有一定的门槛要求。这篇文章真正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个论点,科幻小说其实是旅行文学的延伸,从它的源头上看出两种文体的相似性。这是一个大胆的看法,有很多不一定周全的地方,其实不是一篇容易读的文章,但在叙述的策略上,我尽量用公众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讲。举个例子,凡尔纳和斯文·赫定的书在科幻小说和旅行文学类别里都是比较大众的作品,读起来难度没有那么高。
我的写作其实大部分是理论性的文字,很少会写抒发个人情感的东西,过去十年当中我只有两三本书比较感性一点,包括这本书在内。感性的书和理性的书目标不同,也很难彼此替代,并不是说我希望跟更多的读者沟通,就能去写更故事性的作品。有的书出发点就是理论性的,它也只能写成理论,如果能够沟通的人数有限,也只能这样,这是创作者忠于题材的方法。我只能说我很幸运,还有机会讲故事,这给了我一个和比较多的读者接触的可能,现在看起来好像的确如此,这本书显然能够接触到的读者比我过去纯粹理论的书多一些。这个话好像也不太对,我 80 年代末写过分析台湾社会发展的书,在台湾可以卖到四十万本,当然那时候整个社会对台湾何去何从有强烈的困惑,正好跟这个书相符合。不过我现在可以感觉到,一本说故事的书,让我接触到的读者是比较多元的,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单读:
您书中记述了大量的细节,我很好奇这些细节是什么时候记下的?用什么记下的?
詹宏志:
这个大家都猜错了,我大部分文章都写在旅行之后很长的时间。比如阿拉斯加那篇,我写它的时候距离那次旅行已经十年了。我写非洲的时候,极可能离我的旅行大概过去七八年。旅行中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全部是靠记忆。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我让它沉淀,如果我还记得那就表示它对我来说印象深刻,记不得我就不可能写它了,第二,我又是一个要跟描述搏斗的人,所以我需要这些细节,任何一个经验我都必须让它反刍到那个地步,我才有办法写它。所以有一部分自然淘汰了,另外一些必须要像一个真正的工作,和记忆拔河,把里面的东西完全抓出来。我很少做完一件事回来就写它,通常会放个五年十年才写,我要确定这个事真的对我有意义,过了十年,如果不在了,就算了,那就不是要紧的事。

在旅行当中,的确有一两件事我当时已经意识到未来有可能会写它,我害怕会忘掉它,当时会有一点简单的描述,比如我写非洲狮子,当时在现场写了车子转弯时看到那头狮子在石头上方的样子,它身上的肌肉,虽然是母狮子,可非常雄壮,还有画下来。写寿司师傅那一篇,我把当天的菜单留下来,所以后来还能记得所有的细节。不过,我平时在旅行当中不记任何笔记,也不拍照,不会把手机拿出来。
单读:
是不是可以说,作者的身份必须忠实自我,对自己表达有要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和读者沟通的障碍?
詹宏志:
你这个话说得很对,作者没有办法的,因为他忠于他的选题,忠于他预设的说话的调性,他已经选择了读者。这当中有的读者群大,有的小,那是求仁得仁,你不可以写一本沟通有困难的书,又抱怨这个社会不买它。如果你提了一个较高的门槛作为阅读的要求,最后读的人不多,每个作者都要明白,这是你做的选择。
单读:
编辑需要帮作者去平衡吗?
詹宏志:
不,我认为一个好的编辑是充分理解这个作者的意图,然后充分地表达这个意图。应该少数人读的书就要变成少数人读的书,要多数人读的书就要让它真正成为多数人能读的书,意图和结果要一致。
单读:
编辑和作者的纠结与矛盾,在您多年的工作中,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吗?
詹宏志:
这个其实是我每天面对的问题,应该这样说,我真正的训练是一个编辑,这是我做最长的时间、也是自己下的工夫最多的一个领域。我是用作为一个编辑的训练,来参与别的工作,并没有真的改过行,从头到底我只会编辑这件事。我是这样来理解编辑工作的,他面对的社会有两种人,左边是一群有知识、有创造力的人,右边是有一群渴求知识的人。我的工作是要认出这些有创造力有知识的人,还有他们身上潜在的题目,我要鼓励他们尽可能把这些能量变成某一个创作物,或者一本书。为了让这些书能够到达这些渴求的人,我需要设定一个情境,让这些人可以理解,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彼此相遇。这是编辑每天在想的事。
当我在出版的工作里失业的时候,有机会跑去做唱片公司的负责人。当时有一种唱片是刚产生的新东西,它需要一个新的沟通情境,比如我 1983 年碰上罗大佑的唱片,台湾之前是没有这样的类型,这个唱片几乎没有办法在传统的唱片管道里出现,它不能在电视上出现,不能在广播里出现,完全不能公播。这要如何让它的潜在听众知道这张唱片的存在,我就需要用别的工具。这种时候,编辑的背景才有用处。
电影的情况是很像的,我有机会处理电影的时候,如果把杨德昌、侯孝贤这样的电影放到院线上去,和成龙的电影一样,在一百家戏院一起上,不容易达到沟通效果。用那样的方式工作,带给这个影片其实是伤害,一部分观众是不能明白的。但当我把这些电影倒过来,如果它是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艺术电影,在较小范围上映,较细致地沟通,找到对这个电影有较强的热情、较多的知识背景的人来看,每个社会都有这么一群人,如果是一个国际性的劝募式的市场,每个地方拿一点钱,结果极可能跟台湾整个院线一样大,或者更大。但它的工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沟通情境完全不同。这个理解就完全来自我对书本的理解,书本就是不同的书种,面对不同的阅读大众,有的书是大众的,有的书是比较学院的、比较高端的市场。我们得做不同的事,用不同的工作方法,到达这些不同的阅读者。不管是唱片、电影或者是后来的互联网,其实我的情境是很像的,也就是那个设计沟通情境的人。
回到自己的书,我当时有一个困难,如果作为创作者,我希望忠于我心里想的题材和我的表达方法,我希望写我想要写的东西,可我作为一个编辑,又希望管住那个写作者。我这时候采取了一个策略,让自己忘掉编辑的身份,先让这些作品被写出来,稿子聚集在一起,再用一个好像第三者的身份来看待它跟社会的关系,再跟编辑商量,甚至我把书交出来,你们怎么做我都没关系。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要改我的书名。我知道这个书名是每个出版社都想改的,都觉得这个书名太笨重,但这个书名隐藏了所有我想做的事。其实这本书在出版之前走了好几个出版社,我都觉得不合适,又拿回来了,最后在台湾给了新经典,在大陆给了中信,也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我的想法。这个想法包括了两个,第一不要改我的书名,第二不要让我放任何一张照片。大家一说这本是旅行书,有这么多地方,有这么多景观,为什么不把照片放上来?既然你都已经写了小野二郎的寿司,为什么不把寿司拍下来?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做了一个描写狂所做的事,19 个寿司写了 1 万 8 千字,已经把眼睛能看到的细节写到如在眼前一样,再放一张照片是非常奇怪的事,那是完全重复、累赘的。而且所有图片都有场景和时间,而我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日期,所以理论上它不会过期,但任何一张照片放上去,就会破坏这个结果。如果放上非洲沙漠里的照片,你马上会看出那是哪一年,因为我穿的衣服会透露,二十年后看起来,这就是一篇古老的文章。现在因为这本书的书写方式是比较古老的,所以文章看起来古已有之,它没有日期,也不会过时,这是我内心的企图。除此以外,编辑们想怎么做,我都完全支持。
单读视频:詹宏志|你住在一个叫做“朋友圈”的监狱里
那个时代一无所有,我们有一种天真
单读:
您八十年代写的台湾趋势系列,虽然有阅读的难度,却取得销量上的成功,一个原因是它和社会的节奏达到某种共振。当时您是怎么样来感知这些时代的变化?
詹宏志:
我不是因为那个社会可能在当时对这个题目感兴趣而写它的,我是基于对自己的困惑而写它的。在那个情境,对社会的动向有焦虑感,不知道它要往哪里去,不知道它未来的面貌是不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问自己,当我看到这个社会有一些力量正在发生,这些东西最后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叙述。我并不知道它跟社会会有共鸣,我不是因为共鸣而写它,共鸣是结果,是我事先不知道的事。
我做编辑的时候,也许会注意到某些书适合这个社会情境,但我自己写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包括我当时如果参与了任何社会的文化上的活动,后来看起来很重要,当时我也是不知道的。我可能从前也说过,我在参与侯孝贤或者杨德昌电影的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很重要而来工作,而是因为这是两位潦倒的朋友,你知道他们很有才气,你知道他们工作不顺利,作为一个朋友坐立难安,你觉得应该出一点力。如果知道他们后来会变成大师,我根本不会参与这个工作,就完全变成沾光了。如果我在很多台湾重要的文化事件上正好也在现场,不是因为重要所以我在那里,而是因为不管重要不重要,我都在那里。重要的事,我在那里,有更多不重要的事,我也在那里,因为我参与的事足够多,所以看上去所有的事都跟我有关。至于为什么我会参与这么多的事,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代一无所有,我们有一种天真,如果有一个朋友想做一件事,我们都来帮助,没有计算得失,没有想象他会做好或不好,不会问有没有任何资源,要不要任何代价。那个时代,我们懂得太少,我们不太知道事情做了之后,未来会如何。跟今天不太一样,今天可能我们知道太多,变成很多事不能做,因为你知道这个事做了也是徒劳无功,知道它的结果。如果有好结果,很多人愿意做,不会有好结果的话,没有人愿意做。可在我那个时代,没有这个问题,会成功的、不会成功的我们都做,那种天真和不计较,让我们可以在那么匮乏的时代做出一点事来。这个讲的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个时代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从左至右依次为: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单读:
在那些事件的过程中,您的角色依然是一个编辑?
詹宏志:
在我的朋友中,我大概始终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聚合者,这个朋友是个有才气的人,但他需要和别人一起工作,而我通常是那个帮他做组合的人,大家都当我是朋友,每个人都愿意接受我的调度安排,虽然他们并不要好,因为我在,大家也不好意思。第二个,创作或者活动一旦完成,它要跟社会有对话,那个出去寻找沟通的资源、安排沟通的设计的人,也多半是我在扮演的角色。我是一个编辑人,也是一个营销人,我比我做创作的朋友更愿意花力气去寻找沟通的方法,还有贩卖的可能,这是我特别不害怕去做的事。
单读: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恰恰是对文化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最害怕的两个工作。
詹宏志:
是,在我那个时代也是这样,大部分朋友都是,他们愿意做各种创作的工作,但没有人肯去做最市侩气的事情。我很愿意跳脱这个身份,跳脱文化上的洁癖,这些事情向来都是我在做的。
单读:
为什么呢?
詹宏志:
可能有一两个原因让我这么做,第一是我自己受经济学训练的背景,这个背景让我对市场这两个字是有一个比较谦卑的心情。如果我们要跟市场打交道,我们得理解这个市场的规律,不是让市场来迁就你,而是你要有能力跟市场对话。第二,我在学生时期就有感触,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非常有创造力,我觉得他们每个人才情都比我更高,都是一流的创作者,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些一流创作者的支持者,而不是另外再做一个二流的创作者。我很早就觉得这个社会要分工,一定要有人做另一种事,如果我们大家的背景和想法都这么相像,我们造就不了今天的生态。
单读:
您在看书的时候,也不太高低之分,比如您说过,看一本历史书和一本烹饪书,没什么区别,不太有那种对于自己知识分子身份洋洋得意的感觉,我也很好奇,是什么造就了这种人与书的关系?
詹宏志:
这正是我想象中真正编辑的角色,他明白这个社会需要阅读的内容是多元的,各种人要各种东西。这也真实地来自于我的生活经验。比如我去马来西亚,那里有六百多万华人,吉隆坡双子星大厦下面有一个很漂亮的书店,叫纪伊国屋,是一个日本书店,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书店,它的地位几乎像诚品一样,进去之后发现它有 70% 的英文书,30% 的中文书。这是一个讲马来文的国家,在这个社会想要变成一个更有知识的人,必须先学其他人的语言,光凭母语是不够的,你如果不学英文,不学中文,没有办法读到足够的书。那里面的中文书主要是商业企管、应用科学,比如桥梁工程、微积分、园艺、种菜、灌溉,这些需要中文书,所以我说在马来西亚使用中文的华人当中,有机会能读白先勇是一个福分,读不了对那个社会影响也不大,但如果他没办法取得从台湾来的财经管理类的书,他用中文来学习做生意这个链条就断掉了。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作为一个读书人,可能不小心就会有一种人文沙文主义,以为人文书才是所有书当中的高峰。可从整个社会来说,这些很具体的应用科学的书,比如一本好的育婴书,对很多新手父母都是困扰的事,这些书对他的影响比一本文学书、历史书还重要。我们能够有机会出一本了不起的书,觉得很高兴,可是没有好的儿童教养的书,整个社会也会痛苦不堪。有大量的乱七八糟的书充斥在市面上,没有人说出什么书好,什么书坏,这是很严重的,从前我在台湾也常常提醒这些做书评的版面,大众需要你告诉他哪一本育儿的书更好一些,不能所有的评论都在说哪一本小说、哪一本历史著作比较好。读者有生活上立即的需求,你却一点都没有想要帮助的意思,让他在一堆书里面自己去碰撞,这是非常无助的情况,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相信出版是一个专业,我们需要有能力为它找出各种评量的方法,而且不止一个观点。这个平衡感来自于你对社会多元情境的理解,来自做编辑的处境,你意识到你要沟通人的类别是多元的。我们不能只有一种编辑,我们需要多种编辑,各种书都要有专业性。在这个过程里我提醒自己,不要很快为书分出高下来,这个高下往往是知识的傲慢和偏见,不是对这个社会总体的帮助。
单读:
在这个时候,作为作者的那种自我,不会时不时跑出来吗?
詹宏志:
我只有很少的时间是个作者,我也没有享受太多编辑对我的服务,也很少用到作者的那一点点自由和特权。当然创作者坚持他相信的事,这是一个力量,创作的困难在于,如果你不是用那么绝对的自信,你无法坚持,因为创作者在某一个时刻要相信全世界都错了,只有他自己对了,他才有办法追求到极致,我也希望我在创作的时候能够是那样的。但创作一离开我的手边,它就变成公众的评价之物,就丢到市场上了,就要服从社会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了。我内心明白这个事,所以我的得失心不高,因为我知道如果那个书卖得不好,这个社会不需要它,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心存不平。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容易理解事情,然后心平气和,不太利用那个理解去占社会的便宜,这是我还颇引以为傲的地方。
没有一个时代会比另外一个时代更差
单读:
您现在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詹宏志:
虽然我还有一定的好奇,但我没有很大的动机要去解释这个世界了,我也没有那么多焦虑。我年轻的时候很焦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要到哪里去,因为那个世界要去的地方就是我未来要去的地方。现在我不着急了,我已经很老了,这个世界到哪里去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如果要分析这个社会,那年轻人得自己来,我没有这个义务帮他们看出来这个世界要变什么样子。我只剩下一点点时间,我要的是,在这些时间里和这个世界有一个简单和平的关系。我要过得自在一些,修补一些人生的错误,有些事我希望能够把它做得更完整,这是我对余生的想法。所以这个社会要到哪里去,我不是不好奇,只是我没有说的欲望了。哪怕对我儿子的前途有点影响,我也不关心,我也不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或者这个权利去描述它,解释它,甚至去呼吁要做什么样的轨迹修正,我一概都不做。
单读:
之前您谈过,现在大家都读电子书,其实可以得到比纸书时代更多的资讯,下一个应该更有机会做成事情。
詹宏志:
我并不完全知道答案,以现在这个社会的知识工具的条件,年轻人要比我那个时代厉害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取得知识的工具强大太多了。要问他们有没有这么大的动机,有没有像我们那时候求知那样饥渴,如果有,他可以比我们更有理想,但他有可能没有,因为分散他注意力的事太多了,从某个角度看也挺公平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感觉到年轻人要变成专家的能力要比我那个时代要容易,但要变成我那个时代那样世故和平衡会比较难。现在知识集中的过程,不一定同时要对付这个世界,这也是御宅族的意思。宅男宅女对某一个事情的偏执,可以得到足够的力量,不需要跟这个世界形成平衡。如果问我年轻人能不能做到我们80年代做到的事,我不是很确定,80 年代做的事里面有一种天真,现在这个天真相对是没有了,我看到的年轻人,都我们那个时代要聪明很多,他知道很多事是徒劳无功,很早就确定自己不会做那么笨的事。80 年代的那些事到底重不重要,我也不确定,但那就是那个时代产生的东西,也许新一代的人会产生全新的东西。我希望当他们做到的时候,我还能够认得出来,而且能够欣赏,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我对年轻人的要求。
没有一个时代会比另外一个时代来得差,如果我今天说年轻人不如我们,这个话一定是错的,我的上一辈也曾经说过,他的下一代不如他们,我也完全不服气。但某些东西确实变了,比我长一辈的人花在某些东西上的时间比我们多,比如写字,从整体上看,上一代比我这一代写字写得好得多,这是很自然的事。现在看我的下一代,能写字的人就很少了。但这不是要紧的事,每个时代有它要紧的事。

单读:
但您现在的工作依然在处理和新技术相关的项目?您还对这些感兴趣?
詹宏志:
只要是我没做过的事,我都感兴趣,我要常常提醒自己,别做太多事,因为人生有限。我现在是过去很多、未来很少的人,我应该善用未来的时间。这些时间其实不应该开启新的事,应该修补过去没有完善的事。是我工作一不小心就跑去做比较多新的事,那是我的个性使然,并不是我应该做的事。
单读:
新书也是在处理过去的事吗?
詹宏志:
我想写的书都还没写呢,现在出现的书都是因缘际会,在某种情境下写的。我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力气能写我想写的东西。你看《旅行与读书》这本书前后写了六年,我是一个很慢的人。我没有几个六年了,所以我也不会有太多书了,应该把力气放在哪里,我自己得很小心。
单读:
您以前就这样说过,但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詹宏志:
是没停下来,这次再提醒我一次。
单读:
尽管在我们看来您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了,但您自己心里有没有遗憾?有没有特别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
詹宏志:
每一天都有,我内心当然有很想做的事,不过好像这一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机会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做觉得当下应该付起责任的事。朋友做不了的,我应该去做,工作伙伴希望我做的事,我应该去做。我花在这里的时间,被责任感驱策的时间多,满足自己愿望的时间少。我每次都想说,先把这个做了,再回来做我想做的事,怎么一转眼六十岁就到了呢,好像什么事也做不了,这种感触特别深。我开玩笑地把胡适的诗改一改,的确有点像我生平的写照:清夜每自思,此生非我有,一半属工作,一半属朋友。最后做的事,一部分是为了某种公共的利益,一部分是为了朋友的艰难,没有把一生留在自己手上,半是自嘲,半是感慨。
单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