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出生的张文尝过穷的味道,张文身高1米75,来自陕西榆林子洲县,讲普通话带浓郁的陕西腔。
榆林是红军长征后待过的地方。老家人传说毛主席在那胖了三十多斤。现在榆林产煤、石油,少数老板因此致富,但跟张文家这样的普通人家关系不大。
2012年,张文从陕西老家村里考进太原理工大学。当时他黑黑瘦瘦,体重120斤。
大学一年级有天下午,张文发现饭卡里只剩两元钱。加上银行卡和兜里几个铛铛响的硬币,一共六块多。
六块多能吃什么?张文有点发愁。食堂馒头卖5毛一个,张文决定去买馒头吃,总能填饱肚子。在食堂刷卡时,他惊喜地发现饭卡里突然多了100多块——国家给贫困大学生发的补助到账了。
靠这100多,张文撑了一个星期。
掌握自己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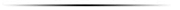
张文第一次开始琢磨“阶层固化”这个概念正是大学一年级。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城市,在当时的张文看来都是“非富即贵”——至少不用像他一样,担心下顿的馒头。
张文高中同学郑玉峰比他小一岁,高考发挥得比他好,考进西安交通大学。郑玉峰肤白眼细,笑起来像男版林忆莲。他来自陕西榆林横山县,家庭条件比张文稍微好一点,能交得出一年5000元的学费。
张文跟郑玉峰从高中起就走得很近。上大学后,他俩常讨论怎么打破“阶层固化”。他们觉得,自己的农村背景,如果按部就班读本科、硕士,找工作,很难出人头地。
“能混个中产以下或中产就已经算很不错了。”这两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尝试过不同的法子打工赚钱。张文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给高中生补习。他请了几个博士、硕士来讲课。
老师好找,学生难寻。为了招学生,他坐公交、骑自行车去太原的小区里贴传单。小区保安见他就赶,运气不好时,还有野狗追着他咬。张文觉得这模式难以持续,把补习班关掉了。赚到几千块钱,他买了台笔记本电脑。
大一下学期,张文去西安交大找郑玉峰,在图书馆看到丁鹏写的《量化交易:策略与技术》。书里一句话打动了他:“喜欢做一名宽客,是因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张文从来没有做过量化交易,但他隐约感觉到,这是一个方向。
大二上半年,张文瞒着父母从太原搬到西安交大,住在郑玉峰宿舍,和他一起研究量化交易。他和郑玉峰开始上各种论坛和QQ群,自学VBA语言。他俩嫌量化交易的软件太贵,就用Excel里面的VBA编程连接CTP(上期技术的综合交易平台简称,期货自动化交易接入API的一种)做期货交易。
那段时间他俩也没忘记赚外快。
他俩发现,同一款手机,淘宝上有人标价3500,有人标价2500,高和低的都有买家。两人做了个类似于“搜同款”功能的网站,让人可以用一个中间价从他那里买到手机。
他们不囤货,不发货,跟淘宝信誉不错的卖家合作,赚差价。张文和郑玉峰前后卖了100多台手机,赚了一万多。郑玉峰记得当时卖得最火的手机是那款长得很像数码相机的三星S4 Zoom。
虽然赚到了钱,他俩担心自己没资质、没仓库,量上去了,会有法律风险。“虽然是套利,搞不好被人告是诈骗。”张文说。
2014年,张文和郑玉峰把手机网站关了。这时,他俩技术能力增强,对自己的期货交易模型感觉良好,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钱,炒期货!
第一桶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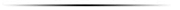
张文和郑玉峰不少初高中同学早几年已经出门打工,手里有些积蓄,虽然搞不懂“量化交易”是什么,但都蛮信任他俩,几万几万地塞给他们。
两人很快就筹来三十万:最多的一笔四万,最小的一万。借钱做交易,张文和郑玉峰压力不小。
“我心里想如果实在亏了,就变成我俩各负债15万,毕业之后自己去找工作,慢慢还也还得起。”张文说。在学校,张文和郑玉峰就一门心思学编程、打工赚钱,经常翘课。这下两人开始炒期货,更成了大家眼里的“败家子”,引来周围许多同学异样的眼光。
期货交易有夜盘,郑玉峰的宿舍要断电,张文又从西安交大搬回了太原。他找学院借来学生会的办公室交易。办公室24小时供电。晚上交易完,张文就睡在充气床上。
张文和郑玉峰把钱全部投在了自己研发的期货中高频策略上。做得最多的品种是被称为“小股指”的橡胶。
大半年时间,他们借来的三十万翻到了200万。张文把这归功于运气。“现在看来,当时建的模型一般,还是机会把握得比较好。”尝到了期货市场的暴利,张文和郑玉峰的第一个想法却是不能再做期货了。
“期货比股市理论上更成熟,比如是T+0。但是越成熟的市场,你很难去赚。多空各种信息都会引领某个方向。”他俩把钱加分红还给同学,就开始注册公司,打算做股票交易。
西安交大曲江科技园免费给了他俩一个50平米的办公室。张文又多租了50平米,房租一年一万多。那时张文和郑玉峰加了许多量化交易的技术群。张文常在群里发言,和群里一位成都的先生成了朋友。
这位老兄做矿起家,后来转做金融,不怎么顺利。他专门从成都开车到西安,张文陪着他逛了三天,喝了三天酒。
“成都人的酒量跟比我们差,其实技术上就简单说了一两句,感觉我大口喝酒,打动他了。”张文说。成都老板成为张文和郑玉峰的第一位客户。
2014到2015年,张文团队攒了20多个客户,几百万规模的理财,赚了钱就提成20%。从2015年初开始,两市持续上升,势头猛烈,张文和郑玉峰的代客理财做得风生水起。赚到第一桶金,他俩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质的改变。
郑玉峰在老家市里给爸妈买了套118平方米的房子。当时均价7000元每平米。张文把自己的手机和电脑换成了苹果。他回榆林的周大福专卖店,花四五万给妈妈买了一套粗的金首饰:手镯、耳环、项链,因为“她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妈妈热泪盈眶,但首饰戴几天就收起来了,说要留给儿媳妇。“我说妈你赶紧戴吧,媳妇不要这些。”张文说。
当上了“暴发户”,张文觉得以前眼里“非富即贵”的同学“都好穷啊”。“他们去学校食堂吃饭,15元钱以上就舍不得吃了。我就大鱼大肉,天天去食堂里吃饭,随便点,随便吃。”
张文很少为自己花钱,但对亲人、同学和女朋友都很慷慨。
赚到钱后,他带80多岁的爷爷旅游,坐飞机,坐高铁, 给女朋友买包包。高中和初中同学从外地来找他玩,他就给他们报销吃住。有朋友做生意找他借钱,他爽快地给借了几十万。
“以前我穷的时候就对朋友很大方,有钱了也是一样。”
搞个大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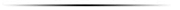
2015年,中国A股越来越火爆。5月22日,上证综指高开,收盘涨到4657点。这一天,北京《新京报》上出现了一张惹眼的“挑战书”。
温城辉、余佳文,5月24日9点,北京前门建国饭店,比比谁才是真正的90后最强创业者!你们敢来吗?
署名:张文。
挑战书占了整整半版,跟着印了一个巨大的二维码。
温城辉、余佳文是当年“90后互联网创业”的红人。余佳文的“超级课程表”项目获得了阿里巴巴的千万美金B轮投资。温城辉的“礼物说”项目获得了红杉资本数百万美金的 A 轮投资。
张文想利用别人的噱头,给自己的基金路演会增加点曝光。“我就是想搞个大新闻。”张文和郑玉峰都不再满足于代客理财,发基金才能有公开的业绩和长久的发展。

张文在《新京报》刊登的广告
半版广告《新京报》要价十几万。张文砍到了5万,他觉得这个钱该花。广告刊出来,张文和郑玉峰傻眼了。二维码在报纸上放大之后,也许是清晰度偏低,手机居然无法识别。
在建国饭店,他俩租下300多人的场子,只来了100多人。张文发基金的渠道方是北京某期货公司。期货公司联系人看到张文的学生样,有点不以为然。
“他问我发多少,我说3000万。”张文承认自己对能募多少钱心里还是没底,但他认为几百万肯定是有的。路演后第一个礼拜,张文和郑玉峰只募到了四五百万。他俩赶紧找以前的客户,好说歹说筹来3140万。
6月18日,A股在4900点位置时,张文开始建仓。两市午盘后跳水,收盘沪指跌3.67%,创业板指暴跌6.33%。6月19日,建仓第二天,沪深两市千股跌停。张文和郑玉峰的产品两天浮亏10%。
“当时就感觉人生又完了。”张文说。
6月20日,张文和郑玉峰当机立断,把仓位全部清掉,决定从多头策略策略转做Alpha策略。Alpha策略维持市场中性,如果股票买入1000万,他俩会做空等额市值的股指期货进行风险对冲。
“之前(多头策略)赚钱太不踏实了,Alpha策略可以规避股灾,最起码不会亏得很多。”
他俩保持30%的仓位上Alpha策略,基本毫发无损地度过了A股从8月18日开始的一周内超过1000点的下跌(这被称为“第二轮股灾”)。
到2015年年底,他俩接近满仓,把基金净值做回到1。有客户撤资,有新客户进来,规模持平。谁料到,一过元旦,熔断又来了。
2016年1月4日,新年首个股市交易日,沪深300指数跌幅达7%,两度触发熔断机制。1月7日,再度触发熔断机制,全日交易不足15分钟便提早收市。这天基金回撤4%,但他俩很平静。
“其实说实话,做Alpha就是等着这种事情发生的。发生的时候,你的压力会小很多。” 到2016年年底,他俩把基金做到了1.23的净值。
信息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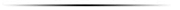
2016年年底,张文和郑玉峰跟其他几位合伙人出现分歧,六个人分成了三拨。张文和郑玉峰从当时办公地杭州搬到了北京。最开始办公室租在丰台,后来从丰台搬到中关村。
说起在北京注册公司,张文一肚子苦水。公司本来打算注册资本1000万。但工商局说,1000万以上,必须叫业主的公司法人代表去工商局签字。
“我说人家房东是国企法人代表,官那么大,我见都没见过面,怎么干这个事。”为了绕过1000万这个坎,张文和郑玉峰把注册资金定在999万。
虽然说北京的生活成本是杭州的三到四倍,但是张文很快发现,这里人才的优势是杭州十倍以上,特别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人家就是又聪明又勤奋”。他俩死死盯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人工智能”方向的大学生招。这是他们的策略十分需的人才。
“比如我们的数据维度是4000维度,股市有3000多只股票,它一天的数据是3000乘4000。人工方法已经完全不能处理这个事了,所以说只能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来处理。”
张文的建模理念很简单——超额收益必定来自于超额信息。“两个国家打仗,你掌握对方情报很多,胜率越大。再举个例子,徐翔,他自己就是内幕,就是超额信息。”张文和郑玉峰自认跟同行比,最大的优势是他俩有更多的优质数据。
市面上,数据公司能卖四五百个因子,但他俩有4000个因子。基础数据库之外的因子,都是他俩自己找的。
“比如说舆情数据库,某个股票的关键字搜索频率,最近一个礼拜的增长率,跟其它股票的相关性系数,不同的周期不同的相关性系数,都可以作为一因子。”张文比喻说,如果说所有因子加起来可以组成一个人的图像的话,头发有多少根也是作为一个因子,鼻子、眼睛、身高、皮肤,哪块皮肤有斑点,都可以作为因子。
“你不要嫌它复杂,不要嫌它麻烦,可能会有重合和不相关,但是越详细是越好的。”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资深量化基金经理告诉我,张文说有4000多个因子并不夸张,因为有时一个因子会有多个变种,“重要的是有效率的因子有多少个”。
张文和郑玉峰跟清华、北大实验室合作,把数据给实验室,让他们分类、评级,从第1名到第3000名。他们每天会做排名,一天一个Excel文件。“你收益最高的票肯定是前50名或者前100名。”
讲到这,张文打开一个Excel文件指给我看。
“纵列相当于投资标的,投资标的我们都是加密过的,横的就是相当于每个特征值。虽然是4000多个,但我们分析之后,可能会有几百个因子没有用,所以我们有时候给他们实验室的时候,直接把那些删了。让他们稍微轻松一点。”如果实验室提前交结果,他们会给实验室额外奖励。
野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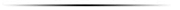
2017年3月,我去中关村拜访张文和郑玉峰。
办公室在知春路的一栋不起眼的大楼,离北大东门几百米距离。大堂站着位执勤保安,穿军大衣,戴皮帽,衣袖上绑着个红袖章。跟他俩同层的邻居大多是IT公司,其中包括腾讯。
办公室前台装修了一半,墙壁半秃着。“去年年底雾霾比较严重,不让装修,今年两会来了,又不让施工了。”张文解释说。

张文(左)和郑玉峰在中关村的办公室
搬进新办公室,张文找北大某道教协会的道长来指导风水。道长通过微信指点,说办公室只能买红色的花,总数不能超过8盆。张文一一照办。他在微信上打赏了道长1000元。
去年12月,两人开始申请基金备案,到春节前备案通过,春节后刚刚开好户开始做。张文和郑玉峰告诉我,现在公司加上他俩一共有12名正式员工。公开管理规模3亿多,私下还管了几个亿。
这两个大学没有毕业的年轻人报出这数字时,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不了。跟传说中长征后的毛主席一样,张文比2012年考入大学时胖了30斤。郑玉峰还是瘦瘦的。
他俩纷纷在各自学校办了休学,但每周都跑到北大清华去旁听人工智能方面的课。张文告诉我,过两年,他还是想回学校把学位拿到手,然后去读个清华的EMBA。“中国讲究出身,我现在都不敢把我简历往网上放。”
这是个竞争已经白热化的行业。张文和郑玉峰知道跟自己在市场上抢钱的,不少是从华尔街回来,在国际金融机构经过严谨训练、头戴光环的牛人。“其实我们的优势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路子比较野一点,自己琢磨的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张文把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能力等同于“创新能力”。他说,去年股灾之后,如果不创新,传统Alpha策略根本没法做,基差成本都覆盖不了。今年的行情“感觉比去年更难赚钱”,张文研发压力很大。
他们在策略里加了一些新因子,最近跑下来,效果还不错。模型每周都要微调,新股发行速度加快,新因子加上去之后也要不断调试。张文认为,他和郑玉峰在量化交易这条路上走得比较顺,是因为风格切换非常及时。
“比如说我一直做期货可能会做得破产,如果我一直做股票(多头),我2016年就没得发展了。这个很关键,路对了,你去奋斗才有成功的概率。”
从单打独斗到带领一个团队,张文和郑玉峰在管理上琢磨出了自己的路数。现在公司员工绝大部分北大清华毕业,最小的1996年出生,不少都是奥赛奖牌获得者。公司还有三十多个实习生。
员工入职时,张文会跟他们一起制定学习计划,事先约定,比如把这门语言学会了,就涨50%工资。
表现不佳者,则被迅速淘汰。
张文“开掉”的第一个人是位北大毕业生。张文觉得直说有点难以启齿,就公布了严格的考核机制。这位员工收到邮件就主动提出辞职。辞职信里,他承认自己“智商不够”。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张文和郑玉峰已经开除了十几个人了。“就是不停地招人,不停地换血,很残酷,但是也没办法。只有公司在,你才有利益,公司不发展,你什么都没有。
张文跟郑玉峰和公司所有员工都住在离公司5分钟步行距离的小区。房租由公司承担,员工伙食补助一天50元。张文认为这能保证员工在通勤上不消耗体力,上班状态良好,“其实很划算”。
搬到北京不久,张文请他爸妈来北京,带他们逛天安门,参观他的办公室。父母始终搞不懂儿子在做什么,心里很忐忑。老两口反复叮嘱儿子:“这行业是不是挺危险的?赚钱可以,千万别做犯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