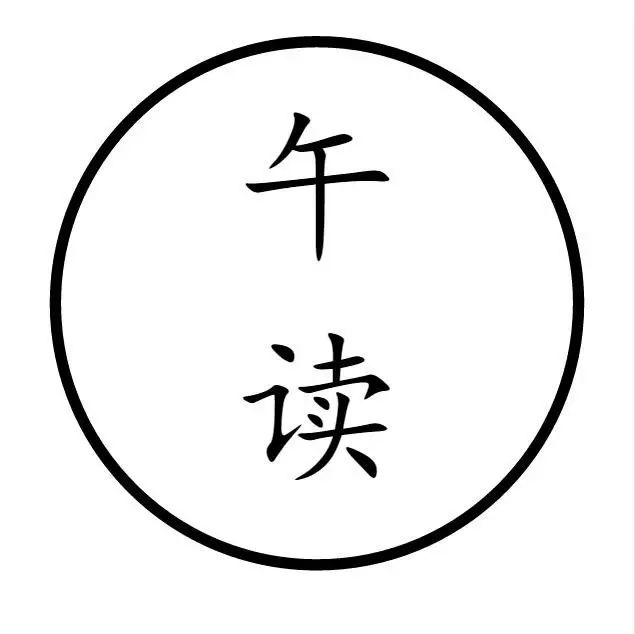编者按:
在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24美国大选之后,界面文化专访了波士顿学院法学博士、美国政治长期观察者王浩岚。他提到,疫情四年的创伤记忆不仅改变了美国选民的政治偏好,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右翼政治的崛起。经济问题,尤其是通胀对选民的影响,成为了今年美国大选的决定性因素。
2020年,界面文化曾专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誉教授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她也是《故土的陌生人》的作者。在采访中,她提到了大流行病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可能影响,比如加剧了美国人对专家和政府官员的不信任,比如郊区“温和右翼”共和党人更有可能转向民主党候选人——显然,这在今年并没有发生。
2016年9月,《故土的陌生人》在美国出版。当年年底,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此前主流民调皆显示克林顿将获胜,而且特朗普在大选期间的种种打破常规的极端右翼言行让他看上去非常不像一位寻常意义上的政治家。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事实迫使沮丧不已的自由派美国人去思索背后的原因,霍赫希尔德的这本书对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答案。
在旁观此前特朗普的竞选集会后,霍赫希尔德在书中总结道,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失落的美国人的情感:“特朗普是个‘情感候选人’。与数十年来的其他任何总统候选人相比,特朗普更加注重激发和称赞支持者的情绪反应,而非叙说详尽的政策计划。他的演讲——令人产生主宰、张狂、明晰的感觉,以及国家自豪感和个人振奋感——会激发一种情感转变,然后他会指出这种转变。”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6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在选举之夜观战活动上发表讲话提前宣布赢得大选。(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2011年到2016年,这位以研究情感、女性和家庭闻名的社会学家频繁前往深红州路易斯安那州,采访了60人,其中包括40位茶党支持者,她拜访了他们的家、社区和办公场所。在写作《故土的陌生人》的过程中,她融合了许多社会学研究方法,比如焦点团体访谈和参与观察——在早年的名作《第二轮班》中,她也运用了这种沉浸式的深入研究方法。在与当地那些深受钻探工业所害的乡村白人小资产阶级交往的过程中,霍赫希尔德试图通过理解一个“锁孔问题”——政府监管严重不足的大型石油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但为什么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人依然维护大型企业和“自由市场”,指责政府监管——来解析右翼的意识形态。
霍赫希尔德指出,要了解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需要首先了解那个人对政治问题投入的情感,她将之称为“深层故事”(Deep Story)。美国右翼的深层故事是这样的:他们相信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公平竞争获得阶级跃升,然而爬上山顶实现美国梦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过去几十年来薪资水平停滞、经济不平等拉大,这种经济打击对制造业和手工业从业者来说尤其沉重。与此同时,他们还面对着此前排在队伍更后面的弱势群体(女性、少数族裔、移民和LGBTQ群体)的上升压力,这些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让他们感到被别人“插队”了。
是这种挫折感令右翼转向反对左翼倡导的平等、自由和多元包容,使他们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邮件采访时,霍赫希尔德特别指出,日益稀薄的经济机会不应被视作右翼深层故事的全部成因,它的形成其实事关一种整体性的失落感,“核心问题不是贫穷(deprivation),而是失落(loss)。而且这不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失落,还是种族地位、地区和宗教自豪感、文化主体性。”许多右翼美国人由是倒向了特朗普的阵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誉教授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
霍赫希尔德她呼吁自由派跨越“同理心之墙”,去理解保守派的忧虑与关切,去讲述自己的愿景,去重建社会共识——政治分歧两端的人的敌人不是彼此,不是社会弱势群体,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书中最后一章,她在一封虚构的给路易斯安那州右翼朋友的信中如此描述属于左翼的深层故事:
“在这个深层故事中,人们站在一个大型公共广场周围,广场里有创造性十足的儿童科技博物馆、公共艺术与戏剧演出、图书馆、学校——最先进的公共基础设施,可供所有人使用。他们对此充满自豪。其中一些人是其建造者。外人可以加入广场周围站立的人群,因为许多现在的圈内人也曾是局外人;吸收及接纳异己似乎是自由女神像所象征的美国价值观。但在自由派的深层故事中,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强盗闯进了公共广场,对其大肆破坏,自私地偷走了广场中心公共建筑的砖头和混凝土块。雪上加霜的是,守卫公共广场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破坏分子用那些砖头和混凝土块建起私人高楼大厦,将公共领域私有化了。那便是自由派深层故事的核心要点,而右派无法理解自由派对他们设计新颖、来之不易的公共领域深深的自豪感——自由派将其视为美国生活中一支强大的融合性力量。讽刺的是,你与左派的共同点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多,因为左派中的许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是故土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