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发现了个“失眠福音”。
睡觉有了它,太舒服了——
《听说》

说来你可能不信,这是一部“
闭着眼睛也能看完
”的网综。
怎么讲?
首先,它
纯粹
。
形式上类似于一档电台节目,由安静的美男子
马世芳
老师担任DJ。
不请嘉宾,也没花招,在微黄的灯光下娓娓道来,就能带你进入另一片天地。

其次,它
好听
。
听过的人都说——
怀孕了……
当然是耳朵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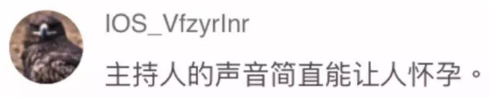
关键是,听完了,它更会给你意想不到的
发现和感动
。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层出不穷的歌星真人秀、音乐选秀节目,那么《听说》无疑是一股清流——
它深扒乐坛,却不见一条八卦;
播着比你还老的歌,却感觉是久别重逢;
聊的是音乐,却每每有弦外之音。
这档调性典雅的网综,第二季一回归,豆瓣再次
9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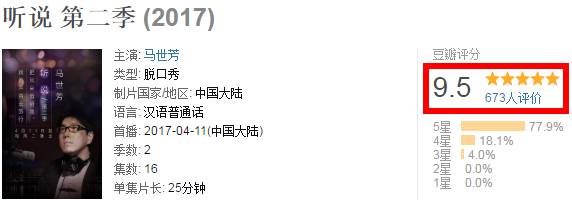
然后,默默被它的一小撮粉丝欣赏着……
每集的点击量,就
十来万
。
好冷啊,是不是?
但要知道,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音乐太少,而是音乐太多、太吵。
就像在一条嘈杂的大街上,为了盖过隔壁的声浪,每一家都想把自己的喇叭开得更响。
结果呢,大家想听的听不到,听到的都是不想听的。
这两种音乐的区别就是——
一个
洗涤
你的耳朵,另个一则
洗劫
你的耳朵。
马世芳的《听说》,或许就是你想听,却没来得及听清的那一个。
李宗盛曾这样说过他的“世芳老弟”——
在众声喧哗时代中,为尽心尽力的音乐人挣些许尊严;在荒谬浮夸行业里,替混沌不明的现象给出诤言补白。
这样的《听说》,谁也不能错过。
《听说》太卓尔不群了。
它掌握
第一手内幕
。
马世芳生于1971年,但入行已有37年了,第一次播音是在九岁。
母亲陶晓清是著名广播人,也是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
这样的家学背景,让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对一票音乐人知根知底。
1976年,李双泽在淡江大学的西洋音乐会上,向众人质问:“
你一个中国人唱英文歌是什么滋味?
”
这就是华语音乐史上著名的“淡江事件”,当时台上的主持人,正是马世芳的母亲。
而马家的客厅,堪称华语流行歌坛的小基地。
从民歌领袖杨弦、李双泽、胡德夫,到后来的乐坛中流砥柱罗大佑、李宗盛,都是常客。

还捕获一只年轻的金士杰
什么是台湾民歌运动?
简单说,它的地位,就相当于一场华语音乐的“白话文运动”——
身影虽已远去,影响却潜入了后人行为方式的深处。
“民歌运动”开一时之风气,才有了台湾歌坛后来鼎盛的时代,乃至今天你到KTV也要唱上一两首的周杰伦、五月天、S.H.E……都无不在“民歌运动”的长波辐射中。
那“民歌运动”以前呢?
看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知道了,电影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就来自于猫王的一句歌词。
那个时候,时髦的是美国驻军带进来的乡村民谣和摇滚。
电影里的“小猫王”,一句英文不会,也要背发音,唱英文歌。

“我们自己的歌”呢?
(李双泽之问)
老歌,嫌土;新歌,没作品。
民歌运动可以说是,
为耳朵找回了听母语的习惯
。
其中流传最广的歌,你肯定听过——
《橄榄树》。
齐豫演唱,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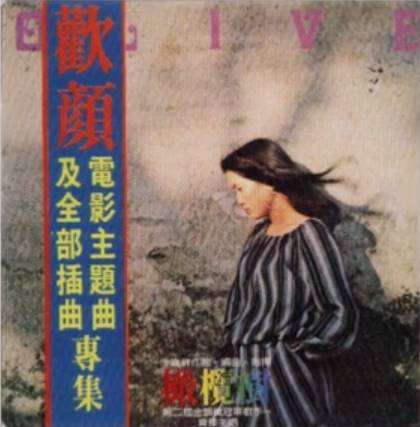
开头谁都会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但背后的事,你未必了解。
马世芳说,这首很梦幻、很抒情的歌,居然也
政治敏感
……
哈?!
没错,你只要联想当年国民政府的处境,再看“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流浪”这两句,就知道G点在哪了。
民歌运动中,还有一首深具影响力的歌——《美丽岛》。
作者李双泽因为下海救人,发生意外,他的一生只活了28岁。朋友杨祖珺和胡德夫,在他出殡的前一天,赶录了他还没来得及发表的《美丽岛》。
听过这个版本的都会疑惑,结尾一句唱到——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为什么杨祖珺的歌声断断续续,最后突然消失了?
马世芳当面问过她,是不是想到亡友,哽咽了?
谁知道她说,才不是咧,我是笑场了,哪有人把香蕉写进歌词里的!
对于这些事情,马世芳都如数家珍了。
《听说》的好,当然不止于爆料。
它靠开阔的视野、精辟的见解,令你
豁然开朗
。
你看他对罗大佑和李宗盛的评价,是不是说出了你的心里话——
罗大佑始终是沉郁而孤傲的,时时把整个时代挑在肩上,连情歌都满是沧桑的伤痕。
李宗盛则擅长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提炼诗意,煽情而不滥情,轻盈而不轻佻。
当你情伤难抑,罗大佑将让你感觉凄清悲壮,李宗盛则让你认清,自己不是世间唯一懂得寂寞的人。
有时他又会穷根究底,告诉我们那些耳熟的旋律是如何漂洋过海而来。
比如《送别》,长亭外,古道边……
这首歌是李叔同到日本留学时听到,重新填入中文后带回来的。
但其实这首歌最初是美国歌谣——《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一位学医的年轻人为了排遣思乡之情所写,在南北战争期间被传唱。
《玫瑰玫瑰我爱你》追究起来,很不政治正确,原歌就叫《Rose Rose I Love You》,歌词是白人大兵对亚洲女郎的轻佻描写。
也有例外,比如“出口转内销”的《何日君再来》。
《听说》对这首歌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爬梳——
最早是1937年出现在电影《三星伴月》中,由17岁的周璇演唱;
后经“满洲国”的电影明星李香兰翻唱,红到了日本;
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1978年邓丽君演唱的版本。
从上海,到日本,再到台湾,简直是一首歌的“三生三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