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徐忠兴
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在重新整合2018年《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第六十三条及《九民纪要》第十一条第二款的基础上,规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修订亮点是增加规定了横向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并将2018年《公司法》确定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独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扩张适用于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本文根据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需求,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实务应用中的44个常见问题予以简要解答,以飨读者。
答:公司人格否认,又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美国称“揭开公司面纱”,英国称“刺破公司面纱”,德国称“直索责任”或“责任穿透”,日本称“透视理论”,是指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要求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述行为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否认被股东控制的其他公司的法人人格,要求各公司之间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人格否认始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法院判例,其后为各国及地区所仿效,并发展成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共同认可的法律原则,但都没有采用成文立法来规定。我国自2005年《公司法》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成文法方式规定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国家。公司人格否认中的“否认”,并不是指公司人格的丧失,此时公司并不会进入解散或者清算等程序。公司人格否认只是一种形象比喻,其实质是无视公司的独立地位,将公司股东和公司视为一体,股东因此丧失以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保护,从而判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可见,公司人格否认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股东有限责任的修正和维护,平衡公司股东与债权人的风险与利益。
延伸阅读:①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87页;②周友苏著:《中国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01-102页;③曹守晔主编:《公司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73页;④周游著:《新公司法条文解读与适用指引:案例·规则·文献》,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48页。
答:根据公司人格否认的方向,公司人格否认可以分为纵向公司人格否认、横向公司人格否认和逆向公司人格否认。其中,纵向公司人格否认,是指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在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当转移风险和利益,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通过否认公司的人格,使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公司人格的纵向否认;横向公司人格否认,是指股东利用其控制的数个关联公司或其他公司实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在各关联公司或其他被控制的公司之间不当转移风险和利益,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通过否认各关联公司或其他被控制的公司的人格,使各关联公司或其他被控制的公司之间对对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公司人格的横向否认;逆向公司人格否认,也称反向公司人格否认,是指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向公司不当转移风险和利益,严重损害股东债权人利益的,通过否认公司的人格,使公司对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公司人格的逆向否认。
纵向公司人格否认与横向公司人格否认是以连带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投资与被投资关系为标准对公司人格否认类型所作的区分。前者的连带债务人(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投资与被投资关系,后者的连带债务人(股东控制的数个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持股与被持股的关系,而是由同一股东持股控制或实际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逆向公司人格否认也应属于纵向公司人格否认,两者的连带债务人同为股东与公司,只是公司人格否认的方向不同而已。
《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纵向公司人格否认,纵向公司人格否认在实务中最常见,也是本来意义上的法人人格否认。《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一人公司人格否认也属于纵向公司人格否认。《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了横向公司人格否认,即“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款吸收借鉴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11条第2款的规定。《公司法》并未规定逆向公司人格否认,但我国学者普遍认为逆向公司人格否认是公司法人理论发展的必然,《公司法》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规定可类推适用于逆向公司人格否认。司法实践中存在支持逆向公司人格否认的判决。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北京长富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武汉航天波纹管股份有限公司、中森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中森华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2158号)的民事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目前司法实践中,在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下,公司亦可为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裁判将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扩展到逆向人格否认,即公司对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李建伟主编的《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认为,逆向公司人格否认的价值有限,股东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执行该股东对公司的股权,大多数情形下足以满足其偿债需求。
延伸阅读:①刘斌编著:《新公司法注释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108页;②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90-91页;③曹守晔主编:《公司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73-74页;④王毓莹著:《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15页;⑤王瑞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释义丛书),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39页。
3.
纵向公司人格否认与横向公司人格否认能否同时合并适用?
答:纵向公司人格否认和横向公司人格否认能否同时合并适用,既纵向否认公司人格,也横向否认公司人格,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同时适用,公司债权人要么可以要求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要么要求公司股东控制的数个其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不能同时要求公司股东和股东控制的其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两者可以同时适用,在否定公司人格的情形下,公司债权人可以同时要求公司股东和股东控制的其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新《公司法》修订过程中的讨论,第二种意见更符合立法本意。如果公司股东既有《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又进行了该条第二款的滥用行为,则可以在否认公司与股东之间的独立人格(纵向否认)的同时,否认该股东控制的各个公司的人格(横向否认),公司债权人可以同时依据这两款,要求股东与公司、公司的姐妹公司、公司的兄弟公司以及其他被股东控制的公司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当然,控制股东是否需要与被控制的公司一样承担连带责任,取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可依职权追加。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南省伟祺园林有限公司、王红军、张强、张坤、河南伟民置业有限公司、河南伟祺置业有限公司与唐新亮、苏州科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合同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1106号)的民事裁定中认同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适用公司人格横向否认与纵向否认的二审判决。
延伸阅读:①刘斌编著:《新公司法注释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110页;②赵旭东主编、刘斌副主编:《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54页;③赵旭东主编、刘斌副主编:《新公司法适用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解读》,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72页。
答: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纵向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对象仅限于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只有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股东才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通常为控股股东(持股占50%及以上)或者控制股东(持股虽不足50%,但足以达到控制的地步),那些无权也无机会实施滥用行为的其他股东不应承担此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实施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涉及公司实践中的参与公司决策和未参与决策的不同情况。如果股东参与了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公司决策并投了赞成票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无论其是控股股东还是非控股股东,都应当视为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都应当对公司人格否认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股东没有参与违法决策或完全不知道违法决策,则不应当承担公司人格否认的责任。在两个以上股东参与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公司人格否认触发的是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关于“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的规定,应当根据参与股东所处的不同地位、发挥作用大小及其过错程度来确定所承担的责任;无法确定的,应当平均承担责任。
延伸阅读:①周友苏著:《中国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09页;②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88页;③曹守晔主编:《公司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74页;④朱慈蕴主编、沈朝晖、陈彦晶副主编:《新公司法条文精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44页。
5.
公司实际控制人能否成为公司人格否认的责任主体?
答:根据《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这一规定表明,实际控制人由于其能够实际支配公司,完全有可能也有条件利用自身地位从事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按照股东滥用公司人格同样的道理,实际控制人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对公司的控制权获得不当利益,导致公司不能偿债的,债权人可以将实际控制人视为实质股东或者事实股东,提起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将非股东的实际控制人纳入责任主体应当比公司人格否认一般案件的法律适用更为严格和谨慎。最高人民法院在“佛山市南海能顺油品燃料有限公司、杜某1、杜某2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西石油分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终30号)的民事判决中指出,杜某1、杜某2作为能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能顺公司收取的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款项无充足合理原因转付给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广东省肇庆市能源交通贸易有限公司、佛山市隆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个人之后,使能顺公司在不能履行与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情况下,亦无能力及时退还其所收取的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购货款,从而严重损害了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的利益。因此,原审判决类推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编者注:对应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杜某1、杜某2应当对能顺公司所负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能否将公司人格否认扩张适用于实际控制人,《九民纪要》第11条第2款在规定横向公司人格否认规则时已有肯定性规定。
延伸阅读:①周友苏著:《中国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09-110页;②朱慈蕴主编、沈朝晖、陈彦晶副主编:《新公司法条文精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44页;③周游著:《新公司法条文解读与适用指引:案例·规则·文献》,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48页;④云闯著:《新公司法司法实务与办案指引》,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364页。
答:对此,学者有肯定说和否定说等不同观点。王毓莹编著的《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认为,名义股东仅在其实际参与实际出资人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情形下,方可要求其承担责任。一方面,隐名持股并非单一类型,实际出资人滥用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往往是名义股东仅持股,而不参与公司经营,也无法了解公司经营情况,以代持股关系的存在径直要求名义股东承担监督义务显然并不符合实际,对名义股东而言亦是强人所难;另一方面,主张按照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的过错过错大小认定责任是一种侵权法的路径,侵权法对“过错”的要求往往是基于满足受害者“泄愤”的考量,但在商事活动中,严格责任往往比过错责任更加有效,因此仅以名义股东代持股时有过错就要求其承担实际出资人滥用公司人格的责任,不符合私法的要求,反而更像是一种惩罚。因此,仅在名义股东实际参与实际出资人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时,基于其股东身份,方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令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延伸阅读:王毓莹著:《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01-102页。
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隐名出资人也称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构成合同关系,并不具有当然的股东身份,因此不能将其直接视为股东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规定。公司实践中,隐名出资人的情形比较复杂,有的处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有的仅仅处于一般委托人地位,完全通过名义股东来行使自己的权利,甚至其他股东也不知道其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因此,对于隐名出资人能否作为公司人格否认的责任主体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处理。对于那些虽未显名但已经处于实际控制人地位的隐名出资人而言,如果其从事了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可以参照前述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处理,让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如果隐名出资人是通过名义股东实施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原则来处理,即名义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隐名出资人追偿。
延伸阅读:周友苏著:《中国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10页。
答:公司实践中,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往往可能是由作为公司的经营管理者的董事、高管具体实施的。董事、高管在公司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承担着法律规定的特别义务和责任。如果董事、高管具有公司股东身份,一旦实施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在法律适用时当然应当成为责任主体,即可以以其具有的股东身份让其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董事、高管不具有股东身份,一旦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在法律适用时就会出现责任主体不适格的问题。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与董事、高管执行股东会违法决议的行为属于两种在性质上有差异的行为。前者是股东的违法行为,应直接对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后者是董事、高管的职务行为,应按照履职过错情况来承担责任。鉴于责任上的差异,公司董事、高管实施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对其履职违法的责任追究都应适用《公司法》关于董事、高管义务和责任的规定(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一条),或者说按照违反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规定(第一百八十条)追究责任;如果其具有股东身份,在作为股东承担公司人格否认责任的同时,并不能免除其作为董事、高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王毓莹编著的《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认为,以违反信义义务的方式追究不具有股东身份的董事、高管的滥用责任固然符合公司与董事、高管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但从结果和效率上都对债权人不利,故将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不具有股东身份的董事、高管具有合理性。
延伸阅读:①周友苏著:《中国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09页;②周游著:《新公司法条文解读与适用指引:案例·规则·文献》,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48页;③王毓莹著:《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03页
。
答:《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款使用的是股东而非实际控制人的概念,故纵向公司人格否认仅限于一层,即仅适用于父子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爷孙公司之间的纵向人格否认并不被允许。例如,控股公司A直接控股子公司B,子公司B直接控股孙公司C,A公司与C公司之间不能适用纵向人格否认制度。但是,由于B公司与C公司同被A公司控制,故B公司与C公司之间可以适用横向人格否认制度。
延伸阅读: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88页。
10.
横向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可否扩展到所有的关联企业?
答: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人格横向否认,是对同一股东控制下的数个公司相互否认人格,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可形象称为“平行否认”。同一股东控制的多家公司之间虽不具有名义上的股东身份,但如果出现股东滥用控制权使多个被控制的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彼此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者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的工具的情况下,否认被控制公司的法人人格,判令彼此承担连带责任。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使用的是“控制”而非“控股”,并不限于基于股权的母子公司式的控制,而是一种广义上的控制,包括以协议或者其他方式对公司具有支配力的控制,故横向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可以扩展到所有的关联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兄弟公司、姐妹公司、叔侄公司、爷孙公司等。应该认为,兄弟公司、姐妹公司之间的人格否认是横向人格否认制度最典型的适用情形,但横向人格否认制度可适用于由同一股东控制或实际控制的公司之间,并不仅仅指向兄弟公司、姐妹公司这类由同一股东控制的同一层级的公司,也包含了诸如叔侄公司、爷孙公司等不同层级公司的情况。
延伸阅读:①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90-91页;②曹守晔主编:《公司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73-74页;③赵旭东主编、刘斌副主编:《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54页;④赵旭东主编、刘斌副主编:《新公司法重点热点问题解读:新旧公司法比较分析》,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426-427页。
11.
横向公司人格否认能否适用于没有被同一股东控股或实际控制的非关联企业?
答:《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在规定横向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时,将横向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前提表述为“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在文义上,“控制”一词不仅仅指向控股,也包含实际控制。因此,依照《公司法》的上述规定,现行的横向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强调多个企业之间需具有被同一股东控制的关联关系。被同一股东控制的关联企业,彼此之间可能是同层级的兄弟公司、姐妹公司,也可能是不同层级的叔侄公司,也有可能是股东控制的一级公司与二级公司。没有被同一股东控股或实际控制的非关联企业,无法适用《公司法》规定的横向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延伸阅读:①赵旭东主编、刘斌副主编:《新公司法适用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解读》,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73页;②赵旭东主编、刘斌副主编:《新公司法重点热点问题解读:新旧公司法比较分析》,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428页。
答:《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将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受害者明确界定为“公司债权人”。就公司人格否认之诉的原告而言,可以提起公司人格否认之诉的只能是债权人,且该债权人必须是能够证明其债权因公司不能清偿而被损害。公司债权人有自愿债权人和非自愿债权人两种类型。自愿债权人即合同之债的债权人;非自愿债权人包括侵权行为之债的债权人、无因管理的债权人和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人,还包括劳动关系中的债权人(劳动者)和行政关系中的特殊债权人(如国家作为税收债权人)等。自愿债权人和非自愿债权人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是自愿与被滥用独立人格的公司打交道,其本有机会发现公司的人格不独立,并有机会采取保护措施;而后者因各种原因与公司发生交集,被公司侵权,其没有机会事先采取措施进行防护。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法官在处理公司人格否认案件时,有区分自愿债权人与非自愿债权人的必要,对自愿债权人应当从严适用,对非自愿债权人(侵权行为的受害者)应当稍微宽容一些。当然,这里的“从严”和“宽容”主要指向的是构成要件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延伸阅读:①周友苏著:《中国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11-112页;②朱慈蕴主编、沈朝晖、陈彦晶副主编:《新公司法条文精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43-44页。
答: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受害者即是公司人格否认的责任相对人。只有公司人格否认的责任相对人才能提起公司人格否认之诉。公司人格否认的责任相对人是指因公司人格被滥用而受到损害并有权主张侵权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也可将其称之为责任承担的主张者。《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将其明确界定为“公司债权人”。这一界定排除了某些公司股东为排除某种不利后果而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请求的可能,比如控股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主张否定公司人格的情形。不仅如此,公司股东以否认公司人格为目的的诉讼抗辩也不应支持。《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8期刊载的田某媛诉刘某丽股权转让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宁民二终字第39号),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存在瑕疵的股权并非不可转让的标的,被告刘某丽作为云凯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云凯公司的出资情况是了解的,对原告未出资的情况也是明知的;被告请求揭开公司面纱,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并进而请求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应当依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只要具有股东身份就绝对不能主张否认公司人格,当股东同时兼具公司债权人的身份时即为例外。因为公司法并不绝对禁止公司股东与公司进行交易,所以在个案中,原告可能兼具股东与债权人双重身份。
延伸阅读:①周友苏著:《中国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11-112页;②云闯著:《新公司法司法实务与办案指引》,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375页。
答:公司股东负有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义务,这一义务是由《公司法》直接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而非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约定的义务。因此,违反该强制性义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必然属于侵权责任,在否定公司人格、追究股东责任时需要遵循侵权责任的相关法理。
延伸阅读:周友苏著:《中国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06页。
答:《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概括规定了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在客观行为方面应具备的要件,即“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从法条的文义解释来看,认定这一行为具体需把握两点:第一,行为人须有逃避债务的行为,这里的“债务”是指公司对外所负债务,它直接与股东利益相关;这里的“逃避”尽管可能表现为欺骗债权人、抽逃出资、规避法律等形式,但就其实质来看,是一种不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的行为。第二,行为人逃避债务的行为是通过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实现的。在公司人格否认中,“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与“逃避债务”之间应为行为方式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如果股东采取了滥用公司人格以外的方式,就应当适用其他相关法律来处理,而不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需要指出的是,《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逃避债务”,属于客观行为要件,而非股东的主观要件。从立法本意而言,《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并没有将主观意图作为认定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标准。
延伸阅读:①周友苏著:《中国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12页;②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88-89页。
答:《九民纪要》将常见的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类型化为三种:一是人格混同。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又称公司人格的形骸化、公司与股东关系不清,意指公司成为股东的另一自我、工具、同一体,因而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应否定其人格,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九民纪要》第10条规定,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二是过度支配与控制。《九民纪要》第11条规定,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是资本显著不足。《九民纪要》第12条规定,资本显著不足是指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股东利用较少资本从事力所不及的经营,表明其没有从事公司经营的诚意,实质是恶意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资本显著不足包括公司成立时资本显著不足和经营过程中资本显著不足两种情形。《九民纪要》没有规定公司成立时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仅规定了经营过程中的资本显著不足。由此可知,判断公司资本是否显著不足,是将公司设立后经营过程中作为判断时点,而非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额;是以股东实际缴纳的出资额作为与风险比较的对象,而非公司的注册资本额。司法实践中,公司债权人如果仅以公司注册资本少于其与公司签订合同的金额为由起诉,法院一般不会认定存在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另外,赵旭东主编的《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认为,利用公司规避法律所规定的强制性义务,比如为了逃税、洗钱等非法目的而成立公司等,也属于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情形。但朱慈蕴、王毓莹等学者认为,域外公司法理论上的欺诈行为及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的行为不适用于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延伸阅读:①曹守晔主编:《公司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75-77页;②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页;③朱慈蕴主编、沈朝晖、陈彦晶副主编:《新公司法条文精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版,第44页;④赵旭东主编、刘斌副主编:《新公司法诉讼实务指南》,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341页;⑤赵旭东主编、刘斌副主编:《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57页。
17.
认定是否构成公司人格混同应当综合考虑哪些因素?
答:《九民纪要》第10条规定,在认定是否构成公司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在出现人格混同的情况下,往往同时出现以下混同:公司业务和股东业务混同;公司员工与股东员工混同,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公司住所与股东住所混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关键要审查是否构成人格混同,而不要求同时具备其他方面的混同,其他方面的混同往往只是人格混同的补强。
延伸阅读: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页。
18.
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常见情形有哪些?
答:实践中,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常见情形包括:(1)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的;(2)母子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收益归一方,损失却由另一方承担的;(3)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然后再成立经营目的相同或者类似的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5)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其他情形。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工具的,可以综合案件事实,否认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判令承担连带责任。
延伸阅读: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页。
19.
公司与股东人员混同、财产混同、业务混同的主要表现有哪些?
答:人员混同、财产混同、业务混同是判断公司人格混同的基本标准。人员混同可形象地概括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主要涉及三种情形:一是公司组织机构中特定岗位的工作人员与股东或关联公司组织机构中特定岗位的工作人员相同,例如母公司的经理同时任职子公司的经理;二是公司组织机构中特定岗位的工作人员与股东或关联公司组织机构中特定岗位的工作人员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况,例如母公司的经理同时任职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三是公司的人事任免交由股东或关联公司决定。财产混同是指公司与股东或关联公司的资产难以区分,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公司与股东或关联公司之间共用同一账户、共用同一办公设备或办公地点、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财产且不作财务记载、不区分公司账簿和股东账簿、公司财产记载于股东或关联公司名下等。业务混同则是指公司在经营管理和日常事务方面的决定权由股东或关联公司完全掌握,公司无法形成独立决策,实践中的典型表现包括公司与股东或关联企业从事同一业务、由股东或关联公司实际履行加盖公司公章的合同等。
延伸阅读:王毓莹著:《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06页。
20.
能否仅以人员混同和/或业务混同为由直接认定公司人格混同?
答:在公司人格否认个案中,公司人员混同、财产混同、业务混同通常一起出现。就三者与人格混同构成之间的关系而言,我国司法实践大都认为,并非三种情况同时满足才构成人格混同,但财产混同是构成人格混同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仅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可被判定为人格混同,存在财产混同和人员混同和/或业务混同也可被认定为人格混同,但仅存在人员混同和/或业务混同一般不能直接认定为人格混同。对此,《九民纪要》第 10条指出,财产混同往往出现业务混同和人员混同,但其关键仍然是财产混同,其他的只是具有补强作用。
延伸阅读:王毓莹著:《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06页
。
21.
公司集团内部的统一管理能否作为否认其中某一公司人格的依据?
答:公司集团是由多个在法律上各自独立的公司联合组成的大型企业联合体,其特点之一是集团之中的各个公司均受到处于主导地位的母公司的统一管理。公司集团内部的统一管理在人员任用方面体现为母公司在整个集团的层面决定各子公司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管理及向子公司派遣劳务等,在财务方面体现为制定统一的财务管理规则、集中管理各公司资金、合并财务报表等,在经营业务方面体现为建立统一的业务规范、下达统一的生产经营计划并统一考核等。从表面上看,公司集团内部统一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人员混同、财产混同、业务混同的情形相吻合。但是,在公司集团的情境下,人格混同的判断标准不应机械地套用,否认公司集团中某一公司人格不应简单地以公司之间存在统一管理为依据,更重要的是判断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统一管理的必要范围,导致债权人完全无法区分各公司的独立人格。
延伸阅读:王毓莹著:《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06-107页。
答: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人格混同、财产混同等。在“北京格林伟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2021〕京民终652号)的民事判决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与集团行为作出了区分,其指出,关联公司之间代收货款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会计准则的规定,而关联公司之间存在控股关系、个别工作人员相同属于正常现象,二者共用一个经营地址亦不能说明二者存在业务混同。只要关联公司有独立经营场所及组织机构,有自己的财产并建立独立账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即便关联公司之间有人员交叉任职、经营业务交叉,也不足以认定产生公司人格否认层面混同的法律后果。
延伸阅读:王毓莹著:《新公司法二十四讲:审判原理与疑难问题深度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18页。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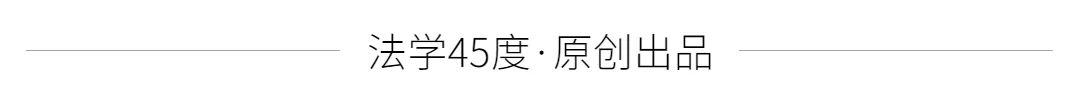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