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农历2017的最后一篇文章,小哲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感谢大家这一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今后我会努力为大家提供更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阖家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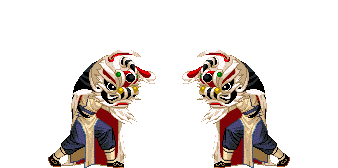
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对于未来农村经济工作和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意味着多年以来中央的农村工作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回顾2012年到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总体目标,到了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十三五规划目标里,没有再提四化同步发展,而是提出“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2017年的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农业供给侧改革。可以看到,近七年以来一号文件的重心,是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也即从如何推动城镇化发展到如何发展农村,到了2018年的时候,乡村振兴战略破茧而出。
那么,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一、近年一号文件出台的经济大背景
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因为中国广袤的国土里,不仅农村占了很大比重,农村人口占了半数之多,而且城乡差距较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因此能否实现农村的发展,既是宏观经济的制约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
但与此同时,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转变,反过来也会影响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所以农村政策的转变,需要放在三个经济大背景下进行考虑。
一是投资、消费、出口,也即三驾马车拉动结构的转变。
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发展的重心是城市经济,那么城市会不断吸引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农村集体用地大量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支持城市的工业、基建和地产投资。所以,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进程,某种程度上掏空了农村的资源,导致了农村的衰败。
而2009年之后,投资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消费开始对经济起到主要的支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提振农村人口的生活和消费水平,而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如果能追赶上城市,毫无疑问对消费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2013年,时任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就曾指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因此,前几年的农村政策倾向于在城镇化上做文章。
二是产业升级大背景下的劳动人口迁移。
工业化和城镇化主导下的人口迁移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沿海地区,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完成,城市可以提供的中低端就业机会开始减少,劳动力开始向中西部和农村回流。国家卫计委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连续第二年下降,这对于区域经济关系和城乡关系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关系,90年代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设想,也即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那么沿海的产业会先实现升级,同时一些中低端产业开始流往中西部,从而带动劳动力的回流,这样能够实现产业升级的平稳过渡。但实际上,受各种成本大幅抬升的影响,沿海的很多企业不是转移到内陆,而是到海外设厂,或者直接使用机器人,那么这个转换和缓冲的空间就没有了。
对于中西部省份而言,面对回流的劳动人口,本身并不具备充足的财政实力,就业机会也相对较少,那么在城镇化的问题上就会相当吃力。
三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结构性问题。
工业化进程中,以投资为主导的年代里,地方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基建和经济方面的事务,而在民生社保类的支出太少,而到了经济结构出现投资向消费的转换,需要财政发挥民生消费支撑作用的时候,财政收入已经开始出现下滑,不仅财政收入下滑,而且部分欠发达省份和城市负债率高企,此时要保民生就比较捉襟见肘了。
如果农村人口进城买房能落户,然后可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既接了地产的盘,又拉了消费,皆大欢喜,当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这个能力,你要忽悠他放开户口,是忽悠不动的。
二、新型城镇化,从哪里搞钱?
城镇化政策,经历过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的转变。传统城镇化是人为的造城,这走的其实还是投资拉动的老路,但问题是,地方政府依靠投资造出了城,但是民生公共物品的供给并没有跟上,农村人口没有能力进城消费,所以传统城镇化的结局基本就是空城、鬼城。
所以2013年之后,李总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核心是要解决农村人口在城里安居乐业的问题,那就意味着就业、居住、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一系列的民生公共物品的供给都要跟上,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农村进城人口才有足够的依托和保障,才能增加消费、拉动内需。
但问题是,新型城镇化不仅需要钱,而且需要比传统城镇化多得多的钱,这个资金缺口难以填补。这几年在棚改上面投入了那么多资金,还仅仅只是解决了一小部分进城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已。除了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之外,社保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2013年的时候,中农办主任陈锡文曾指出,我国推进城镇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国外大规模推进城镇化时,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不大,而我国目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的差距很大。对农民工参与各项社会保险的统计显示,只有22.2%的农民工在城里缴纳了养老保险。按照统计局发布的去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2290元计算,如果按照城镇标准缴纳社会保险,一个农民工一年要缴纳8000元,其中企业负担6000多元,按照1.6亿到外地务工的进城农民工推算,全国一年企业欠交的缺口就近1万亿元。
“企业补不起这个钱,政府也拿不出这么多钱。”陈锡文认为,城镇化进程比预想得快得多,各级政府也想帮助农民工解决市民化的问题,但至今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针对城镇化建设融资的国际经验,央行曾经做过专题研究(201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谈到,从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来看,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税收;二是基于使用者付费原则的项目收益;三是通过发行市政债或类似债务工具从金融市场融资。但无论是政府税收、使用者付费还是发债,其来源都与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提升,以及土地、房产带来的未来收入有关。
在实践上,对于新型城镇化到底从哪里搞钱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尝试过各种办法,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发行城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忽悠海外资金等等,但正如央行的报告所指出的,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在土地上做文章,都离不开土地的升值所带来的未来收入的变现。
然而,这里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对于城市土地来说,发达地区土地值钱,但土地储备已经不多了,可以卖的地都卖得差不多了,欠发达地区虽然土地多,但地不值钱;
第二,对于农村土地来说,想要在土地流转上做文章,那么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需要卖多少钱才能满足农民进城的公共物品支出呢?农业产出的利润率需要达到多少才能承担这么高的土地成本呢?
第三,民生支出与基建支出不同,缺乏现金流与收益,无法采用使用者付费的模式;
第四,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已经相当高了;
最后,要利用土地融资来拿到足够的资金,必然推高土地及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从而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
三、破局之法:乡村振兴
过去,之所以农村发展的政策重心在城市,是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掏空了农村的资源,使农村缺乏发展的基础,而在目前城镇化成本过高的情况下,顺应经济结构转变的大趋势,让沿海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中西部,让城市务工人员回流乡下,引导各类资源和要素反哺农村,在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在生产各种高质量农产品以及乡村旅游、休闲、养老、文化等农村服务业上下功夫,这其实是一个城市反哺农村的模式,既能使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又能使城市居民得到更好的消费体验,财政上的压力也不会很大,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成本更低,这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一个主要思路和背景。
从对经济增长和大宗商品需求的影响来看,未来农村消费和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有望进一步提升,但另一方面,城镇化的重点在于基建和地产,那么农村工作重点从城镇转移到乡村之后,对城市基建和地产的影响也是偏负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