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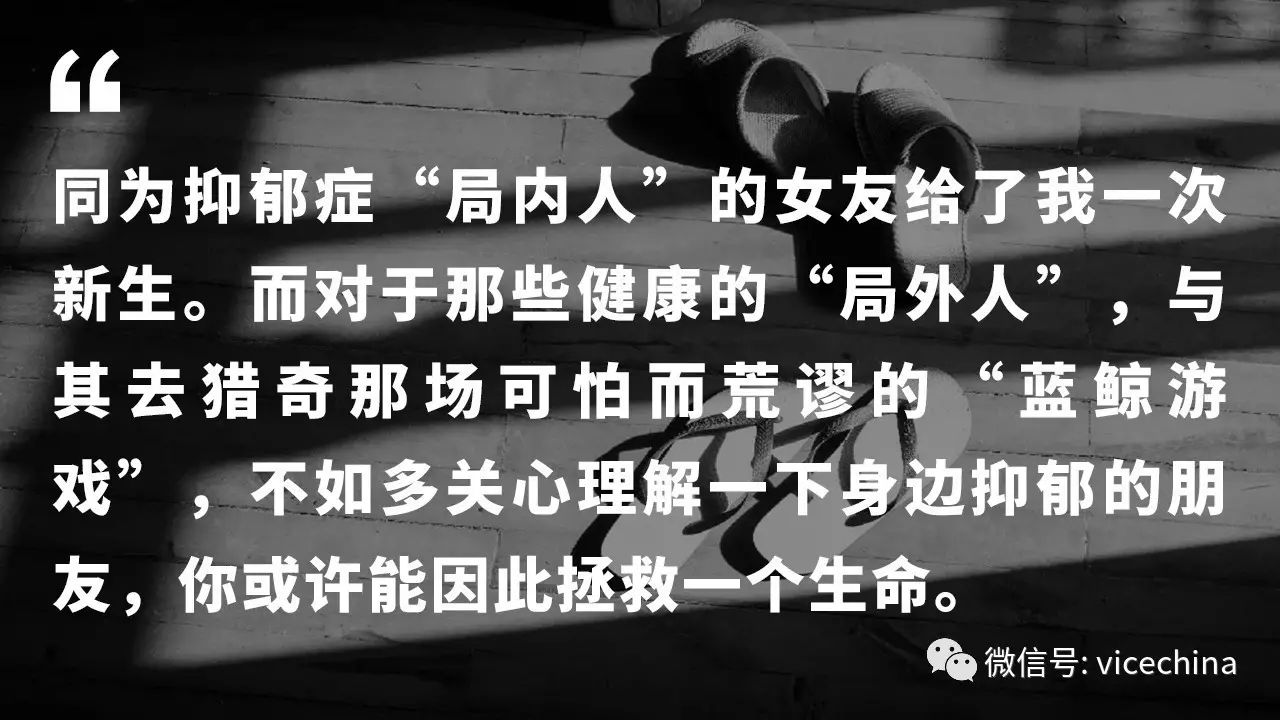

第一次崩溃尝试自杀,是三年前在重庆去往武汉的盘山高速上。
我当时一心只想回到武汉,回到学校,那个我能感觉到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不顾恶劣的天气开始了长时间的驾驶。在深夜的暴雨里,面对是看不到尽头的大山,我把双手从方向盘上拿开,张开双臂,心想,算了吧,都算了吧。
我的身体和大脑,都感觉太累了。短短的一年里,我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家庭破裂、感情欺骗和学业危机,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自由落体,在跌向生活的最低谷。每天醒来,我根本不知道第二天的生活,该从哪开始。在那之前的几天,我从武汉自驾12个小时到重庆,和前女友约在山城过情人节。我得到的,却是被欺骗和分手的结果。所有的打击在那一刻一起冲上我的大脑,我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彻底崩溃了。
那段时间一直环绕在心里的,就是偶像
Otis Redding
的那句歌词,生活一成不变,生无可恋 (I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noting’s gonna come my way)。大概是受他在巡演中飞机失事而去世的影响,在无法承受的悲伤下,我打算效仿偶像,把生命结束在路上。当然,这种想法只是一个借口,真正让我选择尝试自杀的原因,是无助与孤独。我面对过更艰难的生活,但我从没面对如此孤单的心境。当我生活的轨迹和身边的亲人朋友都渐行渐远,我变成了大海里的一叶孤舟,我的存在与否,又有什么区别呢?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在车即将进入下一个山路拐弯时,巨大的恐惧和求生欲,让我下意识的控制住了方向盘。我安全的回到了车道上,疲惫和无力感一扫而空,我从未如此强烈的体验过,活着的感受。大概这种超脱的感受,就是所谓的涅槃吧。
这种求生欲,成了支撑我每天生活的力量。我去找了心理医生,他告诉我,我得了
双相情感障碍
,抑郁向 —— 这是一种类似躁郁症的疾病。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药、安定药和安眠药。每种药都有一长串的副作用说明,但是为了活着,我连续服用了三年药。
药物确实能让我摆脱持续的失落和不安,但也让我的情绪变得麻木。在得知父母离婚的消息时,我的反应仅仅是一个,“哦”。 这种麻木感,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每天醒来,我仍然要面对一大堆无能为力的困扰。只不过,我学会了用每天在湖边喝着咖啡,抽一天烟放空的方式,来打发这些我不懂如何解决问题。
我试过寻求身边人的帮助。当我第一次克服了可能被歧视的恐惧,告诉几个要好的朋友我抑郁的病情时,大部分人无法理解,我这样一个各方面还算 “不错” 的年轻人,怎么会得抑郁症。其实我也不懂,医生解释抑郁的病因,是先天和后天经历多方面造成的。甚至有朋友惊讶的问我,“小白,你怎么还能得神经病啦?” 可能他并无恶意,但 “神经病” 这个字眼,确实刺痛了我。几天之后,从其他同学口中,我又一次听到了 “神经病” 这个字眼。
父母和亲戚,在得知我生病后,纷纷迫不及待的打电话 “慰问” 我。很多只有过年才会见一面的亲戚,忧心忡忡地询问我的病情,以示关心。他们告诉我最多的话,就是 “开心点,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我理解他们出于亲情的善意,但是,这句话在我看来,就像问一个骨折的人,“好好走路啊,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走路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闭门不出,靠药物和零食生活
从此之后,我选择了沉默。我又经历过几次崩溃和尝试自杀,是药物的力量,让我渐渐能控制自己崩溃时的行为,也都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是我不会再去向别人分享这些痛苦经历,很多时候,我想我的一生可能就得靠自己这样坚持了,直到我坚持不住为止。
但有些时候,生活在一瞬间就会发生变化。去年初秋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三里屯的一家咖啡馆,抽着烟想着一些无边无际的烦恼。那天我遇到了改变我生活的人,我的女朋友 —— 多多。
我们在一起,要感谢一位天天穿着丝袜短裙,带着长发和浓妆,出没在三里屯蹭烟抽的异装大叔。多多和我坐在一家咖啡馆门外抽烟,大叔那天选择找她蹭根烟抽,她当时吓坏了,问我可不可以坐到我这桌,躲开那位大叔。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其实,她在一进咖啡馆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她,但是我想想我自己活得这操行,我哪还敢和女生搭讪。现在我偶尔还会遇到那位异装癖大叔,每次见到他,我都要跟他一块抽根烟。)
最不可思议的是,她和我一样,也是抑郁症患者。从小家庭的变故和在国外孤独的留学经历,让她在几年前有了抑郁症状。她去了几家医院,医生都给不了不同的诊断结果。为了逃离原来的困境,她刚刚孤身一人来北京,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我第一次找到了可以 “零压力” 交流的人,她不会因为抑郁症而对我有偏见。我们的交流不存在障碍,她愿意倾听我脑中不切实际的担忧和烦恼,也愿意用她的经历,来安慰和鼓励我。 她能够理解,为什么每天起床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也明白心理崩溃,甚至想自杀时,有多么痛苦。她有一点疑病症,每天都会担心自己身体不舒服,我每天会给她解释她身体很好,时常带她检查身体。我们成了一对彼此扶持的 “病友”。
过去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痛苦的,所以我们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各自找到了工作,租了一间小房子,养了几条狗。我们很少纠结彼此过去的经历,也尽量不让的家庭等其他因素影响我们的生活。她和我一样,对彼此和未来的要求不高,过好每一天就好。

有些时候,我的狗比外人更理解我
从我出现抑郁症状到现在已经有四五年,这是我第一次敢说,我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至少我没有再崩溃过,更没有想过自杀的念头。生活虽然平淡无奇,不过基本每一天都是快乐的。她给我的支持和陪伴,停止了我自暴自弃的自由落体式的生活。
“蓝鲸游戏”
在国内的悄悄风靡,让 “自杀” 最近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因此我才得知身边很多朋友和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几天前,我的朋友和我讲述了她的闺蜜因抑郁自杀的秘密。她的闺蜜生活在一个偏远地区的小镇上,在长期被妈妈的男友性侵后,患上了抑郁症并伴有癔症。当地没有正规的心理医院可以提供治疗,面对来自身边人的伤害,她只能选择通过微信聊天来获得一些来自远方朋友的帮助。相比于性侵和抑郁带来的痛苦,这一点点帮助实在太微弱了。最终,她选择了跳楼自杀。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朋友万般自责,她曾决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永远的秘密带进棺材里,然而,她却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分享了这个秘密之后,她坦言自己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担子了。但闺蜜的死,永远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孤独,可能是最让抑郁症患者恐惧的一个词。心理医生曾告诉我,没有体验过抑郁症的生活的人,是无法去和一个病人产生心理共鸣的。他们不止一次建议我,尽量和专业人士或真正能理解自己的人,沟通交流自己的感受,不要把那些 “局外人” 的误解放在心上。
然而,对抑郁症患者,所谓的 “局内人”,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据中国医科大学的调查,中国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抑郁症患者约7000万人,三分之二的抑郁症患者曾有过自杀的想法,15%的重度抑郁患者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每千人拥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是“健康社会的平衡点”。在中国,通过资格考试的心理咨询师只有约2万人,每千人仅拥有0.018个心理咨询师。
在这个失去健康平衡点的社会,我是幸运的,同为抑郁症 “局内人” 的女友给了我一次新生,让我还能活着去思考这些关于抑郁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健康的 “局外人”,与其去猎奇那场可怕而荒谬的 “蓝鲸游戏”,不如多关心理解一下身边抑郁的朋友,你或许能因此拯救一个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