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你说句对不起有这么难嘛?!”
“对不起我错了。”
“你以为你道个歉就没事了?!”
作死从来都不是新鲜事儿!
●
●
●
古人云:“劝君莫打三更鸟,儿在巢中盼母归。”于是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在这些类似的话语中寻找蛛丝马迹,对古人或远古时期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深信不疑。然而,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尤瓦尔 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中告诉我们,
“和谐相处?你想多了。”
在人类45000年前登陆澳大利亚时,原有的24种体重在50公斤以上的动物,被人类消灭了23种;公元前14000年左右,人类又成功地血洗了美洲,造成34/47,50/60的北、南美斩杀效率……这是多么和谐啊,和谐的登顶生物学有史以来最致命物种的宝座。
其实也许有人会从好的来想,至少我们现在比以前克制了。是吗?
我们用赫拉利的这本《人类简史》颠覆下我们的思维吧,看经历了书中的“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与科学革命”,我们是不是更好一些?
最早的人类是从大约250万年前的东非开始演化,祖先是一种更早的猿属Australopithecus(南方古猿)。大约200万年前,这些古远人类有一部分离开了家园而踏上旅程,足迹遍及北非、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带。
因为向不同方向进化以适应环境,于是人类发展出了几个不同物种。比如在欧洲,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图左)。这是个大力士的人种,据考古学家发现,他们打熊抢熊洞不是个事儿,战斗民族只能望其项背。
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弗洛里斯人(图右),身高最高不过1米,体重最重也不过25公斤,也许是霍比特人的原型……


在几十年万前的地球上,至少就有6种不同的人。——那么为何我们智人如此孤单?自己作死的呗。你以为我们对这些同人科生物“猩猩”相惜?

是种族大灭绝啊!听过黑猩猩捕杀疣猴导致后者几乎灭绝的故事么?

在最先长达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会猎杀小动物、采集种种能得到的食物,但同时也会遭到较大型食肉动物的猎杀,长久以来稳定位于食物链的中间位置,还没想到去诛杀同类。

一直到40万年前,有几种人种才开始固定追捕大型动物,而要到10万年前智人崛起,人类才一跃而居于食物链顶端。
于是生态系统猝不及防,人类自身也开始懵逼了。懵逼干啥?
人类到底还是动物,交配和打架呗,俗称“吃饱了撑的”。于是过去3万年间,已经太习惯自己是唯一人类物种,集强迫症,洁癖症,焦虑症,暴戾症于一身的智人开始了他们的“吃豆豆旅行”——种族净化过程。
不禁让人想起非洲军蚁的行军路线以及鬼子进村……
所以现在各种族看其他种族不顺眼,非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遗传基因里带的。

那么面对比毛子还强壮的尼安德特人,又矮又挫的智人怎么取胜的?靠语言呗。
大约距今7万年到3万年前,认知革命发生了
。智人开始八卦,说坏话,发展了语言的社会功能。
别奇怪,人类靠八卦凝聚彼此是很容易理解的,即便现在,物理学家聚在一起也不可能讲夸克,你以为你是谢耳朵啊?谢耳朵和莱纳德的共同语言@#¥&*还拿来泡妹子玩游戏呢。

有了八卦基础,智人就开始创建自己的虚构体系,将八卦社交圈扩大进化,并演进成了贸易甚至是制度和社会结构。
这样的“好处”在于,以一个虚构的“八卦”象征,比如部落守护灵,神明,图腾,贸易伙伴等为共同语言的基准,智人联合了许多共同行为的“说坏话好哥们”团体,十分没有职业操守,厚颜无耻的群殴了如果一对一单挑必输的尼安德特人。
而在与尼安德特人实战之前,智人是用了成片屠杀兽群的方法来练手的。所以,每当我们看小说发现所谓正义人士围殴所谓“坏人”时总觉得哪里没对又说不上来,基因里的“群殴”遗传因子作祟呗。

屠杀了尼安德特人以及和少数尼安德特人做了不可描述之事嘿嘿咻咻(哔——)之后,智人基本在地球上无敌了。独孤求败是很寂寞的,于是智人开始探寻是作死还是发展的道路。
他们没作死,许多生命被他们的“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作得尸骨不剩。那些还留有化石的灭绝动物好歹还可以作为赤裸裸的智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证,跟着这些动物一起亡灭的寄生虫等就白白做了冤死鬼……
正如前记的数据,智人每“旅行”到一个地方,就会成为生态的连环杀手,恐龙在天之灵一定甘拜下风……大约每一种接触过人类的生物都会告诉下一代,“听妈妈的话,别靠近那个用两脚走路的怪咖,走哪灭哪的……”
作死无辜的生命还不算,智人们是不甘寂寞的,他们又开始了作死自己的农业革命……
大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了农业革命。
以我们惯常思维以及所受历史教育,这是好事吧,人类的大跃进,人类脑力进了一大步。
然而,赫拉利认为这是史上最大骗局,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类越来越聪明。
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
原来狩猎采集时期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诚然,农业革命是增加了食物总量,但人口爆炸,有利的是精英分子,就是凡勃仑所说的“有闲阶级”。虽然凡勃仑的一些论点非常阶级论,但确实农业革命是助长了这些养尊处优,不从事生产的精英阶级产生的。
相对来说,农民的工作更为繁重了,而且到头来饮食比采集狩猎时期遭。采集狩猎时期还可以寻求不同物种满足不同营养,天灾人祸物质匮乏时期还可以举族大迁徙。农业革命时期,农民可就被农作物“困住”了,疾病,人祸,天灾……许多因素都能造成农民辛苦一辈子却家破人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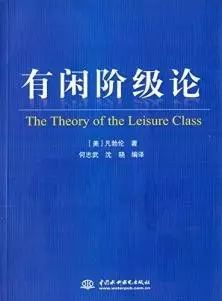
人类在农业革命里作得一手好死。
鉴于人类“一定不能只我一类生物作死”的原则,人类又开始折腾家畜。于是在农业革命时期,绵羊、山羊、猪、牛鸡等终于被人类折腾得毫无还手之力了。
野生鸡的自然寿命大约是7-12年,牛则是20-25年,虽然在实际的野生环境可能不会活那么久,但总比人类驯化的长吧。驯化后的肉牛和肉鸡不过出生几周和几个月,就到了最佳屠宰年龄,简直是悲哀短暂,还来不及思考的鸡生和牛生。

另外,人类学家发现,在许多新几内亚的部落社会里,想判断一个人富不富有,就要看其拥有几头猪。为了确保猪跑不掉,新几内亚北部的农民会把猪的鼻子切掉一大块。这样一来,每次猪想闻东西,都会感到强烈的疼痛,不但无法觅食,甚至连找路都做不到,于是不得不完全依赖主人。
农业革命时期的农民算是被自己作死,家畜被农民作死,那么农业革命时期的精英分子又在干什么?他们在用“想象建构的秩序”这样的工具建立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所有这些合作网络,不管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还是秦朝和古罗马的帝国,都只是“由想象建构的秩序”。支持它们的社会规范既不是人类自然的天性本能,也不是人际的交流关系,而是他们都相信着共同的虚构神话故事。
比如,公元前1776年左右的《汉谟拉比法典》,开头就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位大神安努、恩利尔和马杜克任命汉莫拉比“在这片土地上伸张正义,驱除不义罪恶,阻绝恃强凌弱”。
接着,法典列出大约300条判例,固定写法是“如果情形如何如何,判决便应如何如何”。
虽然一些法律并不符合现代人价值观,比如一个女奴隶只值20舍客勒,但光是平民男性的一只眼睛就值60舍客勒。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看来,这是公平正义的,因为《汉谟拉比法典》背后的一项重要假设,就是只要国王的臣民全部接受各自的阶级角色、各司其职,整个帝国上百万的人就能有效合作。
建构这么复杂的“想象秩序”,在农业革命时期,当然只有“闲的没事干”的精英分子推动了。

如此建构的历史有正义可言吗?赫拉利可能会送历史“呵呵”二字。
对赫拉利而言,历史从无正义。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看得透。现代西方教育对历史形成的种族制度嗤之以鼻,却认为历史形成的贫富阶级天经地义而自然。
但事实是大多数有钱人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出生在有钱的家庭,而大多数穷人一辈子没钱,也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贫穷的家庭,犹如网络上的洗脑心灵鸡汤“读书与不读书的差别”信誓旦旦证明读书比不读书的人发展好,这不过是鸡屁汤,在这阶级固化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你得看不读书的人读得上书吗?
一场出国留学必考雅思1950,低保资助每月几百元。这还是城市社区,你让人家如何和起跑就用豪车跑的读书人比?
但不幸的是,复杂的人类社会似乎就是需要这些由想象构建出来的阶级制度和歧视。
有了这些后,人类就可以懒,陌生人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了解彼此,也能知道如何对待对方了。
这种“懒”法根本谈不上正义,许多阶级制度开始时多半是因为历史上的偶发意外,但部分群体取得既得利益后,世世代代加以改良,形成了所谓的“理所当然”。

以现代观点,穿着丝袜和高跟鞋,站得无比娘娘腔的路易十四
人类当然不满足这样的作死,他们继续在作死自己以及作死它物的康庄大道上坚持不懈地前进着,于是迎来了科技革命。
(以下图片恐引起读者不适,慎看或跳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