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丹尼尔·齐布拉特
(Daniel Ziblatt)
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兼伊顿政府学教授,2023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研究重点是欧洲政治和民主比较研究。
同一时期发生的德意志革命与意大利革命,有朝一日将被视为历史哲学中最富有成果的比较之一。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很
大程度上来说,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向学者发出的对德意志与意大利民族革命进行比较的邀约,在过去的130年里还没有得到回应。尽管德国与意大利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历了同样动荡的政治发展,但在关乎国家形成、民族主义与联邦制等研究领域,这一组案例的许多可比之处还没有被充分利用。本书的研究接受了特赖奇克的呼吁,对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关键插曲进行比较,从而回答如下疑问:民族国家是如何被缔造的?哪些因素决定了民族国家最终将建成联邦制或是单一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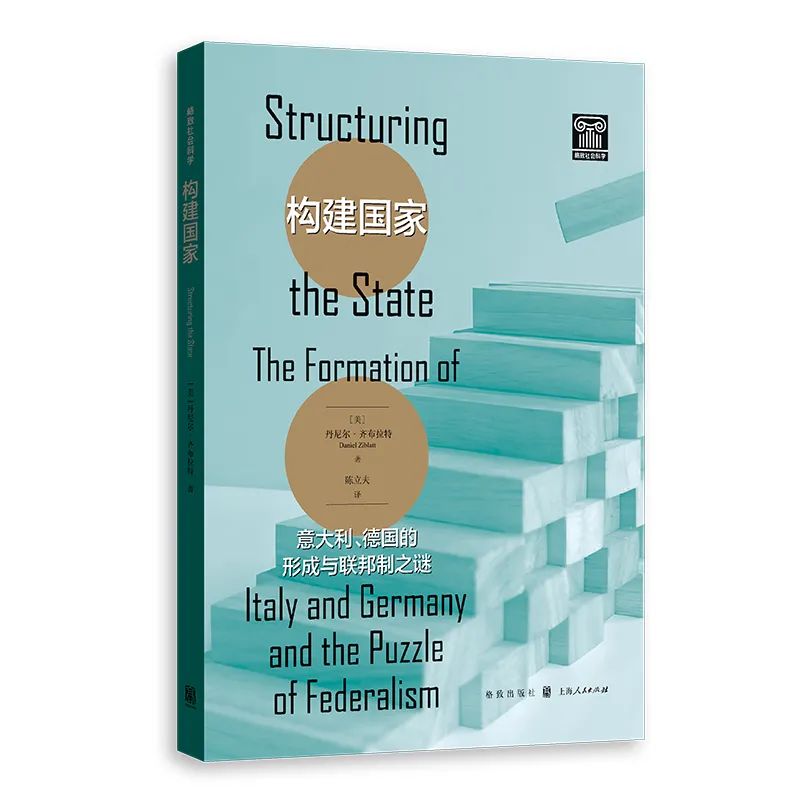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当代,国家建构与联邦制的议题经由对欧盟的成立以及更广泛的国家建构相关议题的讨论,重新回到政治学的舞台中央,而对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进行比较分析,将为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再次关注的这一问题提供有益的研究方式:新的政治体诞生需要哪些条件?什么决定了政治体的制度形式?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联邦制?在制度创设的时刻,政治领袖在设计政治体制时实际上有多大影响力?寻求建立联邦制的政治领袖能否简单地通过颁布一部宪法来确保联邦制的推行?推行联邦制的宪法可以通过暴力手段强行施加吗,还是它必须在由彼此实力相当的次国家政权组成的集合里,经由次国家政权内部之间的谈判而“自下而上”地涌现?
本书的研究聚焦于19世纪的欧洲,因为这一时期能够给这些议题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尽管学界一般将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功于法国大革命,但事实上,民族主义是在1830年至1880年这一决定性时期兴起的。许多位于欧洲、北美洲与南美洲的当代民族国家在帝国的解体与国家整合的双重过程中创建,而希腊、比利时、意大利、德国、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等老牌欧洲国家则回炉重造。这一段被我称为“建国时刻”的时期,改变了欧洲、北美洲与南美洲的政治版图。就是在这一连串几乎同时发生的民族国家形成经历里涌现出来的政治体系,以各式各样的制度形式的出现为标志,为当代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提供了一系列多样化的经验研究案例。
其中,特别是关于国家结构的一个领域,也就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的制度化分配方面,在19世纪末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呈现出制度上的多样性,这也就引发了民族国家将如何建立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的问题。一些新建立的政权,例如德国与加拿大就建成了非常明确的联邦制政体,而另一些政权,例如比利时与意大利就建成了典型的单一制国家。在联邦制下,如加拿大与德国,地区政权尽管被吸纳,但仍完好无缺地作为宪法规定的主权的组成部分被保留在了更大的“全国性”政治框架内,地方政府能够正式参与全国政府的决策、对公共财政(诸如税收与支出)的自由裁量权,以及行政自主权。相比之下,在意大利与比利时,任何曾经存在并作为主权实体的地区政权都被从政治版图上抹去,地方政府无法正式参与新的全国政府的决策,没有公共财政的自由裁量权,也没有行政自主权。尽管这些国家在建立的过程中经历了相似的时刻,但是在19世纪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却在国家统一后的领土治理模式上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是这一时期制度建设试验的产物,而它们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关乎联邦制起源问题的悖论,这也就是本书的核心问题:寻求整合邻邦的政治核心发起统一时,如何能够强大到足以建立起更大的民族国家,但又不至于过于强大,以至于彻底吸纳与抹除其他已有的次国家政权,从而建成单一制国家?如果发起统一的政治核心过于强硬,那么单一制国家是否不可避免?而如果过于退让,岂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建起任何政治联合?
简而言之,我认为要想解释为什么会形成单一制或是联邦制的民族国家,就必须回答在分析层面上相互独立的问题:民族国家为什么会形成?民族国家又为什么采用单一制或联邦制的政权结构?本书的第一部分将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部分则回答第二个问题。本书认为一旦国家统一的进程开启,对于有志于建成联邦制国家的政治领袖而言,摆脱联邦制起源悖论的方法就是,由发起国家统一的政治核心(核心邦国)吸纳我所称的拥有更强的“基础性能力”(infrastructural capacity,即征税、维持秩序、规制社会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治理能力)的邦国。如果政治核心吸纳了这一类型的邦国,那么构建联邦制时可能存在的政治核心与其他次国家政权之间潜在的争端就可以被克服。一旦有基础性能力较高的邦国,那么民族国家就能经由邦国之间的协商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能够让渡给国家之下的次国家政权。为什么?因为只有那些拥有较高基础性能力的次国家政权才能为政治核心与其他次国家政权带来收益,而这也正是国家统一所追求的最初目的。反之,无论政治核心自身军事力量是强是弱,如果政治核心在吸纳其他地方邦国时发现后者并没有这样的基础性能力,那么政治核心与其他次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将更加难办。因为一旦被吸纳的地方邦国被认为对国家统一毫无增益,那么它们就会纯粹地被视为国家统一的绊脚石,这就使得协商建国的可能性变小,导致形成民族国家的路径只能依靠军事征服与创建单一制政体来实现。为了解释开国元勋到底会选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本书收获了最有讽刺性的教训:如果国家缔造者寻求建立联邦制,但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吸纳的都是基础性能力欠缺的邦国,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受制于这些被纳入国家统一对象的邦国的内部治理结构。
至少从两个原因来看,研究联邦制的起源非常重要。第一,联邦制在近些年来已经越来越被视为解决广泛问题的一种制度方案,像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这样的学者就强调联邦制在创建与维持自由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其他学者,如乔纳森·罗登(Jonathan Rodden)和埃里克·威贝尔斯(Erik Wibbels),则指出联邦制对财政绩效、政府发展以及经济绩效带来的潜在收益与隐患。还有一些学者,例如迈克尔·赫希特(MichaelHechter)与南希·贝尔梅奥(Nancy Bermeo),则认为与单一制相比,联邦制结构在包容少数群体、消弭族群冲突与维持民族国家团结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好处。不仅仅是学者,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与政治领袖也日渐将联邦制视为解决各种问题的潜在方案。尽管我们都清楚推行联邦制会产生哪些结果,但是我们对联邦制建成的原因可以说是还一无所知。如果联邦制真的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潜在的制度配置,那么民族国家的缔造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才能真正采用这种制度形式?尽管目前已经开始有文献探索推行联邦制的可持续性,但对联邦制起源的关注依然太少。难道联邦制宪法能够在任意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中颁布推行?又或是,联邦制必须通过加盟邦国间的协商才能建立?政治领袖又可以通过哪些途径使他们的政体朝着联邦制的方向迈进?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什么诞生的是联邦制而非单一制?
第二,对国家形成与联邦制起源开展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政治发展本身。尽管研究欧洲政治发展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欧洲大陆上国家体制的多样性,但是在欧洲的发展过程里,在联邦制与单一制民族国家之间的关键且长久的分殊却很少被比较研究。基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与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传统,在解释宏观制度差异的起源与持续性方面,已经产生了许多学术研究,以辨明形成民族国家的不同路径如何催生了绝对主义统治模式的性质、政权类型、资本主义的国家组织以及选举制度的选择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联邦制与单一制的分野”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尚未为学者所关注,尤其是考虑到当代欧洲的17个国家之中有4个联邦制国家与13个单一制国家。因此,本书的研究将探索欧洲民族国家结构的多样性来源,先研究19 世纪的德国与意大利这一对关键案例,进而在最后一章里将这一对案例置于西欧17个最大的国家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之下进行观察,最终形成推广至欧洲之外的理论洞见。
在解释民族国家形成与联邦制起源的问题前,我需要对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我所说的“民族国家”,指的是在法国大革命后,以英法两国的经验为蓝本,在欧洲、北美洲与南美洲出现的一组特定的领土主权单位,它们既不是绝对主义国家,也不是跨民族地域的帝国政权,相反,它们是包含国民、民族以及国家组织和国家认同在内的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综合体。关于“联邦制”的定义显然更有争议,部分学者会从文化或是意识形态的范畴来定义“联邦制”,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延伸了联邦制的定义,将诸如“民主”,甚至是“政治稳定”等概念也视为其必要组成。而我发现将“联邦制”的国家定义为那些存在地方主权政府(且这些地方政府拥有三个宪法赋予的制度性特征)的国家,会更有益于开展实证性的社会科学分析。这三项通常集中出现的特征是:(1)地方政府能够正式或非正式地参与全国政府的决策;(2)地方公共财政(税收与支出)的自由裁量权;(3)在中央政权之下,地区政府拥有行政自主权。我采用了遵循严格两分法的联邦制定义来界定中央政府与它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即使存在地方政府,但是只有那些拥有为宪法所保护的次国家政权的民族国家才能被称为“联邦制”国家。如果只存在唯一的全国政权或是次国家政权不受宪法保护,那么这样的政治体是单一制国家。
本书的核心研究问题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缔造国家的政治核心会吸纳已有的次国家政权,但同时保持其独立完整,从而缔造联邦制国家?而在什么条件下,缔造国家的政治核心会解除地区政府的权力,从而构造具有更多单一制特征的国家?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联邦制可以被成功构建?而为什么在另一些情况下,联邦制则难以扎根?有关这些问题的政治学与历史学既有研究集中于三个主要变量:观念、文化或权力。表1.1展示了每条研究路径的概述示意图。
|
理论
|
因果机制
|
预期结果
|
|
联邦制的
“
观念
”
理论(例
如伯吉斯)
|
社会中的观念构造
|
一个社会中对权力下放的观念共识越强,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就越大
|
|
联邦制的
“
历史文化
”
理论
[
例如翁巴赫(
Umbach
)
]
|
社会中的文化裂隙构造
|
在国家统一前各地域的文化独立性越强,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就越大
|
|
联邦制的
“
社会契约
”
理论
(例如赖克)
|
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构造
|
在国家统一的协商过程中,政治核心相对于其他地方政权的军事力量越弱,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就越大
|
乍看起来,每一条研究联邦制的路径似乎都对民族国家为什么会在央地关系里采用联邦制提供了使人信服的解释。第一种方法通常来自迈克尔·伯吉斯(Michael Burgess)等学者,他们认为政治领袖与制宪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观念在形塑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结构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种观点则严肃对待历史与文化的作用,关注社会中的文化分裂或族群分裂的天性。尽管第二种视角通常强调各民族的“原初”差异,但这一论点可以延伸至国家内不同地区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或是高度的地域忠诚的情况,也就是,即使并没有“族群”分裂根源,在一个人口在地域内高度分散,且民众普遍有着根深蒂固的地域忠诚感的政权里,联邦制也更可能出现。最后,第三种观点与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的观点最为密切,也包含在近期一些对赖克的论证逻辑进行形式建模的研究中,这一观点认为联邦制的出现与维持只可能通过势均力敌的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的“讨价还价”实现,此时的中央既没有强大到可以“压倒”各地区,各地区也没有强大到可以“破坏”国家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