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后汉书》冯良事迹成立小论
徐冲(复旦大学历史系)
【提要】本文对范晔《后汉书》中文本面貌高度相似的冯良事迹与赵晔事迹提供了一个解释。东汉国史《东观汉记》所记冯良事迹构成了最初的文本起源。这一类型的书写在东汉后期颇有其例,与当时“士、吏之别”的起源正相对应。成于孙吴的谢承《后汉书》以《东观汉记》所记冯良事迹为蓝本,书写了江东名士赵晔事迹。东晋时期的袁宏《后汉纪》与葛洪《抱朴子》,则通过发展若干相异的新细节,使冯良分别呈现为儒学名士和道教先驱的不同形象。刘宋初年范晔著《后汉书》书写冯良事迹时,一方面继承了《东观汉记》以降以冯良为儒学名士的主流书写,一方面又将谢承《后汉书》、葛洪《抱朴子》等发展出的新细节纳入其中。冯良事迹在诸家“后汉书”中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古代史学作品在文本传承方面所蕴含的因袭、歧变与反哺的层累过程的典型表现。
一、范晔《后汉书》中的冯良事迹与赵晔事迹
据范晔《后汉书》卷五三《周燮传》记载,延光二年(123)安帝朝廷曾以玄纁羔币礼聘汝南周燮与南阳冯良两位名士,二人皆辞疾不就
[1]
。其后范书附记冯良事迹如下:
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妻子求索,踪迹断绝。后乃见草中有败车死马,衣裳腐朽,谓为虎狼盗贼所害,发丧制服。积十许年,乃还乡里。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妻子如君臣,乡党以为仪表。
[2]
以上文字中包含了诸多有趣的历史信息。“出于孤微”,指冯良在乡里无可凭藉的家族势力,即所谓“单家”、“贫贱”,而与“大姓”、“冠族”相对
[3]
。这一出身与他年少时即进入“县吏”行列的经历是对应的。至三十岁时为“尉从佐”。虽未明言郡县,但光武帝建武六年(30)省罢郡都尉,终东汉一世都未恢复
[4]
。这里的“尉从佐”只能是“县尉”之从佐,仍然属于县吏序列
[5]
。这说明冯良自入仕后一直服务于郡县官僚系统的底层。然而就在执行一次“奉檄”迎接督邮的例行公务时,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所从事的“厮役”之耻。此处李贤注曰:“厮,贱也。”“耻”和“厮役”实际上是同一种认识的反复表达,以说明其后毅然决裂的动机所在。这种决裂表现为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其一为“坏车杀马,毁裂衣冠”,车、马、衣、冠当然都是“公物”,即破坏过去县吏身份的象征物。其二为逃离家乡,至犍为郡师从杜抚为学,这是新身份与新生活的开始。最终经十余年学成归来后,成为表率乡里的儒学名士
[6]
。
不同于《后汉书》插叙附传时常见的疏略情形,这里的冯良事迹本末皆具,且叙述有致,颇富戏剧性。然而,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范晔所记冯良事迹,与同书《儒林传》中的赵晔事迹颇为相似。《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下·赵晔传》载: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
。
[7]
赵晔为会稽山阴人,因所著《吴越春秋》流传于世而较知名
[8]
。而范书所记赵晔事迹,除去开头的姓名籍贯与结尾的著述信息以外,中间的主要经历部分,如清人何焯所言,“《周燮传》载南阳冯良事,与此相类,而所从皆杜抚,必一事而传者互异耳”
[9]
。
范晔《后汉书》中的冯良事迹与赵晔事迹究竟相似到什么程度呢?不妨将二人事迹中的情节要素简单归纳为如下五点:
(A)出身底层,在家乡从事卑职多年。
(B)因某次受辱而觉醒,逃离家乡。
(C)在新环境中成长,获得新身份。
(D)旧身份在家乡以假死亡的形式被消灭。
(E)以新身份荣归家乡。
按照上列五个情节要素,可将《后汉书》所记冯良和赵晔事迹分列如表1。
表1
|
范晔《后汉书·周燮传》附冯良小传
|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赵晔》
|
|
A
|
出于孤微,少作县吏。
|
少尝为县吏。
|
|
B
|
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
|
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
|
|
C
|
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
|
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
|
|
D
|
妻子求索,踪迹断绝。后乃见草中有败车死马,衣裳腐朽,谓为虎狼盗贼所害,发丧制服。
|
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
|
|
E
|
积十许年,乃还乡里。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妻子如君臣,乡党以为仪表。
|
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
|
可以看到,以上二者虽然在具体文字方面有相当多的差异,但是均全部包含了上述五个情节要素在内,而且在设定的发展顺序上也如出一辙。同时,在各个情节要素所包含的关键细节上也保持了高度一致。如A的“县吏”身份,B的以“奉檄迎督邮”为“耻”,C的逃至“犍为”从“杜抚”为学,D的家人为其“发丧制服”,等等。
对此,上引何焯的判断是“必一事而传者互异耳”。所谓“一事”,基本应等同于表1所示的情节要素和关键细节;而“传者互异”,似乎暗示冯良与赵晔中必有一人为这一事迹的真正主人,范晔《后汉书》中之所以出现另一人的相似记录,是事迹在当时流传过程中的讹误所致。这一意见谨慎避免了二者文本面貌的相似来自于文本传承方面存在关连性的判断。
不过要从史实的层面确定冯良与赵晔何者为伪,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何氏提示二人“所从皆杜抚”。此人确非僻居蜀中的泛泛陋儒。《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下·薛汉传》言薛汉弟子中,“犍为杜抚、会稽澹台敬伯、巨鹿韩伯高最知名”,其后亦有杜抚本人小传,言抚“定《韩诗》章句”,“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
[10]
。杜抚曾先后辟于东平王刘苍之骠骑将军府及太尉府,是当时知名于天下的学者。史载他在犍为所教授的弟子达到千余人之多,冯良与赵晔均出于其门下并非没有可能
[11]
。
又冯良为南阳人,赵晔为会稽人。据《续汉书·郡国志》,犍为在“洛阳西三千二百七十里”,而南阳在“洛阳南七百里”,会稽在“洛阳东三千八百里”。虽然会稽距离犍为要比南阳遥远很多,不过在东汉当时盛行的游学风气中,这样看似遥远的空间距离也并不足以构成决定性的障碍。这方面例子很多。前引《后汉书·薛汉传》言犍为杜抚为薛汉名弟子,而薛汉为淮阳人。又如郑玄出身北海高密,“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师事扶风马融,而在马融门下为郑玄充当介绍人的则是来自涿郡的卢植
[12]
。又如景鸾为广汉梓潼人,“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
[13]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论》所谓“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
[14]
,实非虚言。
总之,单纯从记载内容的“内证”来看,很难判断范晔《后汉书》中的冯良事迹和赵晔事迹何者为伪。有必要暂时离开“史实”与“叙述”单纯对应的视角,从文本本身形成的线索去解释这一历史现象。

二、东汉时代的“不为县吏”群像
如所周知,在范晔《后汉书》于刘宋初年问世之前,已经有多部关于东汉历史的作品存在。构成众书基础的是东汉王朝国史《东观汉记》,其后从三国至两晋时期,多种纪传体、编年体东汉史层出不穷。到了南朝初年范晔著成《后汉书》,实际上与先前的诸家“后汉书”存在诸多形式的密切关联
[15]
。一方面如刘知几在《史通·书事篇》中所言,“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16]
。另一方面,范书中也不可避免的渗入了若干魏晋南朝方才发展出来的观念,与东汉时代的历史实态已经颇有距离
[17]
。
具体到本文的问题,如果从文本的角度向前追索,在范晔《后汉书》之前,最早可以确认的冯良事迹来自于《北堂书钞》所引《东观汉记》
[18]
。而最早的赵晔事迹则来自《北堂书钞》所引谢承《后汉书》
[19]
,已在三国孙吴时期。谢承《后汉书》所记赵晔事迹的问题将留置下节讨论,这里先来看《东观汉记》所载冯良事迹。如表2所示,可将相关文字按照前述A-E五个情节要素进行分节排列。
表2
|
《东观汉记》载冯良事迹
|
《东观汉记》载逢萌事迹
|
蔡邕《贞节先生陈留范史云铭》
|
|
A
|
南阳冯良,少作县吏。
|
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节,志意抗厉,家贫,给事为县亭长。
|
先生讳丹,字史云,陈留外黄人。(中略)君受天正性,志髙行洁,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节矣。时人未之或知,屈为县吏。
|
|
B
|
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主挞之。
|
尉过迎拜,问事微久。尉去,举拳挝地,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耶?”
|
亟从仕进,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托死遁去,亲戚莫知其谋。遂隠窜山中,渉五经,览书传,尤笃《易》与《尚书》。
|
|
C
|
从杜抚学。
|
遂去学问。
|
|
D
|
妻子见车有死马,谓为盗贼所害。
|
|
|
E
|
良志行高洁,约礼者也。
|
|
学立道通,久而后归。游集太学,知人审友。苟非其类,无所容纳。介操所在,不顾贵贱。其乡党也,事长惟敬,养稚惟爱。言行举动,斯为楷式。
|
作为东汉王朝的国史,《东观汉记》
虽然在唐代以前曾经位列“三史”,但后来地位逐渐为范晔《后汉书》所取代,
至元代就已经全部散佚了
[20]
。
仅凭《北堂书钞》所保留的这段关于冯良的《东观》佚文,难以判断其在原书中的本来位置。从“南阳冯良”而非“冯良,南阳人也”这样的表述来看,这段文字或许也是来自附传或者插叙,而非正传。范晔《后汉书》于《周燮传》下插叙冯良事迹,其来有自。另外,如“主挞之”和“从杜抚学”之间,或者“谓为盗贼所害”和“良志行高洁”之间,以文意推之,应该都是有所节略的,当非《东观》原文全貌。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北堂书钞》引《东观汉记》所保留的冯良事迹,在A-E五个情节要素的设定上是非常完整的,叙述次序与范晔《后汉书》完全一致,“县吏”、“坏车杀马,毁裂衣冠”、“杜抚”等关键细节也已经出现。就目前的史料状况而言,基本可以认为这一文本是范晔《后汉书》中冯良事迹与赵晔事迹的最早源头。
但《东观汉记》中的这一冯良事迹文本,与范晔《后汉书》相比,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并未出现“年三十,为尉从佐”这样具体的年龄和身份,也没有“奉檄迎督邮”这一极富场面感的设定。这可能是因为《东观汉记》原本即缺失相关信息,但也不能排除是《北堂书钞》在引用《东观》文字时节略的结果。从“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的表述来看,《东观》原文本来也存在一个具体的场景设定,否则就无所“因”了。而在冯良如此行为之后,招致“主挞之”这样的惩罚。如后文所述,这是仅见于《东观汉记》的独特记录。说明他破坏象征县吏身份的公物行为似乎并不隐秘。上级部门对冯良的公开惩罚羞辱,可能才是他其后“(遁至犍为,)从杜抚学”的最主要动因,县吏身份所带来的耻辱感还未强大到如此地步。冯良事迹在东汉文本与魏晋南朝文本间呈现出的这些差异,并非无关紧要。
如果将眼光扩大到同时代的其他文本,可以发现类似故事在东汉时期并不止冯良一例。《太平御览》引《东观汉记》载有逢萌事迹,如表2所示
[21]
。在A-E的五个情节要素之中,这一文本至少可以在前三个方面都对应起来
[22]
,均为不愿做县吏后又去游学之事。但是与冯良事迹相比,构成各个情节要素的关键细节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逢萌为县亭长,而非笼统的“县吏”。在感受到这一身份的低下时,他的反应是“举楯挝地”且长叹,而非“坏车杀马,毁裂衣冠”。其后外出游学之地也看不出与“犍为杜抚”有关(实际上是在长安太学)
[23]
。所以虽然逢萌的活动时代在西汉末经新莽至于东汉初,远早于冯良的东汉中期,二人事迹的情节要素又多有相通,但就文本而言,很难说二者存在传承关系。《东观汉记》虽为国史,但其中如冯良、逢萌这样以“处士”身份载入者,史料来源很可能就是各郡国作为上计材料提交朝廷的本地耆旧、先贤记录之类
[24]
。
更有对比价值的是蔡邕所撰《贞节先生范史云铭》,这里择取其中叙述碑主范丹早年经历部分列如表2
[25]
。铭文结尾部分言范丹卒于中平二年(185),年七十四
[26]
。则其最初被“屈为县吏”之事大致发生在顺帝时代。与冯良、逢萌的人生轨迹类似,范丹年轻时也做过县吏,后不愿继续,就托死逃到山中,通过长时期研习儒学经典,将自己的身份转变为儒生,回到家乡后成为表率乡里的名士。值得注意的是,在描述范丹从县吏到儒生这一转变过程的位置,即表2中以不同形式见于冯良事迹和逢萌事迹的B-D情节要素,在蔡邕这里并未以清晰的形式体现出来。他既未设定一个如“尉过迎拜,问事微久”这样具体的场景,也没有将范丹的心理定位为“耻在厮役”,只是在强调他年少时即已“藐然有烈节”的基础上,将“亟从仕进,非其好也”书写为他转变身份的主要动机。
此铭文结尾说范丹死后,“太尉张公、兖州刘君、陈留太守淳于君、外黄令刘君,佥有休命,使诸儒参按典礼,作诔著谥,曰‘贞节先生’。昭其功行,录记所履,谋于耆旧,刊石树铭,光示来世”
[27]
。范丹成名后,不断受到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的辟召,虽基本未有应命,但官方记录应该均有留存,不难查找。而其“不为县吏”的早年经历,至少发生于半个世纪之前,除了“谋于耆旧”即向本地故老打听之外,确实难有他途。蔡邕铭文中对范丹早年经历的记录形式,应该就是“谋于耆旧”的结果,而非限于碑铭体裁略而不言
[2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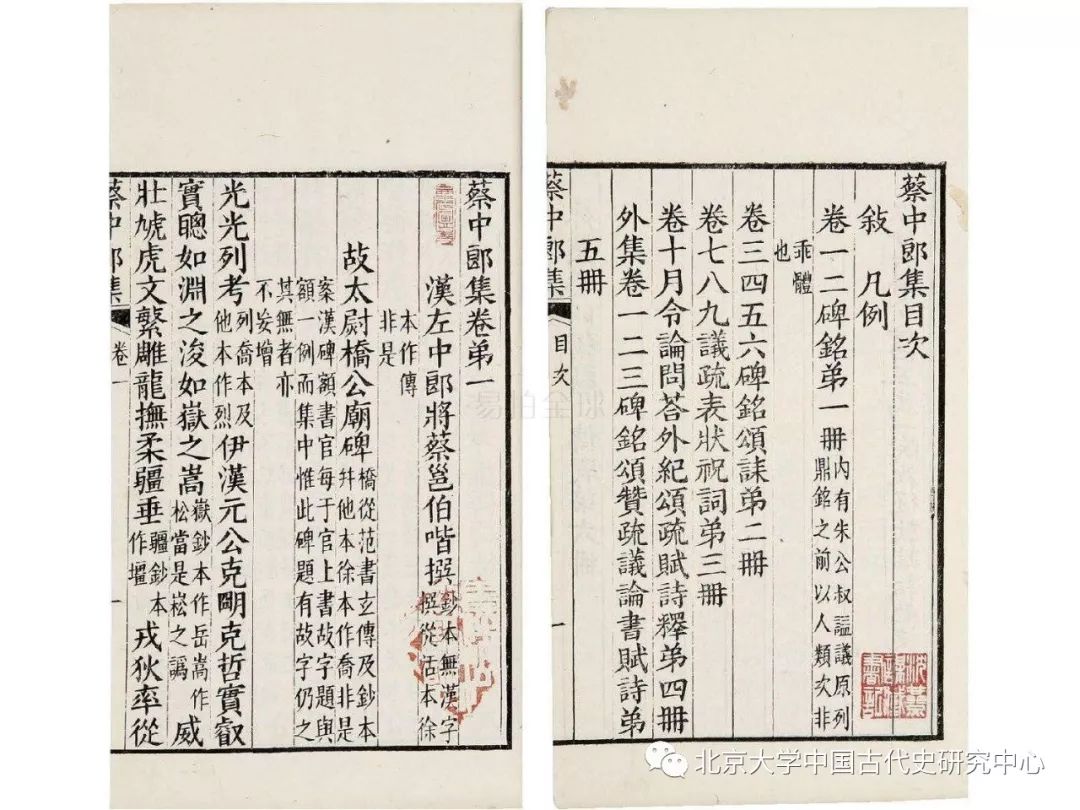
可以看到,表2所列的三个例子,材料出自不同,人物故事各异,但情节要素反而一致度颇高。实际上冯良事迹与逢萌事迹最初虽然可能出之于郡国上计材料,却同被收入国史《东观汉记》;范丹早年事迹来自于家乡耆旧所言,但蔡邕将之写入碑铭,显然也受到了从县、郡、州到太尉各级官府长官及“诸儒”的一致认可。这显示地方士人对于县吏身份的拒绝,以及与之相反相成的对于儒生身份的追求,在东汉时期已经是一种受到精英阶层推崇和宣扬的意识形态。这是伴随着地方上儒学教育的普及与知识阶层的形成
[29]
,而出现的新历史现象。对于汉代传统的地方属吏而言,基本的素质要求是对文书的处理能力和对相关律令的熟悉与把握
[30]
。在地方官僚系统中的升迁,也主要是从最底层的卑微小吏做起,以“积功劳”的方式一步步进行的
[31]
。但这样的仕进和生活方式,对于东汉时期的士人来说,却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了。书写在国史和碑铭上的冯良、逢萌和范丹事迹,实际上既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不同表现,也通过这些书写和宣扬加速了这一进程
[32]
。
三、赵晔事迹与孙吴精英的地方书写
上节指出了范晔《后汉书》所记冯良事迹,最早来源于东汉国史《东观汉记》。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范书中与冯良事迹高度相似的赵晔事迹呢?
如表3所示,赵晔事迹今天所能追溯到的最早史源是《北堂书钞》所引谢承《后汉书》。此段文字来自于《北堂书钞·艺文部》的“檄”条,故只是摘取了原书中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部分,事情其后的发展付之阙如。不过,即使只就现有文本的情节要素A-C进行比较,也很容易看出谢承《后汉书》所记赵晔事迹与《东观汉记》所记冯良事迹在情节设定上的高度相似,其中也包含了少为“县吏”、以“斯役”为“耻”、从“杜抚”学这些关键细节的雷同
[33]
。
表3
|
《北堂书钞》引《东观汉记》冯良事迹
|
《北堂书钞》引谢承《后汉书》赵晔事迹
|
|
A
|
南阳冯良,少作县吏。
|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少尝为县吏。
|
|
B
|
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主挞之。
|
奉檄送督邮。晔心耻斯役,遂弃车马去。
|
|
C
|
从杜抚学。
|
到犍为,诣杜抚受《韩诗》。
|
|
D
|
妻子见车有死马,谓为盗贼所害。
|
|
|
E
|
良志行高洁,约礼者也。
|
|
谢承《后汉书》的成书在三国孙吴时期,是《东观汉记》之后出现的第一部关于东汉历史的纪传体王朝史
[34]
。作为一部以孙吴为正统的前代纪传体王朝史,其书一方面以《东观汉记》为主要史料来源,一方面又对东汉时期的江东人士多有侧重
[35]
。刘知几在《史通·烦省篇》中批评“谢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
[36]
。吴树平也指出:“《东观汉记》的作者不会像谢承那样偏爱江左人物,某些江左人物,谢承书有传而《东观汉记》无传是完全可能的。”
[37]
身为会稽山阴人的赵晔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如此。如上节所论,东汉时期类似冯良“不为县吏”之事并不罕见,在后期更是成为精英阶层广泛认可的意识形态。冯良事迹之外,如逢萌、范丹事迹也各有不同表现的叙述。谢承《后汉书》中若出现包含“不为县吏”情节要素的事迹记述并不值得惊讶。但是在情节要素的设定和关键细节上出现如表3所示的如此重合,只能认为谢承《后汉书》中的赵晔事迹当本于《东观汉记》中的冯良事迹。谢氏或利用赵晔与冯良同为杜抚门生这一共同点,将冯良事迹移植至赵晔身上,以彰显、提升江东本地精英在东汉时期的社会地位与历史形象
[38]
。至于谢承《后汉书》中是否还保留有《冯良传》,就不得而知了。
值得注意的是,谢氏亦为会稽山阴人。而据《隋书·经籍志》,谢承在《后汉书》外,尚著有《会稽先贤传》七卷
[39]
。《会稽先贤传》中收录赵晔事迹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旁证。《太平御览》卷五五六《礼仪部·葬送》引虞预《会稽典录》曰:
赵晔,字长君,山阴人也。少为县吏。奉檄迎督邮,甚耻之,由是委吏。到犍为,诣博士杜抚,受《韩诗》。抚嘉其精力,尽以其道授之。积二十年不还,家人为之发丧制服。至抚卒,晔经营葬之,然后归家。
[40]
这段文字所记赵晔事迹较谢承《后汉书》更为完整,在文本面貌上与表1所示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赵晔》也已经相差无几。虞预出身会稽余姚,活动于东晋前期,《晋书》本传载其著《会稽典录》二十卷
[41]
。《史通·杂述篇》将虞预此书与圈称《陈留耆旧传》、周斐《汝南先贤传》、陈寿《益部耆旧传》共同归于“郡书”之列
[42]
。谢承的《会稽先贤传》性质亦当近之。那么上引《会稽典录》中的赵晔事迹,很可能就是承袭自孙吴时期的《会稽先贤传》。更进一步来说,这与谢承《后汉书》中《赵晔传》原来的文本面貌可能也相去不远。
谢承《后汉书》中的赵晔事迹,与《东观汉记》中的冯良事迹两相比较,除了因袭之外,在情节上也有新的发展,即在情节要素B中,增加了“奉檄送督邮”,而删去了“主挞之”。“奉檄送督邮”是一个极富场面感的具体设定,以至于引起了《北堂书钞·艺文部》编者的注意,将其特意收录于“檄”条之下
[43]
。前文指出了《东观汉记》所记冯良“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的行为应该存在一个具体的场景设定,只是在《北堂书钞·设官部》引用时被略去了。那么,被略去的是否即为“奉檄送督邮”呢?从下面将要看到的东晋时期《后汉纪》与《抱朴子》所记冯良事迹来看(详见表4),“送/迎督邮”的场景设定在《东观汉记·冯良传》中应该已经存在,但“奉檄”这个更为具体的细节,则是谢承《后汉书》在因袭冯良事迹来书写赵晔时的新发明。虞预《会稽典录》对“奉檄迎督邮”这五个字的忠实传承,也正说明了它与谢承所著《后汉书》与《会稽先贤传》之间的密切关系。
谢承《后汉书》将《东观》原文中的“主挞之”三字删去也值得注意。如前文的分析,《东观汉记》将“主挞之”三字置于“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和“从杜抚学”之间,实际是强调了上级部门的公开羞辱与冯良其后“遁至犍为,从杜抚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削弱了县吏身份本身给他所带来的耻辱感。如表2所见,东汉时不为县吏之例虽然所在多有,但明言以之为“耻”者却并不多见。到了三国孙吴时代的谢承《后汉书》以《东观汉记》中的冯良事迹为蓝本书写赵晔事迹时,则一方面以“奉檄”这一细节进一步渲染了“迎督邮”时的县吏身份之卑微,一方面又删去“主挞之”的环节,强调赵晔本人对县吏身份的耻辱感已经足以构成他其后“弃车马去。到犍为,诣杜抚受《韩诗》”的行为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赵晔虽然被谢承作为孙吴精英的地方先驱而书写,但弥漫其间的是魏晋时期新意识形态的整体进展,并不仅限于江东一隅。或者反过来说,孙吴精英为其地方先驱所书写的历史形象,正是按照汉魏间登上历史舞台并把握政治主导权的士人阶层的主流观念而量身定做的
[44]
。在汉代尚显模糊的“士、吏之别”,魏晋时期以制度化的方式急速推进,表现在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选官论清浊等各个方面
[45]
。政治上的建设进程显然也促进了士人对于新身份的自我认定。
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另一位汉末名士
郭泰早年事迹书写的变化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范晔《后汉书》卷六八《郭泰传》载: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
[46]
范书记郭泰早年“给事县廷”,且自言为“斗筲之役”,遂辞而就学,这与前文所论冯良、逢萌、范丹等人事迹颇为相似。然而东汉末蔡邕所作《郭有道碑》所描摹的郭泰形象,与此却颇有差距:
先生诞应天衷,聪叡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尔乃潜隐衡门,收朋勤诲,童蒙赖焉,用袪其蔽。州郡闻德,虚己备礼,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举有道,皆以疾辞。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
[47]
如学者所指出的,在《郭有道碑》这一距离郭泰本人时代最为接近的史料中,郭泰主要的形象为“隐逸”,而后世熟悉的“人物品评家”形象,是在魏晋南朝时代逐步发展出来的
[48]
。同样,以“斗筲之役”这一细节为特征的郭泰早年事迹,也不见于《郭有道碑》。目前可以确认的最早来源是西晋时皇甫谧所作《高士传》
[49]
。皇甫谧虽终身不仕,但著述颇丰,在当时即为朝野所重
[50]
。他在《高士传》中为郭泰早年事迹加入“不为斗筲之役”的情节,与其说是继承了汉末以来的某一具体文本,毋宁认为是以魏晋以降“士、吏之别”的加速建构为观念基础而出现的歧变。就性质而言,与之前的孙吴精英因袭冯良事迹书写赵晔时所发展出的“奉檄”情节并无二致。

四、东晋时代的多面冯良
世入东晋,流亡至江南的士人群体在继承魏晋精英文化的同时,也逐渐发展出了自身的特质。在冯良事迹的历史书写方面,如表4所示(已经按照前文所列情节要素A-E进行了简单排列),袁宏《后汉纪》和葛洪《抱朴子》两种东晋作品的记述幸运留存至今
[51]
,让我们得以观察在前述范晔《后汉书•周燮传》附冯良小传出现之前,原《东观汉记》中冯良事迹文本的多元展开。
表4
|
袁宏《后汉纪》
|
《太平御览·道部》引葛洪《抱朴子》
|
|
A
|
冯良字君卿,少为县吏。
|
A
|
冯良者,南阳人。少作县吏。
|
|
B
|
从尉迎督邮。良耻厮役,因毁其车马,坏其衣冠,绝迹远遁。
|
B
|
年三十,为尉佐史,迎督邮。自耻无志,乃毁车杀牛,裂败衣帻去。
|
|
D
|
妻子见败车坏衣,皆以猛兽所食,遂发丧制服。
|
C
|
从师受《诗》、《传》、《礼》、《易》,复学道术占游候。
|
|
C
|
良至犍为,从师受业十余年。
|
D
|
|
|
E
|
还乡里。虽处幽闇,必自整顿,非礼不动,乡里以为师。举贤良、方正、敦朴皆不行。
|
E
|
十五年乃还。州郡礼辟不就。诏特举贤良髙第,半道委还家。
|
|
|
F
|
年六十七,弃世东度入山,在鹿迹洞中。
|
先来看
袁宏《后汉纪》。袁宏此书约成于东晋中期,在范晔《后汉书》之前五十余年
[52]
。与表2所列《北堂书钞》引《东观汉记》相比,《后汉纪》明确记录了冯良以县吏厮役为耻的具体契机,即“从尉迎督邮”。如前文所指出的,《东观汉记》本文在“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之前,应该存在一个具体的场景设定,否则就无所“因”了。《后汉纪》的记述说明这一被《北堂书钞》在引用《东观》文字时所节略的具体场景很可能就是“从尉迎督邮”。袁宏在《后汉纪》序文中明言他所利用的资料包括“其所缀会汉纪〔记〕、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
[53]
。则从《东观汉记》到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
[54]
乃至东晋袁宏《后汉纪》,冯良早年事迹的书写或当一直保持了“从尉迎督邮”的形式。而前述孙吴谢承《后汉书》在因袭《东观》冯良事迹书写赵晔时所发展出的“奉檄迎督邮”细节,并未被其后的主流“后汉书”书写所继承,只是在孙吴精英的地方书写中延续文脉。
同时,《后汉纪》文本也有新的发展。除了调整情节要素C与D的顺序之外,最为显著的调整就是对于冯良的坏毁车马衣冠行为,袁宏删去了《东观》原文中的“主挞之”。同样的文本更动也见于前述谢承《后汉书》中的赵晔事迹。显然《东观》原文的表达暗示了上级部门对冯良的公开惩罚羞辱可能才是他其后“(遁至犍为,)从杜抚学”的最主要动因,反而降低了县吏身份本身所带来的耻辱感,已经不及于魏晋以降“士、吏分途”的观念进展,所以从谢承书以降即消匿不见。从这一角度来看,《后汉纪》中的这一表现也未必是袁宏直接改写《东观》原文而成,不能排除在先于《后汉纪》成书的如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诸书中就已经形成了这一文本面貌
[55]
。
关于冯良所从学之师,《后汉纪》中未出现杜抚之名,仅言“至犍为,从师受业十余年”。周天游认为这显示了袁宏对冯良所从学者为杜抚的怀疑:
按:范书《周燮传》言良师乃犍为武阳人杜抚。杜抚虽于乡里授弟子千余人,然后应东平王苍之辟,至永平五年苍就国始归。不久复辟太尉府,建初中,卒于公车令职。传言良年三十入蜀,七十余岁卒。若以永平元年抚应辟计,至建光元年,近百岁矣;以建初元年计,亦八十余年,良岂能于蜀从抚受学达十余年之久!袁《纪》不言其师之名,恐其亦疑焉。
[56]
周氏质疑的论据来自于《后汉书·周燮传》所记冯良入蜀受业年龄(年三十)及享寿年龄(七十余卒)与杜抚的活动时间之间的矛盾。据前引《后汉书·儒林·杜抚传》,杜抚于建初中卒于公车令之位。则冯良入蜀从杜抚学,至迟也应在建初八年(83)之前。但其后周氏的质疑却未必成立。若将冯良三十岁入蜀的时间点设定于永平元年(58)杜抚应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之辟命时,则延光二年(123)他与周燮一起受安帝礼聘时
[57]
即已年过九十(遑论设定于此年之前),与其享寿年龄不符,自然是不成立的设定。而若将冯良三十岁入蜀时间设定为周氏所言的建初元年(76),则延光二年时冯良年龄为七十七岁,并非周氏所言的“八十余年”,与其享寿年龄并不矛盾。
事实上,如表4所示,《后汉纪》中虽然有冯良因耻迎督邮而入蜀受业的情节,但并未记载“年三十”这样具体的年龄设定。相反,在“少为县吏”之后直接出以“从尉迎督邮”之语,似暗示冯良绝迹入蜀之时年龄尚少。范晔《后汉书·周燮传》所记冯良事迹中确实出现了他三十岁时因以县吏厮役为耻而入蜀求学的记载。但范书晚出于袁书约半个世纪,以此为据来反推袁宏在《后汉纪》中未记录杜抚之名的意图,未必妥当。
考虑到有《东观汉记》的明确记载,冯良与杜抚之间的师生关系应该是较为确实的
[58]
。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找到另一条材料以为佐证。《华阳国志》卷十中《犍为士女赞》赞杜抚曰“叔和(杜抚字)顺终”,后附杜抚小传,文末记“弟子南阳冯良,亦以道学征聘”
[59]
。《华阳国志》成书时间早于《后汉纪》数十年,所依据的材料如陈寿《益部耆旧传》之类当然更早
[60]
。冯良作为杜抚的弟子在其小传结尾被特别提及,说明二人之间的师生关系在汉晋后期以降是得到了普遍的记忆与表彰的。《后汉纪》行文所言的“至犍为,从师受业十余年”,可能只是受限于体裁而没有特意点明而已,无他深意。
不过,《后汉书·周燮传》所言的冯良年三十因耻迎督邮而绝迹入蜀之事,应该也并非范晔所杜撰,而是有其来源,即表4所见《太平御览》所引葛洪《抱朴子》。葛洪活动时代较《后汉纪》作者袁宏更早,以东晋前期为主
[61]
。这段文字并不见于今本《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
[62]
,学者或以之为《内篇》佚文
[63]
。从葛洪自己在《抱朴子外篇·自叙》对《内篇》、《外篇》内容的区分来看,“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64]
,确有可能出自《内篇》。范晔《后汉书》冯良事迹中“年三十”的年龄设定,最早就出现在这里。
葛洪后世虽以道教人士知名,但如《抱朴子》分内、外篇所示,他的知识结构毋宁说属于儒、道并重
[65]
。读书经眼范围比一般的东晋士族精英或有过之而无不及
[66]
。他在《外篇·自叙》中谈到自己“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
[67]
,“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
[68]
。所抄诸史中,至少有一种名为《后汉书抄》
[69]
。学者或以此“后汉书”为《东观汉记》
[70]
,但并不能排除后起的如华峤《后汉书》之类著作的可能性。前引袁宏在《后汉纪》序文中所提及利用的史料范围,包括《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及诸郡“耆旧传”、“先贤传”等,推测也当在葛洪的阅读范围之内。
但葛洪对《抱朴子》的定位为“子书”,尤其内篇旨趣在于“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故其中出现的冯良事迹文本创新度较高,与袁宏利用前人史料时以“缀会”为主大异其趣。葛洪似有意隐去了冯良出走后所从师为川中名儒杜抚,并在其学习内容中增加了“道术占候”
[71]
。更为重要的情节要素变动,则是为冯良设定了“年六十七,弃世东度入山,在鹿迹洞中”这样以道士形象为依归的晚年结局。之前的“年三十,为尉佐史”、“十五年乃还”等时间要素,或许都是对应这一结局而依次设定的。葛洪的这些文本改造,尽管并无具体的材料来源,还是为东汉后期以降冯良的儒学名士经典形象,成功渲染了早期道教的色彩。这一改造一方面为之后南朝的道教文献所继承
[72]
,一方面又成为了范晔《后汉书》的资源汲取对象。
五、结 语
综上所论,可以认为范晔《后汉书》中之所以形成高度相似的冯良事迹与赵晔事迹,原因要比何焯所谓的“必一事而传者互异”更为复杂。简单总结如下。
就史源而言,东汉国史《东观汉记》所记冯良事迹构成了最初的文本起源。这一类型的书写在东汉后期颇有其例,与当时“士、吏之别”的起源正相对应。
成于孙吴的谢承《后汉书》以《东观汉记》所记冯良事迹为蓝本,书写了江东名士赵晔事迹。同时,也加入了“奉檄迎督邮”的新细节。这一文本在孙吴精英的地方书写中延续有年。
东晋时期的袁宏《后汉纪》与葛洪《抱朴子》,则在《东观汉记》以来诸家“后汉书”所记冯良事迹的基础上,通过发展若干相异的新细节,使冯良分别呈现为儒学名士和道教先驱的不同形象。而谢承《后汉书》在赵晔事迹书写中发展出的“奉檄迎督邮”细节,尚未进入东晋时代的冯良事迹。
至刘宋初范晔著《后汉书》时,对冯良事迹进行了明显的综合。冯良事迹所在的
《后汉书》卷五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集中收录了东汉后期引人注目的“处士”群体代表
[73]
。周燮与冯良被范晔作为这一群体的早期代表人物置于开篇位置。在这一文脉下的冯良事迹,大体继承了《东观汉记》以降至于袁宏《后汉纪》的主流书写。特别是对于冯良早年“耻为县吏”事迹的强调,与东汉文本拉开了一定距离,正与魏晋南朝日趋显著的“士、吏之别”相对应。由此也很容易理解
《抱朴子》所述的诸如“复学道术占侯”、“年六十七弃世入山”之类带有明显道教色彩的情节,范书就完全未予采用。
不过《抱朴子》在书写“道教先驱冯良”时所发展出的某些细节,如“年三十为尉佐史”,却也被范晔作为有价值的信息片段整合进了《后汉书》所记冯良事迹之中。而谢承《后汉书》以《东观汉记》冯良事迹为蓝本书写江东名士赵晔时发展出的“奉檄迎督邮”细节,到范晔这里,又反过来被编入《后汉书》的冯良事迹之中,尽管这一表述与同书《赵晔传》雷同。
以上通过讨论范晔《后汉书》中冯良事迹的成立过程,呈现了中国古代史学作品中文本传承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以往诸如史实/叙述、作者/作品等视角中并不能得到完全把握。在此笔者尝试用因袭、歧变与反哺这一组关键词来进行概括。所谓“因袭”,是指文本在传承中大体保持原貌。在语境不发生大的改变的前提下,这种形式最为常见
[74]
,甚至是古人的一种常识。以至于在作品中直接抄录袭用而不特意标明出处的情形所在多有。但这种因袭根据作者和作品的不同情形,往往伴随着“歧变”,即出现不见于前一文本的新细节。这种新细节可能是作者因特殊的关怀有意为之
[75]
;但也有很多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如本文所述谢承《后汉书》书写赵晔事迹,基本沿袭了《东观汉记》的冯良事迹,同时又发展了“奉檄迎督邮”的新细节。歧变在文本传承中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归于消亡者众,但根据文本传承的层累机缘,也有反而成为被因袭对象的可能性,是为“反哺”。赵晔事迹中歧变出的“奉檄迎督邮”,到了范晔《后汉书》中又被整合进冯良事迹行文,正是一个典型表现。那么,面对古代史料中的具体文本,若能够对其所蕴含的因袭、岐变与反哺的层累过程有一定意识,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的把握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
(附记:
本文原刊《中国学术》第38辑,2017年。感谢刘东先生、邱源媛女史的邀约和指正。)
[1]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1742-1743
页。此事又见同书卷四六《陈忠传》:“及邓太后崩,安帝始亲朝事。忠以为临政之初,宜征聘贤才,以宣助风化,数上荐隐逸及直道之士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于是公车礼聘良、燮等。”第1556页。
[2]
《后汉书》,第
1743
页。
[3]
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
[4]
关于光武帝省罢郡尉的经过及原因,参考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45A
,
1961
年,第
153
页;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郡都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初出
1985
年,
2005
年新
1
版,第
339-341
页。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所录《续汉书·百官志》“郡太守”条所含的“尉一人”,是整理者因未谙《续汉书·百官志》体例而误补。参考徐冲:《〈续汉书·百官志〉与汉晋间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条的辩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
2013
年第
1
期,又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
[5]
《后汉书》此处李贤注曰:“从佐谓随从而已,不主案牍也。”
[6]
关于东汉后期地方社会中的儒学士人形象,参考都築晶子:《後漢後半期の処士に関する一考察》,《琉球大学法文学部紀要•史学地理学篇》
26
,
1983
年。
[7]
《后汉书》,第
2575
页。
[8]
参考曹林娣:《关于〈吴越春秋〉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西北大学学报》
1982
年第
4
期;陈桥驿:《〈吴越春秋〉及其记载的吴、越史料》,《杭州大学学报》
1984
年第
1
期;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绪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9]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四《后汉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402
页;又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对何焯意见也有引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
901
页。
[10]
《后汉书》,第
2573
页。
[11]
当然这种师生关系很可能只是停留于“编牒”登记的层次,未必是面授亲传。东汉中期以后名儒在地方开学授徒,多有至数千上万者,其中真正为名师亲授者只是少数。《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记其西入关中拜扶风马融为师,融门徒四百余人,能够“升堂进者”不过五十余生。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而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第
1207
页。
[12]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
1207
页。
[13]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景鸾》,第
2572
页。
[14]
《后汉书》,第
2588
页。
[15]
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1988
年;安部聡一郎:《後漢時代關係史料の再檢討
-
先行研究の檢討を中心に
-
》,《史料批判研究》第
4
卷,
2000
年。
[16]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第
230
页。
[17]
这方面日本学者安部聡一郎有相当具开拓性的系列研究,值得关注:《後漢時代關係史料の再檢討
-
先行研究の檢討を中心に
-
》;《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学雑誌》
111-10
,
2002
年;《『後漢書』郭太列伝の構成過程——人物批評家としての郭泰像の成立》,《金沢大学文学部論叢》(史学
・
考古学
・
地理学篇)
28
,
2008
年;《隠逸、逸民的人士と魏晋期の国家》,《歴史学研究》
846
,
2008
年,中译文载《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3
卷,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另参徐冲:《东汉后期的“处士”与“故吏”再论——以〈隶释•繁阳令杨君碑〉所载“处士功曹”题名为线索》,《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后收入氏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18]
《北堂书钞》卷七七《设官部·吏》,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影宋本,
1989
年。又可参考(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十七,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第
723
页。
[19]
《北堂书钞》卷一〇三《艺文部·檄》。又可参考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第
165
页。
[20]
参考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中有关《东观汉记》的诸文;安部聡一郎:《後漢時代關係史料の再檢討
-
先行研究の檢討を中心に
-
》;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史学史研究》
2001
年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