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喜欢京剧,另一种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
”
当王珮瑜身着一袭黑色长衫说出这段话时,很多人被她气定乾坤的神韵圈了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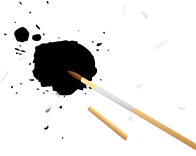

我很好奇,眼前这个在舞台上独有一束光的角儿,过去经历了什么?如今,又被打磨成了何种模样?
王珮瑜名字中的珮、瑜两个字都有美玉的意思,想必父母起名时,希望她将来能成为“温润如美玉,流盼有光华”的女子。
在王珮瑜眼中,父母的性格南辕北辙。父亲是典型的医学工作者,严谨、崇尚逻辑、循规蹈矩。他对王珮瑜的期待是“多读书,将来做个知识分子”。
母亲则是特立独行的文艺女青年,她着重培养王珮瑜的艺术才华。打小儿,母亲就经常告诉她:“任何人议论你、质疑你都没关系,你就是与众不同的。”为了保持女儿的“独特”,她甚至不建议女儿参加学校的春游活动。
然而事实证明,母亲的眼光是精准的,王珮瑜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学什么都有模有样,她8岁就凭借一曲评弹《新木兰辞》名满苏州。
11岁时,舅舅给王珮瑜“浇了一盆冷水”:“这些学得好不算什么,你能把京剧唱好了,那才叫厉害!”这句话,让年少不服输的王珮瑜来了动力。几个月后,她就凭一出《钓金龟》获得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
一次,她遇到了余派资深学者范石人,范老建议她改学老生。“我当下就同意了,老生多帅啊,而且能挑大梁。”
14岁那年,上海戏曲学校招生,王珮瑜得到了所有老师的认可。但自建国以来,中国戏曲学校的老生专业从未招收过女生,谁也不想开这个先河。甚至有老师劝她:“条件这么好,干吗学戏啊!”
王珮瑜煞费苦心地写了一封自荐书,让母亲连同获奖证书一起带着来到了上海市文化局。母亲守在了局长办公室门口,一等就是4个多小时。
马局长被她们的执着打动,她看着王珮瑜的资料说:“冲着你们的这股冲劲儿,我开个绿灯,但有个条件,先试课一年,一年后如果跟不上,那还得退学。”
王珮瑜顺利入学,师从王思及老师学习老生专业,成为了建国后国家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也正是因为王珮瑜的先河,自此全国各大戏剧学校的老生专业陆续修改规定:招生不分男女。

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王珮瑜的人生,仿佛行走在了云彩之上。
在戏校的老师和同学心中,她是明星学生。但只有王珮瑜知道,这里面该吃的苦、该练的功、该掉的眼泪,她一份儿也没落下。
15岁那年,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梅葆玖先生第一次在上海兰心大舞台听到王珮瑜唱戏。一下台,他一把抱住她:“你怎么唱得这么好!”
两年后,正在读四年级的王珮瑜赴京演出,京剧名家谭元寿听完王珮瑜的《文昭关》惊呼:“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孟小冬吗?”

这位曾目睹过孟小冬最后一次登台义演的京剧大师提出:“我陪这孩子唱出戏。”戏码就选了《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赫赫有名的“谭门”掌门人,给一名戏校四年级的学生配戏,这提携非同一般。自此,王珮瑜“小孟小冬”“小冬皇”的名号不胫而走。
然而,让更多人认识王珮瑜的,是陈凯歌电影《梅兰芳》。电影中,有梅兰芳与孟小冬对唱《游龙戏凤》的情节,梅葆玖先生配唱梅兰芳。而王珮瑜接到了剧组的电话:“葆玖老师让我们来找您,他说,当下能给孟小冬配唱的,唯有王珮瑜。”
说到“成名全不费功夫”的这些年,王珮瑜还补充道,9年戏校生涯,她最自豪的却不是这些众星捧月般的厚待,而是占了宿舍里半张床的书。“我不希望因为唱戏而忽略了对知识的学习,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或至少是对文化有追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