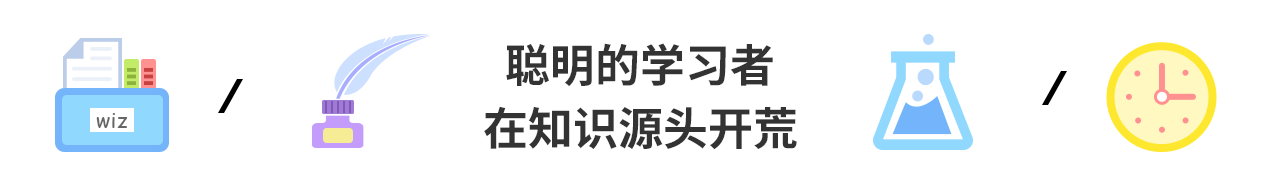
— Note171018003 —
「怎么突然想到她了,你们什么时候结束的?」
「结束?」
「对啊,你们不是在恋爱吗?」……?

4
早晨醒来时,莎梅尔还在睡觉。弗利走到约翰房间,被子完全掉落在地,约翰撅起小屁股睡的正熟。机器人可不会这样睡觉,想到这弗利笑了起来。每个早晨都和前一个早晨一样,没有任何不同。他来到厨房煮上咖啡,打开工作提示,熟悉的女声以一成不变的速度告诉他一天该做的事。
事情可真不少,可弗利觉得似乎还能更多些,他想要更多的工作,甚至越多越好。好奇怪,为什么会想要更满的安排?他有些困惑。低头刷牙,弯腰吐水的时候背部再次传来不适,弗利这才想起昨天去过何塞医生的办公室;想起外科西大楼九楼最靠北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张宽大的座椅;他想起绿色的窗帘以及何塞光着的脚。
都发生过,这一切不是想象,它们确实都发生过,就在昨天。弗利用力含住一口水,快速把他们变成无数细小的泡沫,最后无力的吐出来,不适感随着旋转的泡沫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翻涌的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但无法抹去。它们就在那里,在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一个小医生,又矮又小,但无疑是上帝的代言人。
「见鬼。」弗利再也没了刮胡子的心情,右手的骨头好像被锋利的铁丝捆绑住一般。他站在镜子前凝视自己,一张足够英俊的脸,深邃的眼神,浓密的头发;一张没有被热情抚摸过的脸,一张无精打采的脸,和另一张脸。他没有害怕,而是盯住这张面孔,直到看清镜子里模糊的影像是一个女人。他认出这张脸——艾菲娅。不清晰的五官并没有影响弗利的判断,艾菲娅,艾菲娅,不会错,一定是她。又一次想起消失的女友,他有些疑惑,为什么何塞会让他想起艾菲娅,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已经很多年没有想起过这个女孩,为什么偏偏在这样的时候。
咖啡机发出惨淡的滴哩声,妻子说不喜欢这款机器的声音,去年开始她连咖啡都戒了。渐渐的妻子不再和自己一起吃早餐,大多数时候等弗利来到餐桌只剩下妻子留下的一份面包或者鸡肉。莎梅尔的作息非常规律,上午七点起床去公司,处理一天的事务,十点半外出跑步或者练习瑜伽,午餐通常只是一些蔬菜。下午约见客户,接着就去学校接约翰回家。她在一家传媒公司从事插画设计,画画似乎是弗利所知莎梅尔唯一的爱好,刚结婚那会有一次他看见莎梅尔在整理相册,里面是她从小到大得奖的作品。「父亲一直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有名的画家,我却始终不能让她满意」。莎梅尔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看弗利,虽然带着笑容,但在弗利看来她并不真的快乐。
也许是遗传,约翰三岁起就开始在纸上涂抹,对盘旋的线条更是偏爱,有时候他可以在小桌子前画一个小时,一个一个的螺纹,约翰说那是眼睛,真是叫人喜欢的比喻。想到这里弗利不禁笑了起来。
吃完早餐,再次来到儿子房间时,约翰已经翻过身体咬着自己的手指等待着他,最近半年,每天早上约翰都会在八点多醒来,睡眼惺忪的等弗利开门。看到弗利走进来,约翰小小的嘴就会露出甜蜜的微笑,看着红红的脸蛋和甜蜜的笑容,弗利时常觉得约翰简直就像个小女孩。
「早上好,小家伙。」
「早上好,大个子。」
「快穿衣服,今天有新的牙膏。」
「新的牙膏…」
「你最喜欢的草莓口味。」
「不,我不要草莓口味,我要原来的牙膏,小时候用的,不要草莓牙膏。」
约翰突然大哭大叫起来,与他安静温和的性格判若两人。弗利不知所措,一脸茫然,脑子里快速闪过各种应对方式,可是哪一种都不好,好像什么话都没办法让他立刻平缓下来。
「可是原来的牙膏用完了,约翰。」
弗利寻找了半天却说了一句最不合时宜的话。惹得约翰又是一阵大哭大叫,这下弗利真的吓到了,约翰的表情绝不是撒娇或者故意让人不高兴,他仿佛努力不去哭泣,手指咬在嘴中,又拉扯被子,踢着腿,可这么做却毫不减轻哭喊。
弗利只能茫然的看着儿子,他突然想到也许弗利是害怕,对改变原有习惯的害怕。自从开始刷牙起约翰从没有换过牙膏,也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牙膏是会变的,在听说有了新牙膏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是什么让他如此害怕,**情绪瞬间爆发,无法遏制。
他傻傻的站在约翰房间里,直到哭喊变成断断续续的抽泣。
「那今天不刷牙了,下班我带原来的牙膏回来。」
「好的,爸爸。」
「快穿衣服吧,自己可以吗?」
「当然,爸爸。」
弗利走出房间不停回想刚才发生的哭闹,更加确定约翰脸上的表情是一种恐惧的表现。约翰害怕什么,一支牙膏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威力?紧接着,仿佛很自然的弗利想到了自己,如果爸爸突然消失了,被其他东西取代了,约翰会害怕吗?
原本他想体会下孩子的心情,可走回厨房的时候他在看到的第一张餐椅上坐了下来,胸口蒙上了一层食品保鲜膜般,桌面变的异常坚硬,大脑不再能转动;这一切不知持续了多久直到约翰的脚步声把他叫醒。
「衣服都整理好了?」
「是的。」
「吃饭吧,脸洗过了吗?」
「嗯,但是没有刷牙。」
「不是说好不刷牙吗?不要让妈妈知道就好。」
约翰再次笑起来,趁他吃麦片的间隙弗利整理好带到学校的玩具和自己的包,又想起早上镜子中看到的艾菲娅,也许她也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是不是也和她一样有着深褐色头发。
开车去学校的路上,约翰一直很安静,艾菲娅在弗利脑中不断出现,开始几次他只觉得是偶然想起,到后来弗利接受并且纵容自己回到那段回忆中,总比想到医院好的多吧,他这样告诉自己。
5
开完上午的会,弗利终于有时间喝上一杯水,想起早上约翰的哭吵他感到胸口一阵刺痛。
办公室隔着玻璃就能看到罗德,弗利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心神不安,尤其是罗德。罗德今年34岁,和弗利年龄相仿,但在工作能力上却让弗利时常感到压力,也许这个年龄有没有家庭羁绊的确很不一样。如果自己一直单身,就和刚离开大学那样努力,一心只想着获得能力上的认可,也许如今正在为自己喜爱的事业快乐的奋斗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论做什么都有些紧张,一些担忧,即使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却也不能单纯的全力以赴。
单身的罗德完全没有这样的烦恼,不仅少了家庭羁绊,精力上也远比自己旺盛。同时期到公司的同事都知道等到他顺利完成手上的项目,成为公司合伙人也不在预料之外。相形之下,就算看上去和罗德同样优秀,可背后的勉强也许只有弗利自己心知肚明。
「请再也不要说这些了,贝鲁斯先生,我还有事,下次您要是有更好的合作先和汤米聊,他喜欢喝你那种加了糖的气泡水。」罗德的话似乎想让这个区域的所有人都听到,隔着玻璃弗利也听的一清二楚。
一种罗德式的拒绝,虽有些不近人情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的确高效,让对方明确知道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的确能节省不少沟通上无谓浪费的时间。
这个叫贝鲁斯的人弗利一眼便认了出来,他从座位上站起,考虑是不是上前打个招呼。可是在办公室这样的举动显然并不合适,毕竟刚才罗德才和贝鲁斯起了冲突,要是这个时候贸然与他说话多少有些自寻烦恼。
弗利端起茶杯沿着一扇扇如沙滩上的贝壳般错落排列的玻璃门走廊往通道走去,贝鲁斯离开时一定会经过那个通道,对方如果认出自己,他可以直接从旁边的小门和他一起离开办公室。
弗利回想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当时自己有些着急,至于原因他也不十分清楚。也许最合适的做法是给贝鲁斯打个电话,约他晚上一起喝杯啤酒,也许叫上一碟烤肉,贝鲁斯最喜欢那些烟味十足的食物。
「嗨,尤金。」
尤金是弗利母亲的名字,贝鲁斯说话声很大,好像周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一样。好在公司没人知道这个名字。
弗利举起左手轻轻在嘴边敲了两下,贝鲁斯心领神会的跟着他从侧门走进通道。通道里只有微弱的黄色灯光。
弗利继续往前走,脚步声一前一后,两人一直走到大楼后一片暂未使用的空地。
「尤金,你怎么在这,好多年不见了。」
贝鲁斯像憋着好几个月没说话似的,一脸兴奋的询问着。
「是啊,你还在做医生吗?」
「早不在了,我想想,三年前吧,我就辞职了。」
「三年前。」
弗利重复道。
「是啊。」
「你在这家公司真是太好了,看来以后我们又有机会合作啦。」
「你刚才就在和我同事谈合作的事,听他的口气好像是拒绝了。」
「是啊,这事情绝对不是坏事。」
眼见贝鲁斯即将滔滔不绝的谈论他和罗德之间的事,弗利立刻打断了他。
「嘿,老兄,我可不想知道我同事和你的事,这样不合适。」
「嗯,也是,多年不见你看我太热情了是不是。哈哈。」
弗利笑了笑不知如何回应。
「你这么偷偷把我带出来做什么。这么久也没联系,见面还这么偷偷摸摸的。」
「你也看见了你说话那么大声,打扰别人工作不好,何况我和你又不谈工作最多只是叙旧而已。」
「说的也是。那么,弗利你现在怎么样,莎梅尔还好吗?她那个有钱的老爸有没有给你脸色看?」
「为什么要给我脸色看?」
「你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难道我猜错了,是你和莎梅尔之间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是工作上有些困扰呢?」
「得了吧,弗利你的才华可是在很多人之上的,应付你们公司这点事你还会这么脸色难堪,说实话,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我很好。」
弗利自觉说了谎一般忐忑不安,明明是自己把贝鲁斯急急忙忙带到这里,却什么也不说,好像怎么都让人觉得可疑,这样猜测下去还不如自己把意图说清楚。可自己的意图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相认非要到这没人的地方,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做出这么不合情理的举动多少得有个说的过去的理由才是。
「能还记得…」
「记得什么?」
「记得原先我公司楼下的咖啡店吗?」
「艾菲娅。我知道了,你偷偷把我带出来是想问艾菲娅的事,难怪你这么好奇我什么时候离开医院的。」
贝鲁斯的反应快的让弗利接受不了,他就好像叶子上的昆虫一样机敏和精准。
「你后来有没有见过她。」
「那个知道你喝咖啡要加糖的女孩?」
「别闹了,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她在我家厨房煮咖啡呢。」
「什么。」
贝鲁斯的回答若不是玩笑弗利真不知道如何回应他,祝福还是打他一顿,为什么会想到动手?他不清楚,只觉听了贝鲁斯的话脑子里嗡嗡作响像飞进一只会唱歌的苍蝇。好在贝鲁斯又立刻表示先前不过是开个玩笑,关于艾菲娅他和弗利一样一无所知。
「怎么突然想到她了,你们什么时候结束的?」贝鲁斯问道。
「结束?」
「对啊,你们不是在恋爱吗?」
来电响起时,他正不知道如何回答贝鲁斯这个问题,这个他自己也从未弄清过的问题。弗利真想告诉贝鲁斯这个他们都认识的女孩这几日每天在干扰他的生活,开车、吃饭,甚至开会写邮件的时候都像拥有他意识的钥匙般说来就来,宣告着自己主人的身份。
但他忍住了,他没有说,工作上的事催着俩人不得不暂时分开,贝鲁斯提议弗利周日去自己家坐坐,弗利答应了。
6
离开何塞办公室已经过去一周。临近周末,弗利想起本该这周回家看望父亲。母亲离世几年来,他忙于家庭和孩子,回父母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父亲又是一个坚强的男人,莎梅尔认为老弗利事实上有些固执,孩子三岁生日那天父亲来过后,再没有一家人聚在一起。
也许等五月以后再回去会好些,西雅图的夏天会让人心情愉悦,而在连绵的雨季,晴天变得异常珍贵,心情也跟着密布乌云。母亲生病后几年,家里就没有放晴过,每次回去看她都是愁眉不展又说不出哪里不愉快,父亲整日坐在门外反复读报纸,这就是家留给弗利最后的印象。
母亲一直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直到病情再也瞒不住家里人。一日早上弗利接到父亲电话,说母亲住院了,医生说越快手术越好。当时弗利并没有惊讶,回到租借的房子中,整理好衣服,赶往机场。下午到家时,父亲已经从医院回来。
「没什么事,我都后悔给你打电话,医生说一个小手术。」
父亲说话的声音比电话里轻松很多,或许医生的话让他安心不少,也或许……后来弗利认为父亲也许并不希望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悲伤,于是轻描淡写的描述了母亲当时的状况。
「医生有没有说什么病?」
「甲状腺肿瘤。」
「那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为什么又说手术越快越好?」
「也许现在床位有空吧,谁知道呢。」
弗利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房间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每天都有人打扫的干干净净,当然一定是母亲才会做这些,从小到大母亲都喜欢把弗利的衣服和房间整理的一尘不染,衣服上撒到一些番茄酱或是书本上粘了橡皮屑,只要让母亲看见了,都免不了一番教训然后立刻换上一件熨烫整齐的衣服。
后来的事情远不如父亲当日描述的那么简单,手术当天的病理报告显示母亲的肿瘤是甲状腺肿瘤中愈后最不理想的类型,简单来说就是甲状腺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