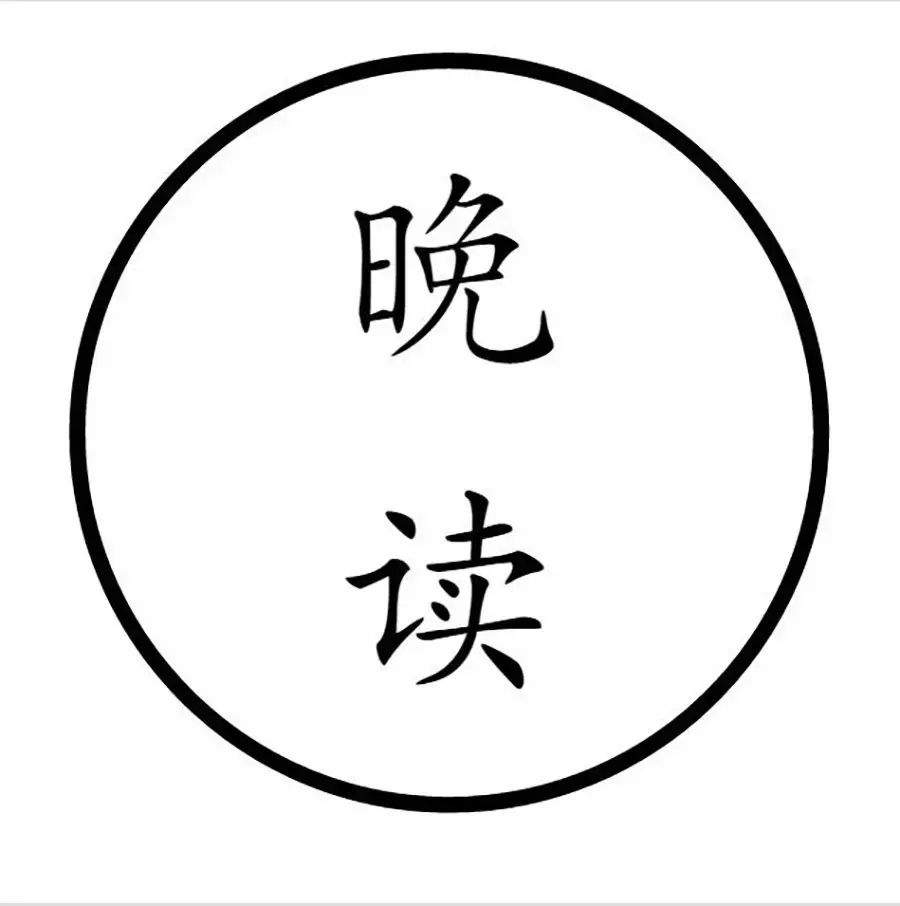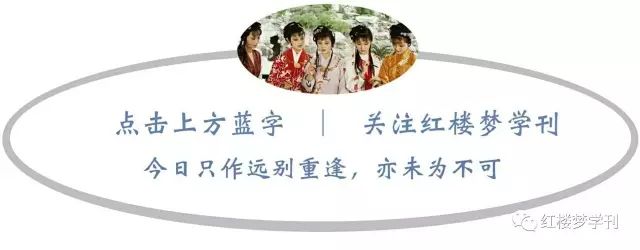

作者:王人恩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中写贾宝玉“曾有几首即事诗,虽不算好,却倒是真情真景”,其第一首《春夜即事》云:
霞绡云幄任铺陈,隔巷蟆更听未真。
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
盈盈烛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
自是小鬟娇懒惯,拥衾不耐笑言频。
对于这首诗的词语和内容,前贤今哲已有多种阐释,为后学解读多所嘉惠。但是,客观地说,诸种解释尚有不妥之处,给人以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之感,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我想从解释“蟆更”一词入手,进而对全诗内容做一解说,兼对张庆善先生的有关观点提出商讨,敬请张先生和其他同志不吝赐教。
(一)释“蟆更”
对此,代表性的解释有两说,《红楼梦大辞典》第539页谓:
蟆更:即虾蟆更。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类“六更鼓”条引《 精隽》:“宋内五鼓绝,梆鼓遍作,谓之虾蟆更。其时禁门开而百官入,所谓六更也。”一说江南夜间击柝曰虾蟆更。《事物纪原》:“夜行击柝代更筹,曰虾蟆更。”《豹隐纪谈》引郝天挺语:“江南以木柝警夜,曰虾蟆更。”又云“内楼更五绝,梆鼓交作,谓之虾蟆更。外方谓之攒点。”
《红楼梦》第322页注③仅引了《七修类稿》一说,未引《红梦大辞典》的又一说。《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九集瞻詹先生《虾蟆更》一文和《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一辑张庆善先生《虾蟆更》一文所引材料与《红楼梦大辞典》基本一样,未能拿出新的材料进行论证。
我不知道上述三家所引《豹隐纪谈》是据何种版本。西北乏书。我翻检《说郛》涵芬楼藏板一百卷本卷七《豹隐纪谈》(一卷),著者署“宋无名氏”,其原文是这样的:“杨成斋诗云:‘天上归来有六更。’盖内楼五更绝,柝鼓变作,谓之虾蟆更,禁门方开,百官随入,所谓六更者也。外方则谓之攒点云。”[1]宛委山堂藏板《说郛》一百二十卷本卷二十于《豹隐纪谈》则署名“宋周遵道”,与百卷本相对照,“柝鼓变作”为“梆鼓交作”,[2]余皆相同。《渊鉴类函》卷四百四十八引作:
宋周遵道《豹隐纪谈》:“杨成斋诗云:‘天上归来有六更。’盖内楼五更绝,梆鼓交作,谓之蟇更,此即六更也。”
[3]
问题已经比较清楚:第一,上述三家所引《豹隐纪谈》之文有小误:或省“云”;或省“所谓六更者也”这一重要语句;尤为不妥的是省去了“天上归来有六更”诗句。第二,新校本作“蟆更”,戚本作“蟇更”,均不误。因为“蟇”同“蟆”。前引《渊鉴类函》引《豹隐纪谈》正作“蟇更”。又《周礼·秋官·蝈氏》:“掌去鼃黽。”《序官》郑注“书或为掌去虾蟇。”白居易《琵琶引》:“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蟇陵下住。”《本草纲目》:“虾蟆一名蟼蟇。”皆是其明证。据此可知有正本作“隔巷暮更”亦误;甲辰本作“隔巷暮声”、程甲本和程乙本作“隔巷蛙声”、郑藏本作“隔岸嚣更”、吴藏本作“蛩墓更深”,皆误。尤其是程本妄改为“蛙声”,实属荒谬。第三,杨万里《诚斋集》卷三十一《谢余处恭送七夕酒果蜜食化生儿》诗:“醉眠管得银河鹊,天上归来打六更。”其自注:“予庚戌考试,殿庐夜漏杀五更之后复打一更,问之鸡人,云:‘宫殿有六更。’”杨万里身经二“庚戌”,其“考试”当为公元1190年(前一庚戌为1130年,时杨仅有四岁),据此可知至迟在南宋时已有“六更”之说。《事物异名录》卷二“虾蟆更”条引《豹隐纪谈》后即注明“六更”。俞樾认为“宋制并无六更”[4],似是而非。要之,“蟆更”即“蛤蟆更”的简称,宋代又称“六更”。
普列汉若夫曾经指出:“在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没有原因就发生的。”[5]那么,为什么“六更”又叫“蛤蟆更”呢?其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阅读古籍时发现了一条材料,对我们研究“虾蟆更”有其重要的价值。清人吴璜《黄琢山房诗集》卷九有《汴京杂咏》五十首,其一云:
金雀亲登展外城,披图宫殿制新成。
西迁雍洛终何用,且打虾蟆鼓六更。
吴诗于每首诗后均有小注,前二句小注因与本题关系不大,姑置不论,其注末二句有如下文字:
《宋史·五行志》:宋以周显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图谶,谓过唐不及汉,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又有谣云:寒在五更头。按,宋自太祖建隆,庚申受禅,至理宗真定元年,历五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盖符。太宗卜世于陈抟睡到五更醒时再来问之说亦合。庚更同音,以此禁中,常打六更,亦谓之虾蟆更。
按:吴璜(1727-1773)字方甸,号鉴南,浙江山阴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与曹雪芹是同时代人。吴诗虽是咏史之作,但据此可知“六更”即“蛤蟆更”一词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仍在沿用、流传,所以曹雪芹在《春夜即事》诗中使用了这一词语。考《宋史·五行志》四载:“宋以周显德七年得天下图谶,谓过唐不及汉,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又有‘寒在五更头’之谣。故宫漏有六更。按汉四百二十余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开庆元年,宋祚过唐十一年,满五庚申之数。至德祐二年正月降附,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见六庚申,如宫漏之数。”
《宋史》虽修得粗疏,但毕竟乃“正史”,其记载不可以为妄言胡语。除前引杨万里诗句“天上归来有六更”外,程大昌(1123-1195)《演繁露》亦载:“禁中钟鼓院,五更已竟,外间通用漏刻方交五更,盖翌日当值宫女,须以未晓前来受事。故候正交五更,则不及事矣。王禹玉词:‘禁鼓六更交早值。’明宫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又考《宋史·律历志》中“攒点”一词屡屡出现,正指天将破晓时分。因此,可以认为至迟在南宋时宫禁中就有打六更之例,“六更”在民间俗语中称作“攒点”;又因为虾蟆于将放亮时叫的最厉害,故称“六更”曰“虾蟆更”。《本草纲目》四十二《虫》四《蝌蚪集解》:“至春水时鸣以聒之,则蝌蚪皆出,谓之‘聒子’”。《五灯会元》载世奇首作甚至将蛙鸣误听为版响。[6]明刘基《听蛙》诗对蛙鸣做过这样的描摹:“初聆衙衙杂更鼓,渐听漕漕成侈哆。犹持坚白较同异,似坐狙丘谈稷下。村童叫噪聋学究,悍妇勃溪喧娣姐。西域胡僧弹般若,齐东老生矜炙(车果)。逸帆独岸靡蒹葭,醉客骂筵投盏斝。……”虾蟆叫声之大,亦可知矣。此其一。宋时之所以将“六更”又称作“虾蟆更”,是由于“得天下图谶”谓“五更”谐音“五庚(申)”的缘故,是考虑到宋朝国祚长短为避凶就吉——“寒在五更头”——而改为“六更”即“虾蟆更”的。曹雪芹乃旷世奇才,博学绝伦,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知。《红楼梦》在诸多地方明显地受到了古代图谶的深刻影响,“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图、诗就与古代图谶大典《推背图》特别相像。甲戌本于元春判词和图画上有一眉批云:“世之好事者,争传《推背图》之说。想前人断不肯煽惑愚迷。即由此说,亦非常人供谈之物。此回悉借其法,为儿女子数运之机,无可以供茶酒之物,亦无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笔!”脂批于此直接点名《红楼梦》“借”《推背图》的形式创作小说,正因此故,清人甚直提出过“《红楼梦》为谶纬之书”之说。[7]曹雪芹用“蟆更”一词入诗,自当对“虾蟆更”的来龙去脉烂熟于心,我们虽然不敢说曹雪芹用“蟆更”也不无暗示图谶之意。此其二。其三,据上可知,《红楼梦》新校注本之注③和瞻詹先生的看法是可取的,虽然二家均未揭明“虾蟆更”的来历;而张庆善先生取《事物纪原》即“前一说”就值得商榷了。
明乎此,我们始可对《春夜即事》的内容做一解说了。

(二)《春夜即事》诗解读
张先生认为,《春夜即事》写的是“春天夜晚的生活情景”,其重在“夜”而不在“晨”这一“时间概念”;否则,“诗题就应改为《春晓即事》更合适”;因此说,“整首诗也确实是春夜即事而不是春晓即事”,如果说诗写的是“天将破晓的时候,何来‘霞绡云幄任铺陈’,倒是该卷铺盖起床了”。
我的粗浅看法是,《春夜即事》写的是一夜未能入眠的贾宝玉在天将破晓时的生活情景和内心感受;时间概念应重在“晨”而不能重在“夜”。兹略述理由如下:
前文对“虾蟆更”的解释已经说明,“隔巷蟆更听未真”实是写天将破晓时隐隐约约听到隔巷传来的嘈杂、急促的虾蟆更的声音,此时的贾宝玉尚未入眠,所以他才能够“听”,这句诗从听觉着笔;而首句“霞绡云幄任铺陈”则是从眼前视觉落墨。为什么“听未真”呢?是因为“隔巷”,这是诗中实有之意。此句的妙处在于是以虾蟆更声的嘈杂来烘托黎明时的寂静,动静相对,彼此映衬,有如《诗·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和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妙;亦即苏轼《宿海会寺》“纟如五更天未明,木鱼呼粥亮且清,不闻人声闻履声”之意。而“红绡云幄任铺陈”者,不过是直道眼前景,“霞绡云幄”是形容被衾帷帐的华丽,“任铺陈”者,空铺陈也,即使再美丽奢华的衾帐,于我难以入眠的宝玉何有哉?“空”摆设、置虚牝而已!此“空”字,亦即杜甫《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之“空”。——“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牡丹亭》名曲正可移笺“任铺陈”句意。此时宝玉的心情或许同张炎《西子妆慢》所写“遥岑寸碧,有谁识朝来清气?自沉吟,甚年光轻掷,繁华如此”的韶华易逝、知音难近的感伤,亦不无鲍照《野鹤赋》所谓“虽物居以成偶,终在我而非群”的众里身单、块然独处的哀愁。二句言情写景,堪称高妙,所以雪芹谓诗“倒是真情真景”。如果认为“天将破晓的时候”就不可能“霞绡云幄任铺陈”,“倒是该卷铺盖起床了”,却有些认虚成实之嫌了。在第四十八回中,雪芹曾借香菱之口说:“据我来看,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确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仔细咀嚼,这番话说得多好呀!
中间二联顺承首联。春雨潇潇,乍暖还寒,绣枕轻凉,有梦也难通!思情如春雨,连绵不断;心绪似春寒,甚感凄凉。宝玉之哀愁、之怨恨、之惆怅、之自责,莫不寄寓其间。随时同居贾府,而相见何啻千里!是否此时彻夜未眠的我在辗转反侧地思她念她,而她也同我一样两地同时相思呢?我是“支颐不语相思坐,料得君心似我心”[8];她是否也同我一样“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9]呢?真正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呀!可谓相去三步,如阻沧海。现实中难以见到她,而黑甜乡里能见一面也好,可眼前景却是“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10]呀!我们用阮瑀《止欲赋》的描写来概括《春夜即事》的主要内容再也恰当不过了:“还伏枕以求寐,庶通梦而交神,神恍惚而难遇,思交错以缤纷,遂终夜而靡见,东方旭以既晨。”[11]雪芹写《春夜即事》与阮瑀《止欲赋》是遥承?是暗合?亦未可知。
尾联似是写宝玉对丫鬟们平素作息习惯、生活特点的评价和设想,并以丫鬟们的“笑言频”来反衬自己此时的孤独哀愁。由于自己终夜未能入睡,所以想在天亮前能进入梦乡,好在梦中与她相见。可是早已睡足睡醒了的丫鬟们已经开始频频笑言了,拥着华衾而卧的宝玉承受不了她们的嬉闹了,这都是平时宝玉对丫鬟们娇惯养成的结果。俗语云:三个女人一台戏。宝玉有好几个丫鬟在侧频频“笑言”,有“戏”上演,宝玉焉能入梦?如果说《诗·齐风·鸡鸣》写的是憎鸡叫旦、断人恩怜,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写的是憎莺啼鸣、惊回春梦的话,那么“自是”二句恰是宝玉憎小丫鬟们频频笑言,阻我不得入春梦而不能与她梦中相见的烦躁情绪。诗含义极为含蓄而丰赡,笔法细密而老辣,隶事用典,了无痕迹。正因此故,才有人“抄录出来各处称颂”,才有人“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哦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倩画求题的”。庚辰本于即事诗上有眉批云:“四诗作尽安富尊荣之贵介公子也。壬午孟夏。”
若上述解说可以成立,则《春夜即事》诗的“时间概念”应重在“晨”而不应重在“夜”之说自可成立,也就没有必要改《春夜即事》为《春晓即事》。因为“夜”与“昼”相对,指从天黑到天亮的一段时间,唐孔颖达疏《左传·庄公七年》即有“夜者,自昏至旦之总名”的解说,更何况诗题标“夜”而不写“夜”的诗词甚多。
诗无达诂。一孔之见,拉杂如上,未知当否?敬请方家赐教。
注释:
[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说郛》三种。
[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说郛》三种。
[3]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8月版影印《渊鉴类函》本。
[4]《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七册《茶香室四钞》卷八。
[5]《论艺术》第104页,三联书店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