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信谁都不会忘记
乔治·奥威尔
经典作品
《动物农场》
中的这句话:
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
有趣的是,最近在翻另一本社科书
《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
的时候,突然觉得,某种程度上,作者
汉斯·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在自己这本阐释“
现实主义与权力现实
”之间关系的作品中,为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个人学识有限程度太低,无法求证奥威尔和汉斯·摩根索之间是否存在任何的学术联系,所以,只能在这里分享两个短篇章,希望您能看出点名堂。大家
周末愉快。
维护道德是善,但“
维护道德”之手段可能就是恶
文
|
汉斯·摩根索
译|
杨吉平
摘自
|
《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
》
之
《科学人的道德盲目》
- 声明:如需
转
载先请私
信联系
-
目标为手段辩护
一种更高明的洞察力认为人们需要承认私人与政治道德之间鸿沟的不可避免,但这个鸿沟可以用一个更高原则来加以辩护。这里和谐不是从实际行为的现实中找到,而是从价值判断中找到。这种和谐通过将有可能不道德的行为视为达至特定目标(ends)的手段(means)而实现,在实现特定目标的过程中手段分享了目标的道德价值。鉴于我们有实现这些目标的道德义务,还因为我们若不使用一些本身不道德的手段就不可能成功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遇到了一个困局:
或是放弃实现道德的目标以避免手段的邪恶;或是做那些可能是邪恶的事以获得目标的善
。我们被告知应该选择后者,因为手段在功能上是附属于目标的,因此它们也是道德的。人们应该选择善的目标,避免恶的目标——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无需顾及所要使用的手段。
目标为那些实现它的手段染上了自己的道德色彩,因此它为一些手段辩护,从自身考虑它也谴责那些实现敌对价值的手段
。
居于其他一切之上的目标被指望为一切手段辩护,只要这些手段是代表作为共同善之储藏室(repository)的国家使用。那些将自我的有限私利作为行动目标的做法不被允许,但是当行为目标是为了促进国家福利和共同善则任何手段都被允许,甚至他有义务使用这些不道德的手段。那些看来会使他成为流氓和罪犯的行为如果是为国家而做就会使他成为英雄和政治家。前文所引作为双重道德表达的加富尔的那句名言在这里可以再次引用。目标为手段辩护,如果仅限于政治领域,它就确实与前文所讨论的双重道德观念相同一,是这种观念的一种特殊表达。
但是事实上,用所服务的目标为那些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行动辩护的趋势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它只是在政治中尤其地显著。人们常说只有正义的战争没有正义的军队,人们也可以同样说只有公正的外交政策没有公正的外交官。伦理与政治之间特殊的不一致以及这种不一致在量的向度上的反常无法逃脱我们的注意,当我们读到下面这则报道时都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回驳阿斯特夫人(Lady Astor)“什么时候停止杀人”的问题时说,“在不再需要的时候”。一位英国记者和斯大林谈到在集体化运动过程中有数百万农民死亡,斯大林用问题作为回应:“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超过了七百五十万,超过七百五十万的人毫无意义地死去了,所以你需要承认我们的损失其实很小,因为你们的战争以混乱收尾,而我们从事了一项惠及整个人类的事业”。
所谓的“资本主义伦理”提供了一个更少惊悚但同样典型的调和行动与伦理的尝试。它们对我们而言更少惊悚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出现在一个和我们的世界迥然不同、在度和量的向度上都超越我们个人经验的世界中,而是作为我们熟悉的日常经验的一部分。新教徒将世俗世界的成功与美德等同,神灵的佑福以这种方式被诠释成预示着那些在成功——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功——之路上所采取的手段分享了成功的伦理尊严。那种认为个人开明自利的自由互动将会产生利益自然和谐(即经济意义上的共同善)的放任自由主义信念赋予个人自利以一种伦理价值,如果个人利己主义不是通过附属于社会和谐这个伦理目标就无法获得这样的伦理价值。个人的伦理生活就是一系列用伦理上有价值的目标为个人利己主义表现辩护的尝试,它试图证明那些看似利己主义的行为实际上超越了个人利益,促进个人利益是迈向实现远超过任何个人利益的更高伦理价值的偶然且不可避免的步骤。
但是,通过上述方式实现伦理标准与人类行动之间的和谐只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它是模糊的而不是确定的。
为了实现这种和谐人们需要在手段的不道德和目标的伦理价值之间权衡,在它们之间建立固定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
。人们或许可从某种特殊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辩护,但他们无法从普世、客观伦理标准的视角来证明目标的善应优先于手段的邪恶,因为根本就没有比较两种幸福或两种不幸,或将一个人的幸福与另一个人的不幸进行比较的客观标准。人们经常议论用一个团体的不幸换取另一个团体的福利的代价过于高昂了或不太高昂,但它从来没有获得证明。对目标—手段关系的捏造、片面特征的分析将有助于阐明这一点。
这种关系在双重意义上是捏造和片面的,一方面,其他团体福利为之牺牲的这个团体的福利,只是对于这个团体的成员和它的辩护者而言才是具有积极伦理价值的目标,另一团体的成员和它的辩护者会将自己的福利看成是应该被促进但事实上被牺牲了的目标。对一个团体而言是目标的东西被另一团体作为手段使用,反之亦是。这样手段—目标关系本身就没有客观性,它取决于观察者的相对社会优势。康德和马克思抨击将人作为实现目标之手段的做法,宣扬每个人都应被视为目标本身这个道德箴言,那些被剥夺者就站在这个诉求一边。然而,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斯宾塞、希特勒,
一类哲学家和政客主张有些人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其他人实现目标的手段,一旦那些被剥夺者升到社会顶层后他们也会支持这个主张,然后再自行决定什么是目标、什么是手段
。
另一方面,目标—手段关系是模糊和相对的还因为当我们观察一系列行动之链中实现某些目标的手段时,手段本身也可以视为目标,如果我们将其置于一条行动之链的终点。相反,我们称为“目标”的东西只是行动之链被认为停在某点上,而实际上行动之链会继续向前超越(beyond)这点,从“超越”这点来看目标将自身转化为手段。因此,所有行动都同时是手段和目标,只是因为我们将行动之链从某处武断地割开才赋予特定行动或是作为手段,或是作为目标的独特特征。
但是事实上,人类行动的总体性(totality)将其自身展现为一系列行动的等级,每个行动是其前面行动的目标,又是接下来行动的手段。这个等级最后汇集于所有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它与绝对善相同一——不管这绝对善是上帝、人类、国家还是个人自己。
绝对善是唯一目标,且仅仅是目标,因此不会充当实现更高目标的手段,从这个终极目标来看所有人类活动都是实现它的手段。
这样,在最后的分析中那种道德目标为不道德手段辩护的教条,导致了对绝对伦理判断的完全否定。因为如果道德目标可以为不道德手段辩护,所有人类活动作为手段希冀实现的目标——最终的、绝对善就可以为一切人类行动辩护。这些行动只有程度的差别,没有性质的差别。“为了上帝的更高荣誉”(ad majorem dei gloriam)所做的任何事也分享了它的最终目标的圣洁性。这样在伦理规范和现实之间建立的和谐确实实现了。但是,问题的解决再次只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因为扰乱人类良心、在人类心灵中提出问题的困境首要地并非关于人类行动与绝对善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行动与有限目标之间的关系。前者被认为是邪恶的,后者被认为是善的
。这样人类急于回答的问题就不是——至少不是在目标—手段讨论的背景下——我们要如何在比照绝对善的情况下解释所有人类行动中显然不可避免的邪恶,而是要解释在实现相对善的一些行动中,尤其在政治行动中存在一些显然是不可避免的邪恶
。
在目标—手段教条中,不同性质行动的道德统一性在表面上实现了,政治行动之道德价值的确立取决于行动所要实现的目标。一种类似的欺骗性和谐与错误的道德辩护来自行动的起源,即行动者的意图。行动的伦理价值不是据其结果来判断,而是根据行动者的意图。如果行动以邪恶收尾,如果它为成千上万的人带去了战争、死亡和痛苦,政治家也不应该受谴责,只要他的意图是好的。鉴于人的意图别无其他,只能是反映在行动者心灵中的行动目标,很显然,求助行动者的意图作为统一和辩护的原则只是在相反方向上重塑了目标—手段论据,它分享了后者的缺陷。
但是,对用行动者的意图为政治行动辩护的做法还有一个特别的批评。法国谚语有云“在政治中比犯罪更糟糕的是笨拙”,换句话说,政治行动者在遵守一般的道德义务之外还有明智地行动这个特殊的道德责任,即据政治艺术的规则而行动,对他而言权宜成了一种道德义务。
那些只代表自己行动的个人可能会不明智地行动而不受指责,只要这种不顾权宜的行动的后果只涉及他自己
。政治领域中行动本质上关涉那些必然要承受不明智行动后果的人,那些怀着好意行动却不明智并因此带来灾难后果的人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因为他违反了所有影响他人因此首要地是政治行动所需服从的责任伦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y)。求助善意作为统一与辩护的原则模糊了政治行动的社会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以某种方式干扰了他人的生活,而私人行动一般而言不会干扰他人生活。
那些政治业余者的良好意图可能比职业政治家的不良意图产生更多的邪恶,检验意图是否良好的做法将会摧毁而不是澄清相应行动的伦理意义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说道:“
我尽最大的努力,知道最多能做到什么,我准备一直这样做直到最终。如果结果证明我正确,所有曾经对我的反对什么都不是。如果结果证明我错了,十个天使发誓说我正确也于事无补。
”
自私与权力欲
不管人们做了或试图做任何事来解放自己,他都会再次指涉(refer)自己。一方面,行动者个人出现在所有意图的、完成的行动中。另一方面,所有行动都会对他者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当所欲或所为的行动指涉他人时——大多数行动都属于此类行动——就对他人产生积极影响,即使当行动没有积极指涉他人时,正是缺乏指涉这一点也将行动与他人联系起来。因为社会向个人行动所做的道德要求从来没有完全被满足,一个没有指涉他人的行动,至少从他人的视角看来是对道德义务的剥夺和侵犯,因此带有消极的道德意义。
如果说通过个人行动自我与他人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道德冲突同样也不可避免。个人有无私的道德义务,即不要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他人的利益,但是仅是
贫穷
一项给我们无私的道德义务施加的压力就如此之大,以致那些只是略微接近无私的努力也必然会导致个人牺牲,因此将会破坏他向世界的压倒性要求贡献至少一定份额的无私的能力。这样试图实现无私伦理(ethics of unselfishness)的要求就会导致道德义务的困境:
人们需要自私才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无私的道德义务
。因此,所欲或所为的无私行动(如善)从来都不是完全善的(即完全的无私),因为它永远无法完全超越导致其自身存在的自私的有限性。马丁·路德说:“强烈的邪欲(concupiscence)是不可战胜的。”甚至那些通过自我牺牲或只是不再缺乏自我牺牲而实现的接近完全良善的行动也悖论式地分享了邪恶。
一旦无私伦理的逻辑给自私盖上了认可的印章,所有同样合法的个人利己主义就会相互冲突,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的战争就上演了。一个人的利己主义必然与另一个人的利己主义相冲突有两个理由。一个人想要的东西他人已经拥有了,或者他人也想要,冲突和竞争因此产生。当人们发现他和同胞的关系中包含了至少是利益冲突的胚芽,他们就不会再寻求那种几近祛尽自私和避免对他人产生伴生危害的良善意图,他们仅希望良心会为邪恶的趋向施加限制。
不能指望人是良善的,需要满足于他不是太邪恶
。
冲突与伴生邪恶的另一来源是权力欲(animus dominandi),
权力欲表现为与他人相比维持、增加或展示支配范围的欲望。不管人们如何掩饰权力关系,它的最终本质和目标都在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众多特殊指涉之一中
。权力欲寄于与他人维持某种关系的行动者身上,它与我们前述的自私紧密相关,虽然未与它同一。因为自私的典型目标是食物、庇护、安全以及获得它们的手段,如钱、工作和婚姻此类的东西,它们与个人的重要需求有着客观关系,获得这些东西将为生活在特定自然与社会条件下的个人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
另一方面,权力欲关注的不是个人生存而是生存获得保证之后个人在同胞中的地位,因此
个人的自私有限,而他的权力欲无限
。人的重要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但只有当最后一个人成为他支配对象的时候——即没有人在他之上或在他之旁,好似他就是上帝,人的权力欲才能满足。亚里士多德说:“事实上最大的罪孽是由过度而不是必需所导致,人无须因为仅想避免酷寒而成为暴君。”当彼得·拉迪松(Peter Radisson)遭遇到苏必略湖区对其惊恐和羡慕的印第安人时,他感受到了不受挑战和无可挑战之权力的愉悦:“我们是恺撒,没有人可以反对我们,我们出行时无须带任何重负,这些可怜、悲惨的人认为替我们搬行李是件幸福的事。”另一方面,塞西尔·罗得斯体会到了权力欲的无限以及使这种权力欲得到满足之不可能的自然限制,“夜里头顶上的繁星是我们永远无法触及的世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瓜分这个星球——我经常这样想,但是看到这些繁星如此清晰却又如此遥远使我感到忧伤。”
在自私中存在着理性的因素,它表现为目标的自然限制,但这种理性因素在权力意志中却匮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仅仅是自私的要求可以被让步所安抚,但是一个要求的满足总会刺激权力意志无限扩张的诉求。
这种权力欲的无限特征反映了人类心灵的一般特征。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提到这个特征时写道:“迷失的心灵哭诉道‘再多点,再多点’,只有全部才能满足人。”只有在穷尽它所有可能的对象之后这个无限和永无止境的欲望才会平息。权力欲和与宇宙相统一的神秘欲望、唐璜的爱、浮士德对知识的渴望同属一种类型。这四种尝试都试图将个人推出他的自然限制之外朝向一个超越性目标,一个栖息点,它们只能在想象中而不能在现实中实现。那些在现实经验中试图实现它的人总会招致自身的毁灭,就像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希特勒的所有世界征服者的命运所证明的那样,伊卡洛斯(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中人物,其父代达罗斯因谋杀外甥被流放至克里特岛,后借助于用蜡粘连的羽翅逃离克里特岛,伊卡洛斯与其父一起逃离,但因为飞得过高,蜡融化导致羽翅解体而摔死。后世以此故事喻示不要得意忘形,追求过高的目标。译者)的传说、唐璜和浮士德的命运也象征性地描绘出了这点。
通过以这种方式一方面将权力欲与自私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将其与其他超越性欲求分离开来,人们已然曲解了权力欲的真实性质。任何时候当一个人试图做出会涉及他人的行动时权力欲就会出现,人们或许可以在概念上将其与社会行动的其他要素分离开来,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行动自身不至少包含着使自己胜过他人的欲望的痕迹。除了其他特殊类型的自私和邪恶目的之外,
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权力欲构成了人类行动中邪恶的独一无二性
。这种腐败与罪恶的因素注入那些甚至是最良善的意图中,也许只是一小滴的邪恶,但仍能糟蹋这些最良善的意图。
在更大范围内,将教会变成政治组织、将革命变成独裁统治、将爱国变成帝国主义都是此类例子
。
从政治的本质和目标是支配他人的权力的意义来看,政治是邪恶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将人贬为他人实现目标的手段。由此可看出权力导致腐败的原型就在政治领域中。因为在此处权力欲不仅与一种性质不同的支配目标相混合,而且是意图中最本质的东西,是行动的生命力,是政治作为一个独特人类活动领域的构成原则。政治就是对支配他人权力的争夺,不管人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权力是最直接的目标,获取、维持和展示权力的模式决定了政治行动的技巧。
腐蚀政治行动的邪恶与腐蚀所有行动的邪恶相同,但是政治行动的腐败确实是所有可能腐败的范式和原型。私人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无辜的,一个是有罪的;一个是道德的,一个是不道德的;一个是善的,一个是邪恶的;这两类行动的区别唯独在于它们偏离伦理规范的程度。这种区别也根本不具有规范特征,如果像双重标准学派所做的那样对它们区别看待会将人的道德义务与参照这些道德义务的人的实际行为相混淆。我们不能期望从一个人在政治中的行为有别于他的私人行为这个事实中得出结论,说他在不同行动领域承认不同的道德观念。并不是有一种伦理观念适于政治行动,另一种伦理观念适于私人领域,这两个领域适用同一种伦理标准,但是,从观察到的和可观察的经验来看这同一观念在两个领域中得到遵守的程度不同。
在政治领域中伦理标准不仅在经验上遭到特别程度的违反,而且一个行动如果想同时遵守政治艺术的规则(如实现政治成功)和伦理规则(如行动本身应该是善的)就根本难以做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上述情况时政治行动与作恶不可避免地相联系这一点才会变得非常明显。对政治成功的检验是要看人们在何种程度上维持、增加和显示对他人的权力,对一个行动道德良善与否的检验,要看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将他人看作目标本身而不是实现行动者目标的手段。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非政治(nonpolitical)的行动永远暴露在被自私和权力欲腐蚀的危险中,这种腐蚀内在于政治行动的本性中。
我们这个时代中只有那些最伟大的异见者才清醒地意识到政治行动不可避免的邪恶。那些在自由时代写作的杰出非自由思想家会与阿克顿(Acton)爵士一起发现,“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或者他们会和雅各布·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一起看到政治中的“绝对邪恶”;又或者他们会同意爱默生的话,他认为武力是“实用的谎言”,“每个现实的国家都是腐败的”。
(完)
相关图
书推
荐

《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
(大学译丛)
[美] 汉斯·摩根索
|著
杨吉平
|
译
《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是摩根索流亡美国(1937)后发表的第一本英文学术著作, “这本书确立了现实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但是,这本书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长期以来,两种情绪决定了我们文明对待现代社会的态度:对以现代科学为代表的理性力量会解决我们时代所有社会问题的信心;对科学理性解决社会问题一再失败的绝望。《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作为阐述政治现实主义的重要奠基性作品,展现出为什么对科学救赎力量的信仰是错置的,指出这种信仰是如何在政治和哲学思维中兴起的,它是如何表现自己的,最后指明哪些人的智识和道德官能独自导致了社会世界的诸多问题。
点击文末
阅读原文
可购买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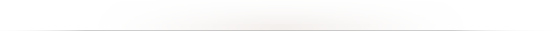
上
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
stphbooks
”添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