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什科·克拉涅茨(
Misko Kranjac
,
1908-1983
)是斯洛文尼亚当代知名小说家。
1938
年加入共产党,
1944
年参加游击队。战后历任出版社社长、斯洛文尼亚作家协会主席和议员。他是斯洛文尼亚科学艺术院院士。
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位长期在外毫无家庭责任感的父亲,兴致所至,突然回家看望子女的一言一行和孩子们的所思所想,反衬出一位含辛茹苦独自担当起抚养子女义务的可爱母亲的形象。故事虽然简单,文笔也朴素,但却揭示了为人父母者应如何尽养育子女义务的主题。
米什科·克拉涅茨作 高韧译
孩子们归我们父母所有,这毋庸置疑。孩子们甚至在我们的出生簿里都登记注册了的,就像房屋、菜园、林地都由我们编目登记在册一样。国家和社会也都把孩子视为己有。此外,教父、教母、亲属甚至街坊邻居对他们也享有某种权利。教会往往也对他们要求享受所有权。不过,糟糕的是这些所有权的界定不大清楚,因此便同某些义务混淆不清。有些父母正是由于这些义务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利;有些父母则抱着不小的欲望想利用所有权为个人私利服务,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权利是一种深厚感情的体现,可容许他们最为严厉地对待子女们,所以,父亲们的表现绝不好于母亲们,而且正好相反。
于是有一天叶利舍维茨忽然想起了叫做孩子的这份私有财产。为什么恰恰在这一天想起来了,也许那些自以为懂心理学的作者们能够解释明白吧。或许是因为他这个打短工的人那天腰包里有了钱,这才想起回家去看看老婆;或许是因为他想家思念孩子。不管怎样,只要他一想起老婆,他立刻就会想到孩子,于是他便想象着老婆和岳母会如何把他赶出家门,这时他就对自己说:“我回去告诉他们,孩子也是我的!出生簿上白纸黑字这么写的!”那天叶利舍维茨挣到了一些钱,所以从一大清早他就去了灯红酒绿的地方。
午后,他想起了老婆,并且心里还想拿孩子来威胁她。随后他也不无父亲自豪感地想到了几个孩子:“孩子本来就是我的嘛。从他们的鼻子就能看得出来。我去看看他们,可怜的孩子,简直就跟弃儿没什么两样!”似乎在他心目中倒也确实对自己的五个孩子真的微微动了点儿爱心。
他心软下来的时候甚至打算给他们带回点儿小礼物,比如小衣服什么的,他们肯定非常需要,这样做不但很好,甚至大有益处。可是他喝完了酒,付完了账以后却改变了主意,又打算买些巧克力和其他糖果了。“孩子们看到这个也会高兴的,通常甚至比衣服更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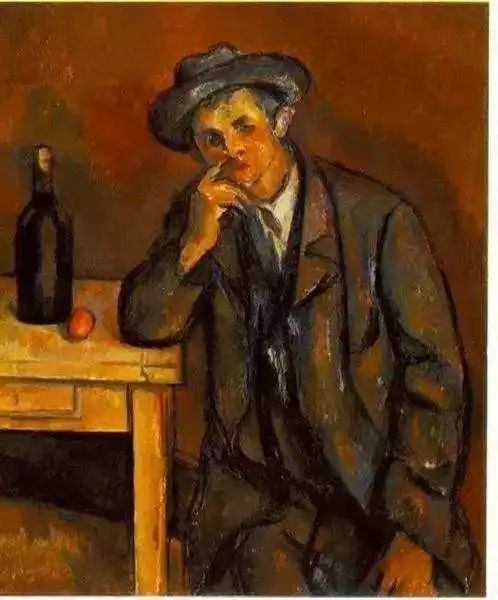
他又喝了三杯酒,先是忘了巧克力,接下去又忘了其他糖果,只剩下气势汹汹的心情没忘。他就怀着这种心情动身返回大山沟里的家,好去责骂老婆,而岳母嘛,“就干脆把她赶出家门”。
时值秋季,叶利舍维茨的五个孩子正在果园里爬树嬉戏,真不亚于那些左邻右舍果园里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的松鸦。这些果园从山顶顺着相当陡峭的山坡一直延伸到深谷。叶利舍维茨家的房子就在这个深谷里。孩子们像松鸦似的大吃梨子,梨汁顺着他们的下巴颏直往下流,满脸脏兮兮的,身上的破衣服有的大有的小。
这几个大头娃娃一瞧见几乎两个月没回家的父亲就安静了下来,但还是像一群松鸦。只不过那些松鸦一见有危险就跑了,而这五个小叶利舍维茨却没地方藏没地方躲,四个大孩子到底还是像群蜥蜴窜进了右侧与果园和房屋紧紧相连的灌木丛里。就只剩下刚一岁半的小五还坐在草地上。他穿了件后开襟小褂,用带子系在脖子上,光着脊背,露出小肚子,赤着小脚丫,惶恐地瞪着他不大认识的父亲,嘴里倒还继续啃着梨,尽管这时他更想嚎啕大哭。
他没有哭,却仍然啃着梨,梨汁从他两边嘴角顺着黏乎乎的下颏往下流淌。在他那件刚能遮住小肚脐的小褂上留下了一道又黏又脏的痕迹,就像泛滥的小溪在草地上留下一条淤泥。他的褐色长发都竖在他的大脑袋上。
叶利舍维茨心中一时间竟漾起了类似人类暖融融的感情波澜。这种感情也许会促使他认识自己的过失,并燃起父亲和温情的火花,哪怕是瞬间的认识也好,于是他的手伸进裤兜里掏出一条又脏又皱的手帕,寻找手帕最净的一角,给孩子擦了擦嘴巴。
“万契克,我是你爸爸。”
他幸而算是想起了孩子叫什么名字。他心中的感情非常复杂混乱,就好像一个人把库房货架上的瓶子、箱子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放乱了一样。他甚至想起自己曾经打算给孩子们买些小礼物的。但他在兜里胡乱地摸了一阵,只找到几支德拉瓦牌香烟,其中一支他还吸过了几口。他掏兜主要是由于惊慌失措这种不愉快的感觉罢了。
“涅特卡!”他叫大女儿。她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但还得照看弟弟妹妹,这就是说,她也应该比其他孩子更听他的话。“你们都躲到哪儿去啦?你们马上到这儿来,你们的父亲回来了!怎么,你们不认识我啦?”
孩子们都认识父亲,但是他们总是觉得跟他见面非常难受,因为他每次回家都跟妈妈和外婆吵嘴,有时甚至会闹到外婆干脆把他从“自己破窝里”赶出去,要不然就动手打起来。说实话,在这样大吵大闹的时候,他连摸都不摸一下孩子,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何况他也看不见他们,因为他们早就赶紧躲藏起来了:涅特卡把他们集合起来,夏天她就跟他们一起躲在灌木丛中,冬天就藏在雷斯卡那边的畜栏里,那儿比较暖和。
这时涅特卡在思索、在考虑。妈妈不在家,而爸爸肯定是为妈妈才回来的。外婆也不在家,她在家就会把他们从父亲手中救出去。不,不必大喊大叫,应当把小家伙集合起来,上山回村里去,等待爸爸离开或者妈妈和外婆回来。可是果园里却只剩下万契克一个人独自面对父亲,涅特卡总不能扔下他一走了事。
“走吧,”涅特卡说着就钻出了树丛。她身后跟着钻出来三个大头娃娃。眨眼工夫他们几个就在树丛前边排成一行,好像一架梯子似的,梯子一级比一级高过小孩的一巴掌,每个孩子都是浅色硬头发,男孩头发耷拉在前额上,快遮住眼睛了,而涅特卡的长发披到两肩和背上,一缕缕垂到两边耳际。
“到这儿来,”父亲说。
涅特卡略显迟疑,瞧也不瞧自己的几个弟弟就说:
“我们走吧。”
她走在前面,“三级梯”跟在她后边,一个比一个矮一巴掌。他们一直走到待涅特卡在万契克面前停下来把他抱起来才站住。其余三个孩子没等命令就列成一排,与她并肩面向父亲。
老实说,叶利舍维茨心中想的全是别的事。
“妈妈在哪儿?”
“她不在家,”涅特卡回答。
“那外婆呢?”
“也不在家。”
全都乱了。
“我们进屋去吧,”父亲说。“你们有什么吃的吗?”
“有牛奶。”
“再没别的啦?有面包吗?”
他惶惶不安地在桌旁坐了下来。桌上摆着涅特卡的课本。他伸手拿起识字课本翻开看了看字母,可是他根本不认识这些字母。
“把牛奶拿来。你们都坐在凳子上。”
他本想把话说得缓和些,但没做到。
涅特卡把万契克放在炉旁的一张凳子上,其他几个孩子按个儿高矮依次挨着小五坐下,一个比一个高一巴掌。
“你们过得怎么样?”
最大的一个开始抠鼻子,其他几个小的也跟着哥哥抠起了各自的鼻子,就只有万契克没抠,而是慢悠悠地摇晃着身子。
“我问你们过得怎么样?米海茨,你怎么不会说话呀?”他依然想表现得友善些。“你们应当说:我们过得好,或者说:我们过得不好……”
米海茨把手指从鼻子里抽出来刚好可以回答:
“我们过得好,或者过得不好。”
父亲不知该怎么说明白,但还是嘟哝说:
“笨蛋,你应当或是这么说,或是那么说。”
“涅特卡说吧,”男孩呐呐地说。“她更清楚我们过得怎么样。”
他说完又把手指伸进了鼻子。若是以往父亲早就生气了,而这回只是双颊动了动,就像嘴里咀嚼一块带筋的肉怎么也咽不下去,或者气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幸亏他头脑里不知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他才没有光火,而是瞧着孩子们垂到眼睛上像稻草一样的头发,问道:
“你们最后一次去理发店是什么时候?”
“三级梯”互相对视了一眼。小五蹲着,依然晃动着身子。涅特卡给父亲端来一杯牛奶。孩子们不懂得什么是理发店,每年村里托奈大叔给他们理两次头发,一次是春天气候变暖的时候,另一次是八月外婆带他们去做祈祷的时候。
涅特卡把牛奶放在桌上父亲的面前。
“没有面包。”她又说道。“可是我们家的梨特别好吃,不知道您是不是要吃。”
“你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理发店的呢?”父亲问涅特卡。见她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就解释说:
“你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剪的头发?”
涅特卡想了想回答说:
“夏天。”
“给我找一把剪子来,”父亲吩咐说。
他喝完了牛奶,涅特卡取来了一把剪刀给他。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掏出自己那把梳齿已经稀疏的梳子,端起一把椅子,手拿着剪刀说:
“我们到外边院子里去。”
说完又对涅特卡说:
“你给自己找条带子,黑色的或者别的颜色的都行。”
“我们家没有带子。”
涅特卡长这么大了,家里有什么没什么她全都清楚。涅特卡搜遍整座房子总算找出了一块布条。她本来也是宁愿在父亲这位外人面前掩饰而不是暴露自家的穷困。
“走吧,”父亲手拎一把椅子又说道。
涅特卡抱起了最小的“一级阶梯”,另外三个按个子高矮排着队跟在她后面。她心里明白她不能不听从父亲的话,妈妈和外婆都不在家,是没人来维护他们的。
“你坐在椅子上,”父亲吩咐涅特卡说。
涅特卡嘴唇直打哆嗦,两眼乱眨巴,但她还是坐了下来。几个“阶梯”都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眼前进行的一切。父亲先翻了翻涅特卡的头发,就气呼呼地梳了几下她的长发,最后在头顶上束起,然后扎了起来。
几个男孩子开口说话了。
“涅特卡有尾巴了!涅特卡有尾巴了!”
看起来他们好像在取笑她,可是父亲心里突然希望孩子们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笑起来就行。但他嘴上说出来的话却很严厉:
“你们瞎笑什么!现在城里小姑娘都这样。”
“村里的马才有这样的尾巴呢!”年龄大点儿的尼科说。“我们家的雷斯卡也差不多长个这样的尾巴。”
“笨蛋!”父亲骂道。“你最好用木碗或脸盆端点儿水来。什么尾巴呀,马呀,也许是这样,不过现在城里小姑娘全都梳这种发型。为什么涅特卡不能梳呢?”
尼科立刻就把水端来了,因为很想看看父亲到底还怎么折腾涅特卡的头发。父亲一只手伸进水盆里蘸一蘸,把女儿一缕头发润湿,往前额一梳,齐刷刷地一剪子剪了下来,像是短短的头发帘儿。这时,男孩们望着变了模样的涅特卡已经不笑了:她头上这个尾巴似乎还算适合她,可是她额头的额发却使她叫人认不出来了。
“现在该你啦,”父亲对尼科说,并且把他放在椅子上。这孩子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长头发已经从头上掉落下来了,只有前额剩下一缕额发。父亲几剪子就剪完了,把这个“小阶梯”的头发剪得一磴一磴的。这他自己也看出来了,但这主要是他理发技术不大高明。
他就这样一个挨一个地都给剪了,还剪得全都一个模样:每个孩子的头上全是一磴一磴的,而且额前都有额发。剪完了头发,他们又按个子高矮列队,只有脑袋后边长了尾巴的涅特卡抱着万契克站在一旁。父亲站在孩子们前边满意地环视着他们说:
“嗯,妈的,这回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她根本就不关心你们!”这话他是指外婆说的。“孩子们本来可以非常好的。可是总不能事事都有工夫亲自来搞呀,真该死。”
叶利舍维茨真的认为情况确实如此。他偶或怀着种种爱心同自己的子女过上半小时,不禁唤起他心中万种思绪,甚至还想到了这些孩子.他的私有财产,总会从他身上看到一些长处。
当他剪完了头发,孩子们完全改变了模样,而且他觉得他们真是可爱迷人极了,接下去还该怎么办他就不知道了。他说:
“现在我们走吧……我们去遛达一会儿。”

糟糕的是妻子和岳母都不在家,否则他们早就对骂起来了,至少也得互相责备。现在叶利舍维茨却没有任何借口张嘴骂人了,所以总得想办法填充一下因妻子和岳母这么长时间不在而造成的空白。他独自一个人能拿他们怎么办呢?他的“财产”与他完全格格不入,嘴上承认他们是他的孩子,这很容易,可就在这半小时工夫他们马上就已经成了他的沉重负担,因为他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
“那么,我们走吧……去遛遛,”他又说了一句。也就只能这么办了,不然他只好离开,因为坐等他又不会。
孩子们一听都愣住了,就单单出去遛弯他们从前还没有过呐,他们也许去过一些地方,比如春天去采樱桃、欧洲越桔一类的野果;夏天采蘑菇;秋天采蘑菇和栗子。可是事情就是这样,他们还从来没单独去过什么地方采摘什么呢。连爸爸带他们去什么地方,这事从来没有过。所以他们都犹疑不决地你看看我,我瞧瞧你,直到三个小家伙醒过神来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才不再盯着涅特卡。
“我们去小馆子喝甜汽水,”父亲突然格外大方起来。“再吃点儿什么。”
“快到晚上了,”涅特卡忽然说道。“雷斯卡和鸡都该喂了。”
“那我们现在就喂吧。奶牛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晚上,什么时候不是。”
涅特卡反对也没用。她只得去给奶牛饮水。她父亲帮她干,又去给鸡撒些饲料,然后又给几个小家伙洗了洗脸,可是却没有什么衣服可换。
父亲望着他们身上穿的破衣服,脸色一沉,说:
“你们就没有稍微好点儿的衣服?”
涅特卡脸上泛起了红晕。
“见鬼,国家不是给孩子们发了点儿钱吗,她都给弄哪儿去了?”
涅特卡明白父亲所说的“她”是说她妈妈。她也知道妈妈在工厂领一份非熟练工的工资,还领五个孩子的补贴,可是每当妈妈和外婆当着他们几个孩子的面,数完这两份钱又把这点儿钱放在桌上时,她俩沮丧地意识到根本没有多少钱可以给孩子们购置衣服。
“国家也来这一套!”父亲在埋怨国家。“希望尽量多生孩子,可是却不关心他们。哼,穷人得给国家培养士兵和工人。”
孩子们对任何事都无从表示反对,更何况对这类说法呢。对这类问题他们暂时还用不着去考虑。然而父亲所说的这些,他们又仿佛觉得没什么道理。母亲和外婆总是反驳他所说的话,而且母亲每一回都说:
“你这么瞎说也不害臊,何况在孩子们面前说。”
他丝毫不感到害臊。他一向坚持自己说的绝对是实话,并且一旦有谁敢说他不关心自己的孩子,他准会跟谁打架。
“喂,孩子们,我们走吧。她可是哪儿也不会领你们去的!她哪能领你们去呀!”
他这话仍然还是指他妻子说的。
他们出发了。他们先沿着林中小径走向大路。待上了大路,穿过村庄,就直奔小馆子而去。在林间小径时,叶利舍维茨抱着万契克走在前头,等一上了路面宽、汽车来来往往的大路时,他便叫孩子们走在前边了。孩子们按个子高矮排列着鱼贯而行。他望着他们剪过的一磴一磴的小脑袋和涅特卡头上束着的“马尾巴”,心里觉得非常得意。
“现在你们总算像个人样了!”
他还格外嘱咐涅特卡说:
“你要一直留这种发式,听见没有?虽说我们住在农村,地方偏僻,而人也应该跟城里人那样打扮。社会主义是为所有人的。”
在小馆子里,他们宽松地围坐在一张距房门不远的餐桌前,因为他们觉得此处比较舒适。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父亲自己随随便便地坐下了,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小馆子里他都觉得很随便。而孩子们则紧靠墙边的一条长凳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怯生生地一会儿望望父亲,一会儿又瞅瞅小馆子里的顾客。
“喂,伊万卡,”叶利舍维茨主人翁似的吩咐说,“你有什么最好吃的东西都端上来吧!我要葡萄酒,给他们甜汽水,孩子们,你们想喝甜汽水吗?”
孩子们都瞧着涅特卡。
“嘿,你们就说:我们要甜汽水。”
于是涅特卡说:
“我们要甜汽水!”
其他三个孩子也学着她说:
“我们要甜汽水!”
“五瓶甜汽水,半升葡萄酒!”叶利舍维茨吩咐说。“可是我们吃什么呢,孩子们?”
孩子们又是盯着涅特卡。“阶梯”全都面向她。他们在家吃过栗子又喝过牛奶。有时为了变换花样,餐桌上也会摆几个土豆,有时还做碗汤,或者是面疙瘩汤,或者芥末疙瘩汤,甚至有时还会端上玉米粥。还不止这些呢,一年能吃两次烤肉卷,一次是樱桃肉卷,一次是桔子肉卷,另外还能吃两回核桃仁甜馅饼。过了星期天以后,妈妈还会从骨头上剔点儿肉下来,所以,除了骨头汤而外,每人还能分到一小块肉。这时,孩子们怎么会知道在小馆子里能够吃什么呢?于是涅特卡就说:
“牛奶和栗子。”
接着“三阶梯”也附和她说:
“牛奶和粟子。”
伊万卡微微一笑,说道:
“有家制香肠和熏肠。还有午餐烤肉,要么吃这个?”
“要烤肉吧!”叶利舍维茨吩咐说。“不然的话,这些可怜的孩子什么好东西都没见过!她不会让他们得到快乐!”他进完转身面对孩子们:“我们吃烤肉吧,孩子们,好吗?”
几个“阶梯”又瞧着涅特卡,于是她便说:
“烤肉吧。”
外面天色已晚。在昏暗的角落里只能影影绰绰看见桌边几个白花花的小脑袋,像是桌上并排放着五个南瓜,在每个南瓜面前各摆着伊万卡端来的一瓶甜汽水,只有叶利舍维茨面前是一杯装的半升酒。惟有叶利舍维茨一个人很显眼,好像他正坐在一畦南瓜前边。
“三份烤肉!”父亲吩咐说。
烤肉端上了餐桌,随着又送来了刀叉。父亲以意味深长的神态把烤肉切成小块,几个小脑袋瓜两眼圆睁地盯着令人垂涎欲滴的几小块牛肉,他们眼睛同时也盯着筐里的面包。父亲把牛肉分装六只小盘里,再把盘子和叉子一起移到几个“南瓜”面前,又给每人分了一块面包。
“吃吧,孩子们,你们都饿了!”
他们吃了烤肉,喝了甜汽水,而父亲喝了葡萄酒,他很贪杯,又要了半升酒,后来在动身回家之前又喝了两杯。酒后他情绪极佳,心中充满了自尊体面的感觉。
“喂,孩子们,你们高兴吗?”
孩子们都很高兴,当涅特卡说了句“高兴”之后,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很高兴,爸爸。”
“就是嘛。谁会傻等着喝牛奶吃栗子呀!有时饭桌上也得添点儿别的。那么,孩子们,现在你们说;你们妈妈什么时候给你们吃过烤肉?”
烤肉他们没吃过,只是每年妈妈生日那天杀一只鸡,那天他们才能饱餐一顿鸡肉,小馆子他们从没来过,妈妈从来没带他们来过!不过,涅特卡明白这事妈妈没错。其实这事谁也没错。他们贫穷,而穷人总难免这样。所以这时涅特卡很难回答父亲的问话。真是的,这事何必要提到妈妈呢?
“嘿。你们怕什么?”他鼓动说。“涅特卡,妈妈过去给你们买过烤肉吗?”
“没有,”涅特卡不大乐意地承认说。她觉得这跟妈妈和小馆子都毫无关系。可是父亲却喜不自禁,眉开眼笑。这是他的胜利日,虽说他自己并不清楚这胜利有何意义,因为明天生活仍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而他也将会连买一杯酒的钱也剩不下了。当然,只要想想这个……然而叶利舍维茨却毫无顾忌地大手大脚,更何况是在自己孩子身上呢!
“他们的头发给剪成什么样啦!”伊万卡打开电灯后说,“这准是您自己给剪的吧?”
“鬼知道他们原来像什么!这回总算像个人样!”叶利舍维茨夸口说。“喂,涅特卡,到前边来,让伊万卡看看!现在城市小姑娘都梳这种发式。那么,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能梳呢?”
叶利舍维茨说完又回过头重提他原来的话茬:
“怎么样,孩子们,吃饱了吗?”
孩子们瞧瞧他,又看看伊万卡。
“喂,涅特卡,你说,你们都吃饱了吧!”父亲问。
“是的,饱了,”涅特卡懂得自己别无选择,才无奈地回答说。
“喂,孩子们,你们呢?”父亲环视其他几个孩子。
“阶梯”都齐声说:
“饱了,饱了,爸爸。”
“不想再喝了?”
“不想了,爸爸,”他们回答。
“那么,我们回家吧?”这时涅特卡问道,孩子们又跟着重复说:
“回家吧,爸爸。天快黑了。”
“回家,回家,当然回家!”叶利舍维茨回答。“不过你们得再说一遍,让伊万卡知道到底是谁关心你们。”
涅特卡本来就知道关心他们的是妈妈和外婆,可是反复说“我们回家吧”却不管用,她才只得说:
“爸爸,是您呗,”她溜了一眼伊万卡,脸红了。
“那么,孩子们,你们学着涅特卡说吧!”
于是“阶梯”学着说:
“爸爸,是您。”
“对啰,”叶利舍维茨醉醺醺地点着头,“让大家都了解实情,总不能让人们都以为什么事都靠她一个人,而我却什么都不管,这回孩子们说了实话,小孩子是不会说瞎话的!”
但是光这样叶利舍维茨还不太满意,所以他又问道:
“那么,孩子们,现在你们再说说你们是谁的孩子。”
涅特卡又溜了一眼伊万卡,脸又涨得通红。她小声说:
“我们回家吧。”
孩子们又跟着说:
“我们回家吧。”
“你们得先说说你们是谁的孩子。”
“您的孩子,爸爸。”
接着三个小家伙也跟着说:
“我们是您的孩子,爸爸。”
“对啦,你们是我的孩子。伊万卡,你要知道,他们是我的孩子。你对什么人都可以这么说。你瞧瞧这群孩子吧!是我在关心他们,他们什么事我都管,我一个人管,噢,孩子们,孩子们……”
叶利舍维茨和他的孩子们离村往家走的时候,夜色已笼罩了山谷,唯有山下的城市万家灯火通明。父亲唱着歌,不时停下来高声问道:
“喂,你们是谁的孩子?”
孩子们排成了“梯形”队列在前边行进,打头的是涅特卡和趴在她肚子上的万契克,他两只小手抱着姐姐,像两个人长在了一起。其他三个小家伙跟在她后头。他们的父亲距他们有几步远,嘴里边唱着,脚下踉跄地走着。他忽而咕咚一声摔倒在路上,忽而滚下山坡,然后手抓树干,再靠孩子们的帮助,笨手笨脚地爬上平坦的地方。即便如此,只要他住口不唱歌,他仍然不停地反复问那句话:
“喂,你们是谁的孩子?孩子们,是谁关心你们?”
由于孩子们这回已经不再回答他的问题,他便自问自答:
“你们是我的孩子,是我这个父亲在关心你们。哼,全都该死!”
他说着又从山坡滑下山沟。
这时,一轮明月从克尔瓦维茨那边升起,通常都说这月亮住在布拉多维查。月亮看见叶利舍维茨的孩子正使劲把父亲从山沟里拽上来。
“瞧呀,我的孩子们,”每当孩子们单独在家的时候,来同他们相聚的月亮总是自言自语地这么说。“现在我快走一步,免得他们迷了路。”于是月亮赶紧沿着下边的路快跑,一直跑到刚刚把父亲从坑里拽出来的孩子们的前头。
“月亮,我们的月亮,”万契克喃喃地说着把两手伸向月亮。
“我是你们的月亮,”月亮喊道。“哎呀呀,”月亮看见了发生的事就难过地说。“我为你们照亮,我们无论如何会走到家的。”
为了照亮道路,月亮在前边走,孩子们在后面跟,而落在最后的是叶利舍维茨。他一会儿唱歌,一会儿高声问道:
“喂,你们告诉大家伙儿,你们是谁的孩子?”
而孩子们只是遥望着月亮。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0年第1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010-59366555
订阅微信:
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
qikanzhengding@ssap.cn
投稿及联系邮箱:
sjwxt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