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跨文明政治交流的五重障碍:
浅谈“预设网”“参照物”与
“推理法”的作用
张善若
作者简介:
[1]
张善若,美国加州理工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
《北大政治学评论》2023年第2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
2023/10/31
版块分类:
前沿文献(推送前知网下载量:20)
PDF全文:
点击链接<
中美跨文明政治交流的五重障碍:浅谈“预设网”“参照物”与“推理法”的作用
>可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摘要:
生命世界是一群人由文化继承而获得的“知识储备”,是一张“由预设构成的、巨大的、无法计算的网”。当一个新“情况”在交流过程中出现时,我们需要到自己的生命世界中调动事实、常模和经验(facts,norms and experiences)作为参照系,并使用已经被预设为合情、合理、合适的推理法将参照系所构成的“过去”与新情况所展现的“现在”联系起来,对其进行诠释,从而完成交流行为。“跨文明交流”,即是“跨理性交流”。跨文明交流的根本困难在于,大洋这一边的听话者与大洋那一边的说话者,生命世界不重合,参照系不共享,推理法不共情。由此,“生命世界,身陷孤岛”“腾空飞起,四面临渊”“临渊垂钓,渊中无鱼”“身临其境,心临奇峰”“中国印象,西方制造”这五重障碍重峦叠嶂,连绵起伏,构成中美交流中难以逾越的鸿沟。
关键词:
生命世界;跨文明交流;参照系;推理法;预设网;政治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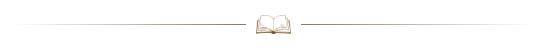
在2022年7月28日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谈中, 习近平主席强调: “从战略竞
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 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 是
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 会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产生误导。”
然而我们对美国政界、 学界和媒体关于中国政治的讨论与报道稍作了解便会认识
到, 美国政治话语并不一定认为他们在 “误读” “误判” “误解” 中国。过去几
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和传媒产业与技术的发展, 使中国与西方的语言能力、 知识积
累和媒体传播能力都获得高速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 “误
解” 不断? 身处西方视域的学习者, 在认知、 理解、 解释关于东方和中国的知识
时, 过程究竟如何? 困难到底有哪些?
本文将中美交流看作一个跨文明 “交流事件” ( communicative event), 借助
近代西方诠释学、 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相关理论, 对其基本状态进行解析。第一
部分对本文的关键概念———预设网、 参照物/ 系和推理法———进行定义、 解释,
在诠释学框架下描述它们在学习和交流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本文认为, 在日常
的交流过程中, 当我们面对一个需要解释的 “新情况” 时, 我们需要到自己的
生命世界中调动事实、 常模和经验作为参照系, 并使用已经被预设为合情、 合
理、 合适的推理法将参照系所构成的 “过去” 与新情况所展现的 “现在” 联系
起来, 对其进行诠释, 从而完成交流行为。一个特定的政治文明, 由于其历史发
展轨迹不同, 它通过政治语言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思考中所定义的 “理性” 是不
同的。如中国政治文明将 “政治稳定” 作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语言 “有道理” 的
根本前提, 不为这个目标服务的说法和论点很容易被当作 “无稽之谈”。而美国
政治文明对 “秩序” 的知识和态度则截然不同, 发展出一套反秩序、 反传统、
反权威的政治思想和话语。预设网、 参照系和推理法与政治理性的设定及其在日
常政治交流中的施行密切相关。以此为基础, 我进一步讨论在中美跨文明交流
中, “美” 对 “中” 实现深度理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五重障碍——— “生命世界,
身陷孤岛” “腾空飞起, 四面临渊” “临渊垂钓, 渊中无鱼” “身临其境, 心临奇
峰” “中国印象, 西方制造”, 并在每一重障碍中具体讨论预设网、 参照物和推
理法的作用及复杂性。在结论部分我简单讨论知识论、 方法论、 理论和实证研究
在发展与完善这一研究领域的过程中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并提出从 “生命世界般
的中国知识” 视角出发, 进行跨文明交流的研究的几个发展思路。

一、 生命世界: 预设网和参照系
多年前, 我对我的博导———一位世界知名的美国学者———说, 我因为在赶写
一篇文章, 着急、 上火, 所以牙疼。导师向我表达同情, 但同时也强调, 他无论
如何不会相信写文章的紧张和口腔病变而引起的牙疼之间会有什么因果关系。在
西方医学里, “紧张” 和 “牙疼” 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被证明, 也许永远也不会被
证明。但是有中国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 “上火” 是中国日常经验中一个有历史
有文化、 有意义有效果的概念; 通过反复观察、 长期积累而发现的现象甲与现象
乙之间的关联关系, 在中医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是有效有用的。然而当我试
图与一个西方人去交流这部分 “中国经历” 时, 我的 “脑海” 的这一部分似乎
被切掉了。看着对方空空如也的眼神, 试图交流的我如同面临断崖。而我导师作
为交流的另一方, 无论如何努力去调动自己的 “生命世界”, 也无法找到能够给
“上火” 与 “牙疼” 之类的事情提供参考的知识积累和自身经历。我的这一席
话, 也让他瞬间四面临渊, 不知该如何是好。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 在这样一个交流行为( communicative act)中, 参与者
们需要在各自的脑海里调动由 “事实” ( facts, 是交流者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
系)、 “常模” (norms, 是交流者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和 “经验” (experience,
是交流者与自己主观世界的关系)这三方面而共同构成的 “参考系统” (reference
system), 给交流内容赋予意义。只有在交流参与者各自的参考系统之间的 “重
叠” 足够大时, 他们才可能对这个交流行为的主题、 意图、 方向、 计划等达成共
识, 这个交流行为才可能获得成功。而这些事实、 常模和经验, 都是交流者的
“生命世界” 的主要内容。
生命世界是诠释学中发展已久的概念, 哈贝马斯借助舒茨(A. Schutz)和卢
克曼(T. Luckmann)的阐释, 将生命世界描绘为一个 “由预设构成的、 巨大的/
无法计算的网”。在本文中, 我将 “预设网” (web of presuppositions)这个概念
抽取出来, 与参照系、 推理法并提, 进一步解释生命世界这三个构成部分对交流
行为及跨文明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舒茨和卢克曼认为, 生命世界是一群人由文化
继承而获得的 “知识储备” (stock of knowledge), 而这些知识是一个文明在其历
史进程中, 以具体经历为基础所构成、 积淀下来的。人, 作为 “经历的主体”
(experiencing subjects), 不光从文化中继承这些知识, 更要把其中的相关内容
“插入” 到他们一项项具体的生命经历中。所以, 人们对于眼下的经历的理解和
把握, 是通过调动生命世界中的知识而协助完成的。
当我跟导师说我因为紧张而牙疼并期待获取同情时, 一个新 “情况” (situa-tion)便出现了。这句话是否能够被对方知晓和认同, 我通过这句话想要实现的效
果是否能够获得对方的配合, 要看这句话与对方的 “预设网” 中已经被预先设
定(established a prior)的合理的事实、 合适的请求、 合情的愿望之间, 是否能够
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交流参与者在他的生命世界中能够调动的, 用来对新情况
进行定义、 塑造、 给予意义的知识、 理解、 习惯, 就是本文说的 “参照系”。文
化如同空气, 是一种透明的、 不假思索的又无处不在的存在。由预设构成的生命
世界也是一样: 哈贝马斯说, 生命世界有着 “直觉性的即时感” (intuitively pres ent), 是 “熟悉的、 透明的” (familiar and transparent), 生活在其中的人, 对它
是不予置疑的。
哈贝马斯对 “生命世界” 这一概念的发展更多地聚焦在其与 “参照系” 相
关的方面, 却忽视 “推理法” ( inferencing methods)的作用。一个交流者, 面临
一个新情况时, 到自己的生命世界中调动事实、 常模和经验, 但无论如何调动、
调动多少, 也都是 “过去时”。要将既有知识与眼下需要被解释、 被学习的新情
况建立有意义、 有用处的联系, 他需要动用一定的推理和论证方式。一般认为,
推理是在证据(evidence)和说理(reasoning)的基础上获得结论的过程。在一个特
定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明中, 什么样的论证方法和说理方式是合适、 合理、 有用
的, 什么样的论证可以被看作 “理性” 的, 也通常由预设网直接限定。

二、 推理法与政治理性
我们如何将生命世界中预设好的理性, 与眼下的新情况建立联系? 本文讨论
两种典型情况: 横向论证和纵向论证。我着急时牙疼, 于是想起大家常说的 “着
急会上火, 上火会牙疼” 的知识、 周围人上火牙疼时通常会吃一些 “下火” 的
食物的行为常模以及我自己以前有过的类似经历。我将这个参照系平行地从 “以
前” 挪到 “现在”, 这就是 “横向论证” (parallel reasoning), 有时也称为 “比喻
性论证”。这样的论证方式, 不追求上升认识的抽象高度, 而讲求推理的效率和
实用性, 美国学者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在《我们赖以
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就此进行了讨论。他们指出, 人类
的 “认知活动大部分是以比喻的方式进行的”。在现实生活的认知过程中, 人
们的认知单位是由几样相互关联的状态或事情而组成的 “经历形态” ( experien tial gestalts)。通过比喻, 人们经由对一件事的认知结构去 “经历另一件事”。具
体来讲, 通过 B 来认识 A, 就是将 B 这个经历形态的不同组成部分及它们之间
的结构和关系, 投射(superimpose)到 A 这个经历形态上, 通过在 A 与 B 之间
建立这些经历形态中各个成分的冾合关系( coherence), 而透过 B 的结构来认识
A。生命世界中被认可的 “道理” 就这样自然而然地, 在 “比喻” 的过程中被转
移、 嫁接到了新情况上, 预设网中认可的那一种 “理性” 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剖
析、 论证新情况的思路。
相较而言, 归纳法一类的论证和思考方式属于 “纵向论证”: 将新情况与一
个更大的类型(category)建立联系, 调动预设网中对这一类情况的既有知识来解
释新情况。例如, “亚里士多德是人, 人都要死, 所以亚里士多德也会死”。美
国逻辑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指出, 在逻辑学传统中, 由 “小前
提、 大前提、 所以结论” (minor premiss, major premiss, so conclusion)所构成的
三段论一直被认定为 “理性论证” ( rational argument)的基本模式。图尔敏问,
“所以” 一词究竟代表了什么样的推理过程? 包含在其中的思考、 辨析、 论证过
程究竟是什么样的? 他认为 “所以” 一词所起到的作用, 依赖于包含在论证过
程中的 “保证” (warrant)、 “支撑” (backing)等不同的论证成分。保证、 支撑
都各司其职, 不宜被混称为 “大的” 或者 “小的” 前提。如, “哈里生于百慕
大。所以, 哈里是英国公民” 这一论证中的 “保证”, 就是 “在英国殖民地出生
的人是英国公民” 这样的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法律事实。因为被广泛接受, 所以没
有必要明确说出。图尔敏将 “保证” 定义为连接论据( data) 和结论( claim) 的
“桥”, 是一套 “规则、 原则、 推理执照(inference-licences)”, 其作用在于显示
“从这样的数据为起点, 到这样的结论为终点, 在这两者之间所进行的跨越, 是
合理的、 合适的 (an appropriate and legitimate one)”。
这样的保证如何使一个具体的论证过程看上去合理合法? 图尔敏指出, 是通
过 “将眼下这个具体的论证过程代回到已经被预设为合适、 合理、 合法( legiti mate)的一个更大的论证过程的类型中”。这里的 “预设” (pre-supposed)一词,
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生命世界中预设网的 “预设” (presupposition)。在现代法
治社会中,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被预设为合理合法、 因而被广为接受的一类论证类
型。关于 “哈里在百慕大出生” 和 “哈里的国籍” 之间的关系的论证就属于这
一类型, 关于哈里国籍的这个具体论证从而获得了被预设的合法性。图尔敏认
为, 如果保证的内容广为人知, 则大可不用明确说出。但当保证受到质疑时, 论
证者则需提供进一步的 “支撑”。图尔敏认为, 如果说保证的作用在于 “允许一
种关系产生和存在” (a permissible relationship), 那么支撑的特点和功能在于对
这种关系提供事实基础。如关于哈里的论证中, 保证能够在 “在英属殖民地出
生” 和 “英国公民” 之间建立一种关系, 而支撑是从资料室、 图书馆查找到的
相关法律条文中, 能够将这种关系的正负、 强弱具体落实的一套事实。
从 “支撑是事实” 出发, 图尔敏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 在不同的论证场
域(如社会学、 生物学、 统计学等)中, 保证作为 “桥” 的作用是一样的, 而在
“桥” 下起 “支撑” 作用的事实的类型是不同的。比如, 对 “彼得是瑞典人, 由
于瑞典人很少信天主教, 所以彼得不太会是天主教徒” 进行支撑的, 是 “瑞典
总人口只有 2%信天主教” 这样的统计事实; 对 “鲸鱼是哺乳动物” 进行支撑
的, 是对鲸鱼生理特征进行观察, 并将结果同生物学知识相对照而得出的事实。
这些 “事实”, 有的是数出来的, 如 “2%的瑞典人信天主教”; 有的是看出来
的, 如 “鲸鱼是哺乳动物”。
图尔敏作为一个逻辑学家的探索到此为止。本文中我们针对法律和政治论证
这样一种 “论证类型”, 进一步探索其中的 “事实” 的来源。表面上看, 法律事
实就是白纸黑字的一通书写。但是, 为什么白纸上有 “这样的” 黑字? 是谁,
为了什么原因, 将现实的 “这一部分” 抽取出来、 书写下来, 并将其定义为
“法律事实”? 在政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政治思想家们通过对政治经历进行反
复提炼, 再用政治经验对其进行来回检验, 从而书写出对当下政治现实能产生有
效回应的, 对此种政治文明的长期生存发展能产生积极维护的行政方式、 文化价
值观、 行为常模、 认知方向。他们通过书写, 将这些流动不定的认识、 做法和习
惯变为固定的文字表述, 再通过国家和社会范围的宣传与教化, 促使人们将其看
作 “事实”。比如, “英国殖民地出生的人具有英国公民身份” 这个法律事实,
是如何从无到有, 被提案、 讨论、 通过而成为法律事实的? 这背后应该存在一系
列政治动因, 如: (我在这里只是猜测)公民身份可以增强人们对英帝国的政治
忠诚和归顺意愿, 使他们更主动地响应国家在征兵、 征税等方面的需求。因此,
政治论证中的 “所以”, 在根本上来源并依托于一套由事实、 常模和经验共同构
成的、 有利于现有政治体制生存和发展的共识。

三、 “文史哲过程”:
政治理性的源起论
亨廷顿指出, 最初使用 “文明” 这个概念的是法国学者, 他们用这个概念
来描述 “定居的、 城市化的、 有文字的” 人类社会。文明是文字塑造出来的,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 哈贝马斯也指出, 生命世界是 “由语言而结构的” ( linguis tically structured)。无论是民间的口耳相传, 还是官方的书卷册目, “文” 都是政
治文明对内教化和对外传播的主要媒介。因此, 对生命世界进行书写的叙述者的
视角和观点, 对生命世界起到直接的塑造作用 这些书写者, 为什么要将某些
政治思考方式 “写” 为 “理性” 的, 而将与其不同的 “写” 为 “非理性” 的?
哈贝马斯给出了一部分答案: 知识, 作为生命世界的一部分, 其核心作用在于维
持和发展生命世界。在继承舒茨和卢克曼学说的基础上, 哈贝马斯强调, 生命世
界的维持是由三个相互支撑的自我持续(self-sustaining)过程共同完成的。首先,
“生命世界的文化再生要保证生活中涌现的新情况与已经吸纳入文化传承中的既
有情况, 在语言层面上保持勾连。这样, 在日常生活中, 传统与现实在知识上才
能保持连贯性和契合性”。其次, 生命世界通过日常的交流行为实现社会整合。
社会行为者的交流行为, 一方面要能够实现相互理解的目的, 以达成交流行为所
预期的目标; 另一方面这些交流与互动也要能让参与者们进一步发展、 确认和延
续他们在自己社会中的地位与身份。最后, “生命世界成员的社会化( socializa-tion)过程……给一代接一代的人们赋予一定的认识和能力, 让他们能够(在生命
世界给他们规范的常模和价值观的范围内)行动, 这样, 个人的经历与集体的历
史记忆之间的和谐关系也能得到保持”。哈贝马斯从强调 “经历” 的现象学、 强
调 “生存” 的存在主义、 强调 “继承” 的诠释学而发展出来这样的知识论并不
出人意料。经过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发展的现代诠释学认为, “求知者” ( kno wer)对文本的理解永远是被他们 “前理解” 中的 “先把握” 活动所规定的, 而
前理解正是历史 “传承物” 所塑造成形的。同时, 研究者也并非实证主义认为
的、 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客观中立的观察者, 而是历史和政治经历的 “事中
人”, 在自己具体的生命经历中与被研究事件形成 “经验关系” (experiential rela-tion to things)。
将哈贝马斯和图尔敏的理论带入跨文化比较研究中, 我们更清晰地发现, 在
一个特定的政治文明中, 通过被预设为合理合法的推理法而推出来的 “理”, 能
够给生命世界带来新鲜的生命力和合法性。推理法就好像是使生命持续运转的要
害器官、 狂奔的赛车的发动机、 让花朵绽放的阳光。合理合法的推理法之所以被
预设为合理合法, 正是因为它们将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秩序进行合理化、 合法化并
给予其保护。也因此, 生命世界的成员在使用这些推理法时还获得一种正义感:
我们这样的 “理” 才是 “理”, 你们那样的 “理” 不是 “理”。一个政治文明中
的政治理性, 为这个政治体制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 一个政治文明中的知识, 展
现的是一套浓缩版的独特的政治经历。
在中国悠远、 浩瀚的政治文本实践中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我们会发现中国政
治理性形成的 “文史哲过程”。在中国古老的职业官僚体制中, 作为儒家学者的
官员, 一方面用儒家知识和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另一方面又从自己的政治经验出
发, 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讨论, 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简单来说, 儒家知识分子用
“文” 对历史事件发展进行捕捉、 记录、 讨论, 形成 “史”; 通过对 “史” 的讨
论和分析推出政治思想, 即 “ 哲”; 而 “ 载道” 作为 “ 文” 的使命, 又赋予
“文” 以隐喻性、 批判性、 规诫性、 和谐性等一系列功能和特点。这样的 “文”,
又被用来对 “史” 进行下一波捕捉。我认为 “文史哲” 作为一个概念, 可以看
作对中国政治文化、 政治文明发生过程的高度概括。正是这一套 “文法”, 以其
独到的修辞手法、 论证方式、 话语策略, 建构了中国政治文明生命世界中的预设
网、 参照系和推理法, 政治理性在此滚滚文潮中不断演化、 发展。从宏观、 历史
层面上看, 儒家传统中的 “民心” “德政” 等价值观, 就是在 “文史哲过程” 中
“生成” 的。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 这些意义、 价值观逐步稳定下来, 为
被这一政治文化意义系统所 “笼罩” 的行为者、 思考者, 提供了一套 “既有”
的意义和理性, 让他们可以将新发生的政治话语和现象 “带回” 到这个意义系
统中, 由此获得意义。正是这样的诠释过程, 将传统和理性都自然而然地融会贯
通在中国政治知识的创造中。直到今天, 学者们对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如天
命、 民本等主要命题, 仍然自然而然地将其重置于其自身发展的历史、 政治、 文
化背景中进行理解和诠释, 同时关注这些概念的现实政治意义, 试图从中国视野
出发, 以中国政治思想为工具来解释近现代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成功与失败。
因为中国政治文明比西方提前三千年进入了 “文为人用” 的 “现代”, 生命
世界 “主动” 地、 有意识地通过语言的运用而自我延续、 自我巩固这一特点,
在中国政治文本、 政治文化中也更加突出。中国的 “ 文治”, 通过 “ 写” 来
“治”, 既是传统, 也是理想。其中浓缩了中国文人对 “文为任用” 的信心, 对
“文” 的长久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的认识, 以及对 “文” 的教化和昭示能力的
深刻思考与积极实践。孔子改《春秋》便 “尽小污” 而 “藏大恶” 以求政治稳定。
春秋笔法经过后世 “大一统” 的洗礼, 发展成为一套促进良政善治、 和而不同
的政治文法。美国政治文明的历史经历和知识提炼塑造了截然不同的 “写法”。
如亨廷顿总结, 在美国大部分的历史中, 美国的自我定义在于 “不同于欧洲”:
美国是充满自由、 平等、 机会和未来的国度, 而欧洲则代表着压迫、 阶级冲突、
等级和落后。这样的 “政治理性”, 在美国历史早期适应它追求独立的需求,
在 20 世纪以后帮助它树立独立的政治和外交形象。冷战以来, 这一套知识和话
语更成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扩大和巩固自己软硬实力的有力工具。在美国的国内
政治中, 与权力针锋相对、 推崇言论自由、 提倡信息透明的一套批判性文法, 其
底色是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经历, 浓缩的是深入骨髓的对权力的不信任, 最
终目的是使得保证个人自由的政治形态得以衍生发展下去。

四、 中美 “跨政治理性
交流” 的五重障碍
在交流行为中, 生命世界中的参照系为其内容、 目的等提供有效性( valida-ting references), 推理法则为其论证过程提供合法合理性 ( rationalizing infer-ences)。从这个方面而言, 中美的 “跨文明交流” 实质上是 “跨政治理性交流”。
从政治文明发展的主轴和轨迹来看, 中国的主旋律是 “大一统”, 欧洲的主轴是
皇权、 教会、 贵族之间的博弈, 而美国政治的发展轨迹则是反传统、 反 “一统”
的权力制衡。围绕和呼应这些主题的经验, 通过思考和总结而形成知识, 并被绵
延不断地叙述和记录成百上千年, 各自生命世界中的 “有效的” 参照物和 “理
性的” 推理法也截然不同。相比之下, 西方与中国相互了解和学习的时间仅仅几
百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 西方势力通过殖民霸权直线上升, 中国因内忧外患、
救国强民而无力顾及上层建筑。在当今世界范围的政治知识、 政治话语环境中,
西方处于强势地位, 西式的理性常被赋予不言自明、 不证自明的正当性, 与其不
同的想法和做法也不言而喻、 无须证明地失去正当性。更应当认识到的是, 当中
国面向美国进行政治交流时, 我们的 “对手” 深深嵌入于西方的生命世界, 他
们能够调动的是在这种知识环境和政治状况下发展出的关于中国政治的知识。他
们既有的西式理性和关于中国的 “截断式” 的知识, 使得中美跨文明交流中常
出现以下五重障碍。
第一重: 生命世界, 身陷孤岛。
生命世界如 “天网恢恢” 而无所不包, 我们对它的接受是无条件、 无质疑
的, 发生在其中的每一个交流事件都起到巩固文化继承、 强化社会整合的作用。
哈贝马斯强调, 每一个具体的交流情况都只唤醒我们对生命世界中一小部分现实
的觉知。这样的认识构成一个有限的、 “临时的现实” (contingent reality)来帮助
我们完成眼下的交流行为。即使我们有时对生命世界中的一部分会有些质疑, 但
这却无法撼动我们对整个生命世界的 “天真的信任” ( naive trust)。交流实践对
生命世界不断的、 完全的、 无法替代的依赖, 与 “一切都可不同” 性的挑战是
不兼容的。因而, 生命世界, “不可置疑, 只可崩塌”①。生命世界的 “不可超
越”, 好比如来佛的五指山, 孙悟空再有本事却也是跳不出去的。
这一点我在面向美国大学生教授中国政治的经历中感受深刻。每次教中国政
治, 我首先需要花几个星期来给学生建构一个 “教室里的中国生命世界”: 儒家
传统、 差序格局、 百年国耻、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集体主义文化等等。学生迈入
教室就进入这个生命世界, 同时将他们的美国理解 “悬置” 起来。在这样的知
识结构和交流环境中, 中国政治一切都讲得通。然而他们一出教室就重新跨入美
国生命世界的河流中, 中国的生命世界立刻崩塌。他们在教室里学到的知识, 能
够帮助他们理解和解释一些关于中国的个别事实, 也促使他们思考美国的中国知
识的局限和偏执。然而这些局部的、 书面的知识, 无法撼动紧紧将他们包围的、
活生生的美国生命世界。
第二重: 腾空飞起, 四面临渊。
当今世界的全球通信网络、 影视技术和互联网, 使得跨文明传播无所不在。
在这样的交流环境中, 跨文明交流的核心载体是 “文本”: 发生在中国的政治事
件, 身处美国的人无法亲自体验; 此事要传播到美国, 必须得有人将其时间、 地
点、 人物、 事件用文字描述出来, 将此文本传输到美国, 美国的报纸、 电台、 电
视台及各社交媒体又依据自己的需求对此文本进行删减、 勾画, 进行下一轮传
播。在此过程中, 一个具体的文本对这件事写什么、 不写什么、 怎么写, 要通过
记者编辑的选择和裁夺、 新闻节目主持人 “阴阳顿挫” 的加工以及读者观众通
过各种形式的反馈和讨论。这件事, 最后在美国被认识成什么样, 是在这样的过
程中由这些交流行为者们共同塑造的。这样的交流过程将一个政治事件从它自身
的文化、 语言土壤中连根拔起, 带它穿越时空而放入一个全然不同的生命世界
中, 一个从截然不同的政治历史进程所积累提炼而形成的政治理性中, 在这里被
解读、 被讨论、 被评价。
这样的 “距离化过程” (distanciation)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关于文本
和话语的理论思考的一个主要方向。利科指出, 在以口语为媒介的直接交流中,
听者与说者的关系相对稳定, 这个关系在听者对说者的理解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但是当被说出的话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 传播出去, 听者与说者的既有关系完全
消失, 使这些话语脱离了它们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现代崇尚民主平等的文化也让
人们普遍认为, 只要能识字的人都有权力来解读这些文本的意义。从本文的理论
视角看, 在口语交流中, 听说双方共处于一个生命世界中, 所调动的参照和推理
系统有相当大的重合, 因而具备交流成功的基础。而依托书面文本进行的跨文明
交流则完全脱离了这个参照系统, 其代表的 “共享的现实” 也不复存在。因
此, 现代全球通信网络看上去可以让人们如同坐上飞毯一样腾空而起, 瞬时进入
另一个国家、 社会和文化, 了解情况甚至参与讨论。然而, 深想一层, 我们认识
到, 这样的交流方式也使人们彻底脱离了自己的生命世界和意义系统, 高高在上
却四处临渊, 忽然间, 一切都不知该从何谈起。
第三重: 临渊垂钓, 渊中无鱼。
在西方的听者, 听到这些关于中国政治的说法后, 会到自己的生命世界中寻
找有用的参照物和推理法。然而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中国材料, 能找到的只有西方
教育、 媒体、 社会在过去几十年生产出的定义中国、 描绘中国的内容。这种由生
命世界缺失造成的 “缺氧性” 理解是中美交流的主要症结之一。我用贝淡宁
(Daniel A. Bell)与汪沛的新书②做简单说明。该书的主要论点是: 政治、 社会、
文化中的等级制度, 因为自然, 所以正常, 而且可以起到促进平等的作用。作者
用荀子记载的 “乡村饮酒” 的例子———在村里的节日庆典上, 年长的人与年幼
的人同饮一杯酒———来展示在中国文明中, “和谐” 和 “等级制” 在理想与现实
两个层面上同时存在。我读了这个例子, 脑中浮现出小时候在外婆家吃饭的场
景: 全家二十来口人聚在一起, 多么热闹; 虽然第一碗面永远端给外公, 而这样
的 “等级制” 却自然而然且充满温情。但是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西方人, 特别
是历史上(相对来说)没有经历过长期的、 严格等级制度的美国人, 能够唤醒什
么样的参照物, 演习什么样的推理法? 当下西方民主政治的左翼和右翼都以追求
平等、 打破等级为基本诉求。任何关于 “和谐的等级制度” 的观点和倡导, 都
会立刻引起深深的怀疑。由于这个文化不鼓励人们用 “和谐等级” 的概念来观
察和思考世界, 因此, 无论是在自己每天亲身经历的政治交往中, 还是在被报纸
电视 “媒体化” (mediated)的政治 “现实” 里, 人们都很难找到可以用来验证这
个概念的事情。相反, 在这样的文化中, 人们能够调动的很有可能是关于 “不和
谐等级” 的例子和知识, 比如天主教会依靠等级制度几十年来隐瞒欺凌幼男的丑
陋行径, 少数族裔在 “民主公平” 的旗帜下受到长期不平等待遇, 等等。在上
文关于中医的例子里, 我导师对中医进行一番搜索后, 找到的是一些西方文化对
于东方 “神秘主义” 的既有看法以及西方自己的关于 “迷信” 的各种想法和
做法。
在中国政治文明中, “大一统” 不仅是意识形态, 而且是深入人心的知识:
中国政治历史中有大量的经历与知识被用来讨论、 展示和证明大一统的重要性,
如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等, 都是家喻户晓的说法。美
国文化可以说是生性多疑的, 对 “统” “合” 之类的概念会本能地产生怀疑、 反
对甚至反感。原因也很简单: 如果天天强调守规矩, 英殖民者就推不翻, 美国也
就不会诞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常听到一句话: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
国大地。” 这句话温暖动人, 为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
它调动了中国文化的预设网中对温暖明媚的促使万物生长的 “春风” 的形象、
对 “有国才有家” 的集体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政府广施仁政的期待。因此, 改革
开放的 “春风” 应该 “吹遍” 祖国大地, 因为这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在美国政
治文明中, “吹遍” 就不一定是好事了, “祖国大地” 这个概念恐怕也要遭到质
疑。美国文化对这个现象的直觉反应会是: “谁允许你吹遍了? 谁让你吹遍了?”
大部分美国人了解、 学习中国知识, 就好像一个人临渊钓鱼, 但是这个池里不但
没鱼且只有螃蟹, 所以他们对鱼的认识, 也只能是根据螃蟹的模样而想象出
来的。
第四重: 身临其境, 心临奇峰。
正如 “真善美” 与 “假恶丑” 这两个词所展现的, 知识、 道德与美感的关
系是密切不分割的。威廉·瑞迪(William Reddy)研究了情感(emotion)在法国大
革命的酝酿和爆发过程中的作用, 并且对情感的政治作用进行了精密扎实的理论
构建。他将情感定义为 “一组松散连接的思维材料(thought material), 由不同的
符号构成, 有目标性, 以图式(schema)的形式存在, 一旦被激活, 很容易会超越
理性注意力(attention)的管控能力, 且无法在短时间内被转化( translated)为行动
或语言表达”。瑞迪还指出, 每一个政治体制都有属于自己的 “ 情感体制”
(emotional regime), 为于这个政治文化中生活的个人在情感的抒发、 表达和反应
等方面提供规范性引导。由于情感是有目标性的, 当几个重要的情感目标相互冲
突时, 当事人就会经受 “情感折磨” ( emotional suffering)。在这种情况下, 情
感体制会对此时此刻 “应有” 的情感感受和情感反应做出指导。
在中国政治生命世界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 政治思想家们通过 “文捕捉史、
史推出哲、 哲塑造文” 这一轮一轮的记录和叙述, 编织了一个庞大强劲的情感体
制。在这里, 情感经历依托于中国人所共享的政治和文化身份, 是具有重大意义
和巨大力量的历史和文化符号。在抗击疫情期间, “白衣执甲” 一词, 仅用四个
字就描绘出勇敢无私的医护工作者照顾和保护病人的动人场面。“最美逆行” 四
个字, 将全国的医护工作者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为救国救民而逆水行舟的
壮阔局面勾画出来。引自《诗经》的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八个字将历史上无
数类似的经历浓缩于其中: 生死与共的中国人, 将自己的最后一层衣衫献出来作
为共同的防御, 把自己的最后一滴水、 一口饭拿出来作为共同的供给。从小学唱
国歌的现代中国人, 哪一个听了 “万众一心” 一词心中能没有暖流? 这些生动
的语言, 制造出一个个具有历史纵深、 特定意义和巨大力量的 “政治戏剧”; 而
剧场, 如亚里士多德所讲, 正是通过一套特定的剧情结构来调动人们心底深处真
善美交织的正义感。通过这样的情感经历, 读者们共同进入了一个 “政治剧
场”: 他们成为其中的一员, 获得一种特定的身份, 自觉自愿地扮演着各自的
角色。
现代媒体制造出的生动逼真的传播效果, 现代新闻业所写出的即时的、 同步
的、 充满确定性和自信的新闻报道, 都会使身处美国生命世界的读者有 “身临其
境” 的感觉。如前文所述, 作为生命世界自我延续的一部分, 在 “美国制造”
的中国的新闻和教育会不停地顺着美国的参照系和推理法来解释中国现象, 这样
的解释因此而成为美国听众能听到、 看到的唯一解释。在这样的信息和知识环境
中, 美国建立在反集权反压迫、 追求民主与自由基础上的自我身份认知, 不可避
免地将中国式的治理方式和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态, 放在了对立面, 而 “距离
化” 这一跨文明交流、 跨时空交流、 跨政治理性交流的内核过程, 被 “眼见为
实” 的幻影掩盖了。美国观众在新闻中看到的栩栩如生的 “事实”、 在访谈中听
到的打动心扉的经历, 实际上是记者、 编辑、 制片人为迎合他们的视角所特意选
取、 塑造的。然而这种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的个人经历, 使他们对在此过程中促
生成形的对中国的认识深信不疑。
更重要的是, 现代媒体传播在观众心中激活的, 是知识和事实层面的认知、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唤醒以及同情、 愤怒、 怨恨等情感反应相互刺激、 相互交织
的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状态使读者和观众有一种 “心临奇峰” 的感
觉: 我亲自 “上去” 了, 我亲眼看见了, 我的感受是最正确、 最不可动摇的。
瑞迪指出, 对个人来说, 什么样的情形引发什么样的情感以及应该如何反应, 是
由这个社会和文化中的 “情感体制” 所引导的。同时, 情感发生时, 在短时间
内又很难甚至无法被翻译成可表达的语言。也许正是情感的这种 “不可表达”
“难以表达” 的特性, 使人们容易被锁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一刻的感受, 因为
我 “无法说出口”, 所以别人 “永远无法完全了解”, 因此 “没有人比我更知道
这一刻的真实”。在这种情感性认知中, 你的 “无法了解” 强化了我的感受的
“真实”。因而, 我认为, 情感体验的公众性和私人性同时塑造、 锁定了这种
“确信无疑” 的感受。
第五重: 中国印象, 西方制造。
西方知识和媒体体系, 一方面缺乏对中国生命世界的直观和直接的了解, 同
时又主观意识浓烈、 知识制造能力强大, 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 “西式的中国生命
世界” 的基本形态。因此, 从中国视角看, 中国在西方视域和知识中常常被
“自然而然” 地构建为 “他者”, 并且在这样被异化的位置上被分析、 被解释,
甚至被刻意扭曲、 脸谱化、 妖魔化。以这种方式呈现出的 “中国”, 进一步呼应
和巩固从西方视角出发理解中国政治的既有知识。这一套知识围绕着这样几个关
键词: 共产主义即是自由民主的反义词, 与美国和西方是 “永久性的殊死的搏
斗”, 联想冷战; 威权主义, 充满贬义, 联想冷战的苏联; 民族主义也极端危险,
联想纳粹德国。然而了解中国政治生命世界的人会明白, 中国政治远远比这些标
签庞大复杂, 其中大部分的预设、 文化和历史参照物、 合理合法的推理法, 发
源、 发展于中国儒家传统和大一统的政治历程, 并与中国近代百年国耻的鲜血淋
漓的记忆、 救亡图存的深刻教训直接相关。媒体业和学术界在此种中国知识的制
造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
罗杰·福勒(Roger Fowler)在对媒体语言的研究中指出, 新闻并非自然生
成, 而是被 “制造” ( newsmaking)出来的。文化性因素, 如与读者的现有文化
的相关性、 距离感是否能够引起共鸣等,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事件是否有新闻
价值。福勒由此认为新闻业是强化 “民族中心主义” ( ethnocentrism) 的工具之
一: 每天的新闻都在制造巩固一个具有共性、 共识的 “我们”。同时, 这样的倾
向和做法也制造分裂: 不同政治立场的 “对方” 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 “他们”,
为了巩固 “我们” 内部的团结, 新闻业对 “他们” 的刻画也越来越不留情面。
在中美或其他形态的跨文明交流中, 写作者有时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 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