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t McGowan
翻译:球球
编辑:Ent
几十年前,行为神经生物学家大卫·克鲁斯(David Crew)读到了一则关于沙原鞭尾蜥(Aspidoscelis uniparens)的奇怪报告,这是一种小而细长的、栖息在美国西南部蒿丛的蜥蜴。论文声称这个物种全都是雌性,通过无性繁殖繁衍后代。
在克鲁斯看来,高等脊椎动物还能有这种事情在生物学上是讲不通的。“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他说。不过他感到好奇,而一位当时要去新墨西哥州的朋友说可以帮忙在野外采集一些。克鲁斯当时在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工作,就在动物饲养室装了玻璃缸,养了半打鞭尾蜥。有一天,他注意到一只蜥蜴在咬她“缸友”的后腿和尾巴,然后就骑了上去。克鲁斯立即意识到她们的行为和蜥蜴交配行为如出一辙。
不过为啥两只雌性要模拟交配动作?
“我简直是摔出了椅子跑去拿相机,”克鲁斯说。“那时候胶卷都是放在冰箱里的,我手忙脚乱地试图把胶卷塞进相机,这样我才能把这场面拍下来,因为当时我觉得这很稀罕——纯粹是奇怪。”他抓拍下这两只采用了“甜甜圈”体位的蜥蜴——在这个扭曲的交配姿势中,上位的蜥蜴扭转身体并且咬住另一只的肚子。
 图片来源:alamy.com
图片来源:alamy.com
克鲁斯现在已经是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动物学和心理学教授。那天他意识到,鞭尾蜥的这种行为可能不只是在闹着玩。他所看到的景象,对他接下来数十年里探索蜥蜴性行为的神经基础至关重要。对他来说,在动物饲养室的那天打开了对生物学理解的全新世界。自此之后,他和其他研究者表明,原来单性繁殖对于我们理解繁殖和演化之间关系意义非凡,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有性生殖远不是一个完美的繁殖方式。它让物种担负了一个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叫做“雄性”。如果一个物种约有50%由不能生娃的雄性组成,相对于另一个绝大部分都由能自己生娃的雌性组成的物种,前者在繁殖方面就居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了。
而且一种自己一个就能繁殖的动物在占据新领地时很有优势,因为她不需要一个伴侣就能开枝散叶。她的每一个孩子也都会生出自己的后代。有性繁殖“似乎像是个简单的事儿,不过从演化角度来看的话,这很低效,”罗勃·丹顿(Rob Denton)说,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单性的蝾螈。“要是大家都是雌性的话,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女性力量:沙原鞭尾蜥不需要雄性就可以繁殖——实际上,连雄性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她们靠无性繁殖来繁衍。图片来源:Ted Morgan/Flickr
女性力量:沙原鞭尾蜥不需要雄性就可以繁殖——实际上,连雄性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她们靠无性繁殖来繁衍。图片来源:Ted Morgan/Flickr
虽然有劣势,但是有性繁殖似乎确实赋予了物种一个无可争议的优势。它重组了个体的基因,使得物种能够保持其性状的多样性,而物种需要这种多样性在各种挑战下生存下来,比如更快的捕猎者、气候变化、巨大的彗星撞击等各种未来会丢出的生存挑战。这样的话,任何在个体中随机出现的有用突变,都能够让物种作为一个整体获益。性也能防止任何个体近亲交配。“基因多样性总是被看作来适应瞬息万变的生存条件的方法。”塔尔萨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华伦·布斯(Warren Booth)说。
按照这个逻辑,单性生殖在演化上是死路一条。本质上只有一组基因组的单性种群对于各种生存挑战应该都是准备不足,这会是灾难性的。然而沙原鞭尾蜥还是生生不息。这也并不是唯一的特例。自从DNA测试变得廉价,单性繁殖就开始在我们面前逐渐展现,仿佛一个暗黑的秘密,自从达尔文的小猎犬号之旅以来就一直被某些物种隐藏着,不为生物学家所知。而有些研究者开始认为,这或许不失为一种生存的好办法。
在20世纪初期,霍华德·休斯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堪萨斯城斯托瓦斯医学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彼得·鲍曼(Peter Baumann)开始探索鞭尾蜥的细胞内部,想要进一步搞明白为何鞭尾蜥属的某些成员是正常有性繁殖的,而另外一些是单性繁殖——以及单性是否真的是演化的死胡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研究者发现,单性鞭尾蜥个体的基因比人们预料的更多样。在尚未发表的研究中,鲍曼发现在基因组的某些部分,单性鞭尾蜥的基因多样性和其有性繁殖的近缘物种相比,是一样高的——但在其他部分,单性的基因多样性远比两性的低。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一个团队把一个单性繁殖鞭尾蜥谱系中的七代和有性繁殖的鞭尾蜥做对比,比较了它们较易测量的性状,比如肚子上的鳞片,或者右腿上的孔。即使单性生殖的鞭尾蜥都具有完全相同的DNA,单性繁殖的蜥蜴展现出的生理多样程度和有性生殖的蜥蜴是一样的。
这怎么可能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沙原鞭尾蜥一开始就是个杂交种。这一整个谱系都是两种近缘鞭尾蜥的杂交产物,它们显然在几千年前开展了一番啪啪啪大冒险。杂交种如果能存活,往往就能繁盛,想必是因为它们的双亲亲缘关系太远了:它们得到了两个不同物种的基因的好处,减少了继承两套不良隐性基因变体的可能性。
 图片绘制:Tara Jacoby
图片绘制:Tara Jacoby
或许因为双亲的错配,沙原鞭尾蜥生来就有三套DNA,这是路易斯·潘诺克(Lewis Pennock)在1965年发现的。不同于一般情况下每个细胞有两套基因组,沙原鞭尾蜥有两组来自母亲,一组来自不同种的父亲。对于任何给定基因,她可能都有三个稍显不同的版本,提高了其中某个能够派上用场的概率。“显然有一套额外的基因是一个优势,”鲍曼说,虽然这种蜥蜴具体如何调节控制那些额外的基因来利用它们的多样性,这仍然是个谜。
在一项2010年的研究中,鲍曼还发现鞭尾蜥用一套特殊的机制,来使这种基因多样性能连续多代保留下来。正常情况下,在有性繁殖的动物中,许多亲代DNA会在卵子和精子的形成中被“丢出来”:在基因组自我复制之后,配对的染色体会与相邻的染色体一一排列并“交叉”,互换DNA片段。比如说,在一个雌性体内,当她产生一个卵子的时候,源自她父亲的21号染色体的副本和源自她母亲的21号染色体副本重新组合。这一基因大洗牌在她的每一个卵子中都创造了一个她双亲基因组的独特组合。精子的形成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会如此不同——每个孩子得到的双亲基因遗传组合都不同。
与此同时,约有一半的双亲的遗传变异也丢失掉了。这对有性繁殖的物种不是问题,它们的卵细胞会和一个与其在基因上显著不同的精子细胞结合。但是对单性繁殖的物种来说就是坏消息了:当染色体在每一代重组和交叉互换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变异也丢失了,越来越多的基因有了同一变体的多个副本(等位基因)。最终,后代基因组里每个基因的等位基因都一样,使它们容易得到隐性遗传疾病。就好像被反复翻录的旧磁带一样,每次翻录都丢失掉一些些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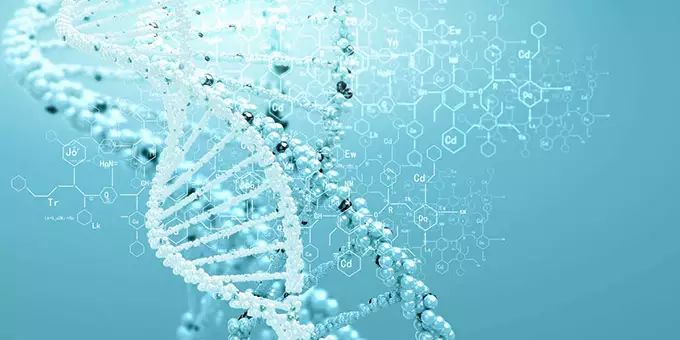
在那篇论文中,鲍曼解释了鞭尾蜥如何通过“定制”卵的形成过程来防止遗传变异的流失。当一个鞭尾蜥的卵形成时,基因组会把自身再次复制一遍。额外的DNA使得卵形成过程得以修改,让只有已经完全一致的染色体才会交换遗传物质。因为它们是一样的,重组和交叉互换不会有任何改变:产生的卵细胞中有一半DNA来自这只雌蜥蜴远古的雌性祖先,另一半DNA来自她远古的雄性祖先,而它很快会变成一个新生的鞭尾蜥宝宝。所有的遗传信息都保留给了下一代,一种无损失的繁殖形式。每一代单性生殖的鞭尾蜥就这样保留了其上一代的基因多样性。
而且,演化生物学家创造的数学模型显示,良性突变在以单性生殖为主的种群中实际上能传播得几乎一样快。有性繁殖只需要每10代或者20代才发生一次,它的好处似乎就达到极限了;正如最近的一篇论文所述,有性繁殖只需要实际发生次数的百分之五到十,就足够得到和每次都发生所相同的基因优势了。不过模型暂且不论,长期以来都没有太多直接的实验证据证明单性繁殖可以得到长远的成功。
这可以解释单性繁殖对于鞭尾蜥来说为何是个如此成功的策略。但是她们为何要假啪啪呢?在1979年的夏天,克鲁斯在他的实验室看到的究竟是什么?答案与物种中性别角色的复杂性有关。
沙原鞭尾蜥并不扮演固定的性别角色。她们每一只在不同的时可“雌”可“雄”,并且还能任意转变。在大部分有性繁殖物种中,性行为由以下三个因素塑造:两套不同的染色体(比如XX和XY),塑造大脑发育的行为相关的不同激素,以及性成熟个体的不同激素模式。
不知怎地,鞭尾蜥无须这些机制就可重现类雄性行为。克鲁斯实验室的前研究生、哈佛大学鲍尔基因组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劳伦·奥康纳(Lauren O’Connell),正在研究使得沙原鞭尾蜥转向单性生殖的基因变化。她发现,一个通常由睾酮和其他“雄激素”来触发和关闭的基因,在这些单性生殖的动物中却反而易受孕酮影响,之前我们只知道孕酮在维持妊娠中极为重要。

孕酮是支持胎儿早期生长发育的重要激素,高浓度的孕酮对增大的子宫起着明显的镇静作用,对早期妊娠的支持也十分重要。
孕酮会触发雌性蜥蜴表现出雄性的行为。在一只沙原鞭尾蜥排卵前,她的孕酮水平较低而雌激素水平较高,她就在性行为中扮演雌性角色。技术上来说,这是“假啪啪啪”:这或许看起来是假的,但是对蜥蜴来说完完全全是真的,这会触发她的激素变化,从而开始繁殖过程。假交配通过重新同步“受”的一方(被咬和骑乘的一方)的激素节律,刺激她体内的卵开始发育。在排卵之后,随着她的孕酮升高,她会表现出雄性行为。在她咬和骑乘其他雌性时,她的体内或许已经在孕育着蛋了。
克鲁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几项研究中发现,那些没有机会经历假交配的蜥蜴下的蛋没有那么多。接着他在2008年发现大脑的两个区域——视前内侧区和下丘脑腹内侧核——在两种行为中都以此消彼长的方式参与。在类雄性行为中,视前内侧区变得活跃起来,而下丘脑腹内侧核变得不活跃。在类雌性行为中,则正好相反。
在蜥蜴的脑中,雌雄皆有可能,只要等待正确的输入信号就行了。“大脑天生就是双性的,”克鲁斯认为。不过在有两种性别的物种中,“被预先设置偏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他说,这一点在鞭尾蜥身上非常明显,但是大体上,动物的大脑或多或少都是这样。这些单性生殖体让我们知道了自己在性别设想上的局限性。大脑不是被预先设计成扮演雌性或雄性,克鲁斯说,而是由性染色体、激素、环境和经历所组织而成的。假交配使得对于雄激素和雌激素、雄性基因和雌性基因的简单化设想复杂了起来。“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这种相同的基因。”克鲁斯说。“其实就是一支成员相同的管弦乐队,但他们演奏的乐曲不同。”
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克鲁斯说。他是展示同性交往的生物要素的第一人,他的研究得到了早期同性恋活动家的拥护。在他心中很早就认清了性向不是二元的,不过这一事实直到最近才得到了更广泛的文化认可。“人们是动物,”他说。“我们只是一种动物,只是凑巧有了社会和文化。”

然而,在演化的长河中,通过杂交创造出新的单性物种或许也不鲜见。或许,跨物种杂交然后单性生殖,这样的过程一直都是一个基因大熔炉,能产生沙原鞭尾蜥这样全新的单性物种——不是通过许多代缓慢逐渐地生成的,而是一次交配行为一下子冒出来的。如果它们创造的杂交种是单性繁殖的,这条新的血脉从一开始就是生殖隔离的。Biu!物种速成。
鲍曼认为这个观点相当令人信服。2014年,他的团队在实验室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杂交单性生殖体。他们让两种鞭尾蜥繁殖了,具体地说,一种是小型的条纹鞭尾蜥(一种有性繁殖种)和一种奇瓦瓦斑点鞭尾蜥(一般情况下是单性繁殖体)。虽然生出来的大部分宝宝都是不育的,他们还是繁育出四条新的单性繁殖杂交谱系,每条都有四组基因组——开天辟地的新生种类。
鉴于这种情况在实验室如此顺溜地发生了,鲍曼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在新墨西哥州的蒿丛中寻找同样的跨种杂交产物。他们猜想,既然它长得很像双亲——一种细长的、茶色条纹的蜥蜴,长尾是一抹天蓝——它应该早已存在。只是还没人认出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