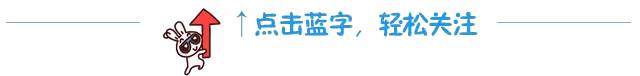

2018
年
3
月
8
日
来源:财经十一人
经济学家圈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
2018
年年会于
2
月
25
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今年年会的主题是:
“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
。以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的发言。
张文魁预警:中国要警惕粉红财团
否则可能发生危机

大家都很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走势,特别是宏观杠杆率较高、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较大等问题,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几个宏观病症,许多宏观经济学家都在把脉搏、开药方。的确,这几个病症合在一起,就增加了我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赢三大攻坚战,首位就是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一战,是很有针对性的。刚刚公布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并要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我认为,
必须要看到宏观病症背后的微观病灶,这样才能使经济政策抓住要领、产生预期效果。
杠杆率快速上升这个最主要的宏观病症,是国家宏观政策失误造成的吗?其实在较大程度上并不是这样的。宏观杠杆率在
2008
年到
2012
年上升了大约
40
个百分点,那一波上升可以算是货币政策主动宽松的结果,那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增速快速下滑而实行总量扩张政策的后遗症。但
2012
年之后呢?国家已经完全意识到不当宽松宏观政策所产生的严重问题,已经确定要控制宏观杠杆率,但
2013-2017
年杠杆率却上升了大约
60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一波杠杆率上升带有被动的性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迫的,或者说是被微观病灶倒逼的。全要素生产率严重下滑的病症,是与杠杆率严重上升的病症同时冒出来的,在
2008
年之前的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年平均增速基本上稳定在
3%
左右,
2010
年之前还可以维持在
2%
左右,而
2012
年之后急剧下滑到
1%
甚至更低。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要核算全要素生产率,但这更不易为宏观政策所可以解决。中央有关会议在几年前就一再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说中央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完全不亚于对控制杠杆率的重视,我还没有看到另外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对这个经济学概念和参数如此熟稔和在乎,但事实告诉我们,必须要精准发现宏观病症下面的微观病灶,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整个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都不能离开这个逻辑。
微观病灶在哪里?
实际上,中央多次重要会议都已经强调,要清理僵尸企业。大量的僵尸企业就是一个病灶。这个病灶不但已经被政府看到了,而且也有许多学者作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但是中国经济的微观病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第二个微观病灶就是
财团企业
,严重的问题是第二个病灶既没有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也没有得到学者的应有重视。
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的杠杆率上升那么快,但广大中小企业却得不到相应的信贷资源,
这些信贷资源到哪里去了?一部分被僵尸企业消耗掉了,大部分信贷都被大企业集团拿走了。
这些大集团许多是国有的,还有一些是民营的。
现在
国有企业
特别是
央企的财团化
非常严重,几个大企业合并起来,就列入中国
500
大甚至世界
500
大,
获得贷款和发行债券就容易了
,然后就去搞金融、搞房地产、搞贸易,并热衷于资本运作,就成了大财团了,这些是
红色财团
。
央企看起来只有
90
多户,但实际上每户央企下面平均有
500
多个法人企业,层层叠叠,一般都有五六层,多的有十一二层
,结构复杂,业务庞杂,一般人搞不清楚,甚至连总部也不容易搞清楚。
地方国企
也有已经或者正在财团化,特别是那些平台化国企更是如此,
把几个国企进行名义上的合并形成新平台
或者将一些国有产权和国有资源注入到新设的平台,
再进行大量融资和投资
,开始时还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随后就不断进入金融、房地产以及各种时髦的所谓高科技领域
,笔者几年前研究
这些平台化企业时就指出其走向严重的
政企边界不清
和
企企边界不清
的趋势
,现在实行财团化之后就更是如此了,以至于宏观杠杆率当中到底哪些归于政府杠杆率哪些归于企业杠杆率都不容易计算。
一些大民营企业集团也通过类似套路实现了财团化
,如中国民营企业
500
大榜单中,许多都成为财团了。这些大财团动辄上千亿甚至几千亿的贷款,但是它们的偿债能力和透明度怎么样?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健康指标怎么样?大部分都很差。这类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了。
对这个微观病灶如何处理,事关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攻坚战这一重大任务。中国还没有出现过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曾经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家作一些分析,有助于看清中国的主要隐患到底是什么。
2018
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十年前发生了美国和欧洲金融风暴,二十年前发生了东亚金融风暴。那几场金融风暴各有病因,我分别称之为北美病、南欧病、东亚病所导致。北美病主要是住户部门过度按揭贷款和储蓄率不足,南欧病主要是人们工作时间短、福利高、实体经济衰败,东亚病就不一样了。
二十多年前,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一批财团崛起,这些财团不但汲取了大量金融资源以进行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而且政商联结也非常严重,
这就是东亚病
。
东亚的那些大财团,许多直接进入了金融行业,此外还通过各种工具与金融机构结成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
,并滋生利益转移和利益攫取等各种问题,一旦经营漏洞和经营损失不能被金融工具所覆盖和掩盖,就会发生债务问题,也会连累金融机构并迅速传染,酿成了金融风暴。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年,东亚病仍要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财团化的企业,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和投资链条也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都不清晰,透明度很差。现在的金融工具的种类和体量已经远远超过二十年前,财团的利益结构、业务体系和公司金融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二十年前,
譬如我们现在颇感头疼的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通道业务就有相当部分指向这些财团
,如果发生问题,破坏性和传染性也会更大。
因此,下一步应该对这些财团企业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透明度,强化披露。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
东亚病
”
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吴敬琏:十八界三中全会
336
项改革措施应一项项查有没有落实

第一,我们的会议主题非常重要,从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
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做学者、做研究工作和做教学工作的人,都应该在这个转变上做出贡献。我想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应该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比如说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大概有两点认识跟高速增长是不一样的。
一是高速增长依靠的是投入的增加,高质量的增长需要靠创新和效率的提高。
要提高效率来支持增长是苏联
60
年代后期最先提出来的。我们正式的提出是在
1995
年,
“
九五计划
”
明确说了,要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所谓集约增长,就是说依靠投入增加的增长转向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
“
十五
”
走了一点弯路,
“
十一五
”
又重新提出,要以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后来一直是维持。后来有一些提法,其实核心也是在提高效率上,比如说要跨越整个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要着眼于供给侧,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二是从集中注意经济增长,提出高质量发展跟增长的内容有一些社会方面的要求。
这个问题据我的记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强调了。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它集中突出的来作为一个主要要求提出,但是分别早就提出来了。现在又集中的提出,说明我们过去这二三十年做的不够好。我们必须要总结经验教训,到底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为什么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这样我们新措施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质的要求。我们如果重复一些过去无效的做法,那就延误时机了。因为现在提出的有些做法过去做过,好像效果并不好,我们需要总结教训。
第二,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政府方面该做些什现在还不太具体。
政府提出号召,你们要做什么,政府自己要做什么,应该做出比较实际和明确的规定。有两件事情:
一是建立一个好的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了
336
项改革,一项项的检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