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国际传播学会(ICA)附属期刊《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版了题为
“领域的躁动(ferment
of the field)”专刊
,
汇集来自传播学界各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所撰写的35篇文章,对传播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制历程、发展导向和学术焦点议题展开探讨。作为反思传播学科建设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专刊的思想史意义受到学科公认。
35年过去,日新月异的环境下,传播学科又将何去何从?鉴于此,新近出版的《传播学刊》发表”领域的躁动:传播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名专刊,开展新一轮传播学科建设反思、展望的探索。有感于“躁动”精神的学术关怀,复旦引擎团队将通过以专题推送的形式,分期摘编本次专刊的原创论文,以期促进同好者交流讨论。
引擎团队提供本次所摘编论文的原文PDF版本,读者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 (提取码:47df)。
编译丨陈鑫盛
△
Ferments in the Field: Introductory Reflections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ristian Fuchs教授 威斯敏斯特大学

邱林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作为本期专刊的主编,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Christian Fuchs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教授在专刊前言中肯定了1983年出版的“领域的躁动”专刊对“界定传播研究及学者的社会角色”的意义,并希冀通过本期专刊完成传播学科的新一次“自拍”,延续“躁动”精神,为传播学科反思发展、审视当下和构想未来发展方向提供资源。
作者们概述了本期专刊关注的五个反思面向:第一,全球化背景下传播研究视野日渐国际化,但研究基金及学术自主性的匮乏使得全球视角的传播研究依旧稀缺,这呼吁着未来的传播学者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及其不平等问题的普遍性,并着力探索民主社会的传播形式;第二,数字化全方面渗透并塑造现代社会,而数字媒体研究却固守既有学科结构、趋于碎片化,而计算科学的日渐普及,则促发传播学者对方法论至上、现实问题缺失这类学科现象的忧思;第三,传播学科关于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这一经典对立的探讨,在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批判研究的边沿化而被搁置,重新构建对话的桥梁,将有助于传播研究焕发批判锋芒;第四,新自由主义的受挫,促使阶级及宰制的视野被拉回传播研究,并形成新一轮批判/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转向;第五,传播学科的定位在全球化受挫、世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语境下被持续探讨,引导学者们从传播实践中寻求建立实践的传播学(praxis communication),并追求更具批判性、公共性的“有机知识分子”。
△ Media as data extraction: towards a new map of a transformed communications field

Josep
h Turow教授 宾夕法尼亚大学

Nick Couldry教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oseph Turow教授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Nick Couldry教授关注信息循环科技(即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与数据提取/分析科技的融合对社会秩序的剧烈影响:受众群体媒介使用的信息被商业化而产生巨额利润,成为价值提取的重要资源,广告及数据分析产业通过网络监控构建起庞大的数据市场,并且构建起诸如大数据分析等知识领域。用户数据被用作商业目的的后果,是用户被企业构建为不同目标群体,并歧视性地采取商业策略。
在作者们看来,这都是当前“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典型特征,在持续性、自动化的监控中,经济意义上的群体行为组织和统治通过数据收集、加工与分析等方式成为可能,而互联网在其中正是持续监测、抽取数据的重要空间,移动互联技术设备让监控的形式及对应的商业策略日渐多样化。因此,媒介概念不再可被局限于叙事内容,而应看到内容背后基础性的传播面向,借由数据管理,媒介成为社会控制的核心科技。对于传播研究来说,需要着重关注作为经济与社会生活基础性维度的监控,寻求新媒介系统所应立基其上的核心价值。
△ For a Practical Discipline

Robert T. Craig教授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Robert T. Craig教授长期致力传播研究领域的整合和学科化,在本期专刊中,他继续这一工作,主张“捍卫实践性学科(For a Practical Discipline)”:这一定位包含着三个组成要素:第一,研究对象是实践(praxis),也即在特定环境下的商谈性选择(deliberative choice),这一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同时兼具规范性与技术性的知识诉求;第二,研究的方法论是商谈性调查(deliberative inquriy),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统摄于理念化实践商谈的取向之下;第三,研究与社会的关联在于贡献元话语(metadiscourse),研究作为制度化实践设计并重构着社会流行的元话语。
那么,为什么传播研究需要走向实践性学科呢?作者认为,一方面由于缺乏智识特殊性和制度根基,传播学的合理性建构依赖于与社会文化的紧密关联,而这可以通过将实践性学科作为规范性理想而达到;另一方面也与传播学不同领域转向实践视角的当前现象相契合。对于“实践性学科”面临的挑战,作者也一一辩护:实践性学科的构想既不会对科学实在论的传播科学研究产生认识论障碍、也能包容将实践视作霸权共谋者的批判理论,更不会被实践理论所强调的实践优先性完全消解,相反,作为一种反事实的规范性理想,它为实践(praxis)的商谈性反思提供了理论资源整合的可能性。
△ Media Materialties: For A Moral Economy of Machi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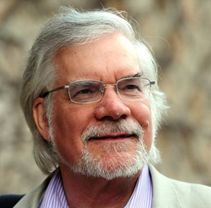
Graham Murdock教授 英国拉夫堡大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性学者、英国拉夫堡大学的Graham Murdock教授认为,在数字技术发达、媒介似乎高度“去物质化”的时代,传播研究的关注点分布于媒介产业的政治经济影响、媒体符号资源和媒介关系实践,媒介物质性(media materialities)、也即传播系统功能的物质资源构成部分,成为一个研究盲点。数字科技的崛起,有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形成的去管制化的产业环境。因此,根植于市场化进程的数字媒体产业本身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构成部分,举例而言,互联网为高消费的市场运作方式提供了便利的空间:依托用户数据,广告可以精准投放产生巨额利润;将商业内容与文化形式结合的原生广告盛行;网络的交互性有助于品牌推广的社交传播;“光滑”的支付系统令互联网消费行为极其便利。
然而,物质性为理解数字科技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数字产业与全球环境问题紧密相关,高消费及浪费的消费文化通过数字媒体流行,文化消费的理念加速了产品的淘汰率,数字科技基础设备的建设对稀有资源及能源的需求膨胀。而数字科技产业的发展,同样遵循既有市场的劳工组织规律,数字繁荣的表象事实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问题紧密相连。随着以云计算、互联化、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浪潮的到来,环境、劳工等体系基础性问题又将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呼吁着传播研究走出舒适区,在与不同领域的学术对话中确立起“机器的道义经济学”(Moral Economy of Machines):在机器走向自动化、智能化、互联化的同时,传播学更需要探索其中的责任所在之处。
△
Materializing Communication: Making the Case for a Relational Ont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