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最好的资讯评论,兼顾专业与趣味。 |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
你会不会觉得生活卡住了,为了不卡你做过什么抽象的事情?知乎答主、 导演覃牧秋 @毛毛毛 拍了一部电影——《东四十条》来回答这个问题,该影片将于 4 月 8 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再也不能这样活了!」是他拍摄的起点,而斩获平遥国际电影节两项大奖、甚至登上大银幕,是寻找答案过程中的一份「意外惊喜」。没有专业的摄影机,没有成熟的拍摄团队,他如何拍出这样一部打动人心、引发共鸣的电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你会不会觉得生活卡住了,为了不卡你做过什么抽象的事情?
| 答主: 毛毛毛
我自己花不到 3w 块,花一年时间拍了个抽象的电影。然后马上要上院线了。
「你是不是卡了?」
以前打游戏的时候遇到朋友不动了,我们就会这样问。
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我自己的生活居然会变得卡卡的。
什么是卡住的人呢?
作家郑执在他小说集的扉页上打了个比喻:
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进入了一种爬杆子的游戏,你要努力往上爬。但很多人会进入一种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的状态:没力气往上了,但是又不甘心滑下去。那他就卡住了。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困境。
具体来说就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症状:
感觉自己的工作很重复,生活不上不下;
外卖列表里无数种吃的,选了半小时选不出一样;
知道不能一直呆在家里,但出去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
很多电影都是看一半没耐心看不下去,游戏打了一会就关掉;
把别人的朋友圈点了一遍,自己的最后一条更新还是半年前;
……
而且我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这好像是一种群体性沉沦。部分朋友甚至开始抑郁。
这种卡卡的情况积攒到了前几年达到了一个顶峰,当然也有疫情的原因。
再也不能这样活了!必须刺激一下自己,找个事情做。
有一天我和邻居大豆在胡同里散步 (我们都是租住在北京胡同里的北漂) ,我们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告示,有个人在找他的鸟。我看到这个鸟在树上,我要怎么抓到它送回失主?又不是猫猫狗狗或者人。这个找鸟的事情就像无聊生活中的一个海市蜃楼,你知道它虚无缥缈,忽远忽近,但是它又给你那么一点点希望,最后不了了之。
这和我们的遭遇多么相似,就像会出现在一部存在主义且脱力的电影里的场景。
以此为灵感和契机,我们决定拍一个电影。
我们还约定,如果真能拍完,就在朋友酒吧放一下,大家乐呵乐呵,抵抗一下这种生活状态。
但是这事情对我来说实在太抽象了,因为我们都没有完整的拍摄长片经验,也没有完整的设备,没有多少钱和资源,完全属于裸体打怪。
我们研究了一些导演拍第一部电影时的经历,比如诺兰和吕克贝松,发现大家开始的时候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他们解决的办法也差不多, 总结起来,就是: 抠抠搜搜,坑蒙拐骗。
1. 确定信念
我们打开加入了 5 年的抠门男子和抠门女子小组,刷了几天,精神赋能一下。 (这很重要,类似附魔叠buff,加精神属性) 。我和大豆商量,拉了个预算,设定一个 5w 的标准,我俩平摊。当时行业停摆,大家收入变少很多 (我们都混迹在视频广告行业) ,于是我们就制定了一个「花最少的钱,玩最久的游戏」的原则:这个片子一定要拍一年四季的景色,让我们这一年都有个事情可做。
2. 剧本的形成
因为穷,剧本必须特别好拍,剧情简单,单一线索。场景调度角色行为也都要非常简单且日常。我们设想了一个线索:两个人花了一年四季找一只悬赏告示上的鸽子,但是他们却一直在说些有的没的,或者在胡同里散步。大豆写好框架,我们就一起聊天,往里面加对白和细节。就近取名,电影就叫 《东四十条》。 这两人就一个叫东四,一个叫十条。
3. 演员和开机
剧本写了一页多,秋天来了,为了落叶的场景,我们决定马上开始拍。大豆开始在朋友圈里筛选演员,她找到两个朋友,一个是张帅 (他也是后来first爆款 《貘之梦》的 导演) ,一个是钱赓 (他是一位行为书法家) 。我们骗他们,这是拍个短片,先试拍一下。吕克贝松在自传《但愿天真》里说,有一次他距开拍还有 15 分钟的时候,在路边便利店用「可以和阿兰德龙搭戏」骗到了一个路人来参演他的电影。相比之下,我们还算善良?
(初代东四和十条)
第一次拍摄后,我们发现张帅面对镜头过于认真,我们决定把他换成杨凯航 (他是独立乐队「踽踽」的贝斯手) 。张帅后来有点伤心。
(最后决定的两位主演:左钱赓 饰十条;右杨凯航 饰东四)
4. 器材和设备
找一个有机器的摄影师,一石二鸟。当时住在附近的摄影师小迪,拥有一台 Red Komodo ,由于这个是原始投资,他最后成为了我们电影的出品人。
(我们最贵的设备:Red Komodo)
5. 开机仪式
简单攒到几个临时组员以后,我们先拍了开机照,就在胡同里。至于为什么选这个角落,因为背后墙上贴有《长津湖》的海报,我们觉得无所不能的吴京老师能带来好运。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简单有效的开机仪式)
(与《长津湖》合影)
6. 时间规划
诺兰在拍摄他的第一部片子《跟随》的时候,由于剧组平时都有别的工作,他只能利用每周六进行拍摄,并且演员也是素人朋友。我们在凑齐人员上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虽然大部分人都没有固定工作,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同一天有空。最后我们发现,每次拍摄,几乎都在周五。为此,我们甚至想把出品单位命名为「 星期五营影业」 。
7. 捉襟见肘 vs 极限操作
除了摄影机,我们几乎没有太多其他设备,很多场戏都只能用我闲鱼 75 块买的三脚架 (基本无法摇) 。录音师自带录音设备。镜头大部分时间是摄影师自己的老蛙 12 和设备商提供的佳能大三元。有时候反光板都是路边捡来的泡沫箱拆成的,组员们也是人尽其用。
8. 美术道具
好在剧情是现实和生活流,美术和道具我们一般都能自己动手制作,或者想些奇怪的招数来解决。比如蒸一个连体的馒头,调制鸟屎,把玩具冻进结冰的河里。
感谢当代科技。 因为简陋的设备和人员很少,我们只能用新事物解决老问题。如果在十几年前,这些问题还真的很难解决,只能说感谢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从这一点上说,本片还是非常当代的,哈哈哈哈。
没租监视器,我们用 ipad 连接摄影机来监看。
用 Red 自带的 app ,还可以用手机跟焦,虽然没有那么精准,但勉强够用。 (还好我不是手残党)
由于胡同的特殊性,转场的时候经常是骑共享单车。设备和道具的转移,也经常使用同城闪送。
9. 自然主义
由于没有预算,我们全片使用自然光。白天就靠天吃饭。每次开拍前,监制就会帮我们在各庙烧香。到了晚上,依然是没有打灯,全是胡同里的路灯,但是坚持在同一场景下,画面中路灯的色温统一的原则
租场地?不可能。全都是蹭胡同里的实景。由于居住在此,我们寻找了很多胡同里有趣的实景。比如这场戏,背景就是一个斑驳的雕花木门和门头,并且附近的居民还会把自己的宠物鸟挂在门头上晒太阳。
10. 小区级前期+宇宙级后期
我们的片子分成 7 个章节。制作的节奏是写一段拍一段然后剪一段,休息一两个月,等待季节变化。经过一年多的拍摄,片子杀青。剪辑和一些简单的视效我们自己搞定。但这时候,调色和声音的制作成了大问题。我们把剪好的片子拿给一些朋友看,其中两个朋友给了我们几万块钱,支持我们去做后期和配乐。
但这些钱,对一部 90 分钟电影的所有后期来说,还是很少。我们就忽悠朋友公司说这个片能拿奖,能为你们公司品牌赋能,以此让朋友用很低的价格 (意思意思那种) 帮我们调色 + 做影院的声音,然后做各种影院技术上的匹配。
但是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朋友的后期制作公司和团队,硬件和软件上都是业内顶尖的。
(我们第一次在影院里监督调色和调音)
(自己在家制作下雪)
最后,反正一路坑蒙拐骗 (非常厚脸皮地) ,也得到了行业内外很多前中后辈的帮助 (感恩) ,这片总算是整完了。
成片也很抽象,因为两个角色一直在说冷笑话,要不就在散步,遇到各种无聊的人。
我们如约拿到朋友酒吧放了一下,大家有人一直笑,有人看哭了,有人睡着了。
审核的老师和专家觉得我们人畜无害,所以很顺利的拿到了龙标。 (存在问题和修改意见是:无)
片子还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次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也展映了。我们几个一脸懵逼去电影节走了个红毯,体验了一次星光大道。
最后一算账,我自己花了 2w8 人民币,稍微超支了一点。我觉得这个支线的游戏体验还是不错的。
弄到这一步,片子本身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主要是在卡卡的状态下做的这个决定,让我们体验了一个完整的电影流程,这个钱花的还是比较值。
现在回想起来,开拍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这个片子能拍完。剧组最多的时候也就 10 个人,每个人都要干几份工。 虽然是草台班子,但是大家都很认真。 想想小时候放假,一旦有朋友打电话叫我出去玩,我都直接出门。先出来,再想玩什么。这种状态真的无敌。 我们拍这片的时候,大家就好像都回滚到了小时候这种状态。
(拍片也是朋友的聚会)
而且这片子 4 月 8 日要全国上映了,这个游戏还没结束,还能玩一个月。
马上开始和朋友一起,干一些毫无目标的事情,虽然不知道它最后能发育成什么样子,
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和生活的抗争呢?希望大家也能行动起来。
这部电影的另一位新人导演詹涵淇 @大豆 说: 「 10 年前我在县城体制内工作,以为人生从此看到头;10 年后我拍了自己的电影,居然还要上院线了。」
她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回答,发布在「普通人人生的容错率真的很高吗?」问题之下,希望为「被困住」的朋友带来一点力量。
点击 【阅读原文】 看更多精彩回答吧!
题图来源:《东四十条》
生活中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可爱的事情?
如果彩票中了五千万该怎么办?
👇 点击【阅读原文】,看更多精彩回答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

|
人力资源管理 · 我一直以为自己擅长做HR…… 7 年前 |

|
大数据风控联盟 · 自己身故,家人不知道有保险可以理赔怎么办? 7 年前 |

|
质化研究 · 2017学者“争议榜” 7 年前 |

|
丁香妈妈 · 冬天宝宝一周洗几次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7 年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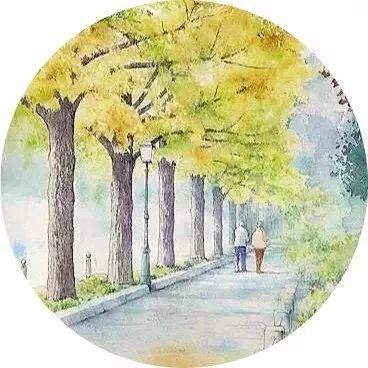
|
诗词天地 · 老去的是年龄,不老的是气质 7 年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