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
腾讯科技
”,选择“置顶公众号”
关键时刻,第一时间送达!


文 / 彦东
微信公众号 / 刺猬公社
——前《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如今转身成为投资人,他住过防空洞、寺庙的地下室,他说“我从来没有过新闻理想,记者对我来说就是份工作”。
——刘本渝(化名)在北京做了5年调查记者,一度罹患抑郁症,而立之年离开北京去了杭州,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在杭州买套房子。
——知名专栏作家潘采夫在北京的头两年,换了7、8份工作,现在转行在小猪短租做了副总裁。
……
2001年7月13日,辞掉了湖南省水电力厅工作的罗昌平回到家里,打开电视看到了北京申奥成功的新闻,“就觉得我赶上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啊,心里挺美的”。
罗昌平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单方面通知父母:他辞掉了父亲找关系给他安排的工作的消息以及他要去北京闯荡的决定。就这样,翌日凌晨,这位日后因实名举报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而名声大噪的调查记者,拿着站票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车。
此时,千里之外的河南郑州,同样是辞掉了《河南日报》广告部工作的潘采夫正赋闲在家,为生活费他变卖了父母给他买的电脑,过着白天看书、晚上和朋友喝酒撸串的生活。
浪荡一段时间后,潘采夫告诉身在北京打拼的女朋友,他还是想做新闻、做记者,“我要去北京了”。
两人当时选择北漂做新闻的理由出奇的一致——
“年轻人,还是该闯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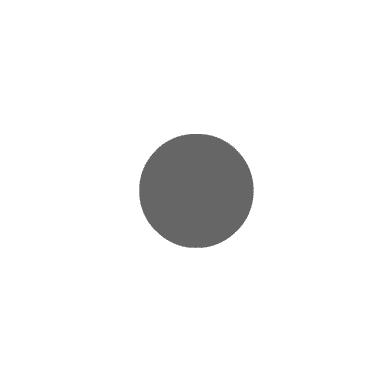
一
来到北京后,罗昌平租的第一个房子是故宫后面的一处地下防空洞,选择那里“因为便宜”——他的存款此时只剩下1000块人民币。
在防空洞“蜗居”期间,罗昌平投了无数份简历,并先后在《今日中国》、中国教育电视台做了个把月,但“《今日中国》变卦让我去做经营、中国教育电视台是母婴节目,我试了一下都觉得不对”。
最后他只拿到了中国教育电视台900块的劳务费,去了海淀清河的一间平房——8平米大、仅有一张木板床和木椅子,租金只要150一个月。

罗昌平
那里后来出了名,被外界称为“北京蚁族村”,北京统计网的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人均消费达到35000元。而蚁族村的人均消费尚不足12000元。
但罗昌平是“幸运”的,中专毕业的他“不知为何”被《中国商报》录取。2001年的《中国商报》还在北京南二环的报国寺内办公,包食宿。
虽然罗昌平只分到了一间地下室,但这却让他摆脱了之前每天上下班坐2个半小时公交的“巨大焦虑感”。在《中国商报》工作的3年时间里,罗昌平的收入也得到了爆发性的增长,“那个年代的纸媒记者不仅有职业光荣感,收入也还不错,一开始我月薪就有8000左右,2003年就已经过万了。”
2003年非典肆虐,罗昌平却做了一个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但事后却显得无比英明的决定——买房。那时北京二手房均价仅有4500元/平,罗昌平看中了广渠门的一套房子——50平米,地段南二环,到报社车程十几分钟,价格为6600元/平。
2017年广渠门房屋均价已经逼近67000元,翻了十倍。
罗昌平买房的一年后,也就是2004年,北京市出台了“招拍挂”政策(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在此之前住房用地以划拨为主。现在看来,2004到2005年是新世纪以来北京房价的第一轮较为明显的上涨,2005年春节北京房价已逼近万元。
这让此时到北京两年多、但已经换了七八份工作,刚在财讯传媒(《财经》杂志母公司)经营部稳定下来的潘采夫压力山大,看着手中4500元的月薪,他只能将目标瞄向价格洼地通州。
潘采夫买的是现房,价格稍贵也只有3000多元/平,可加上1250元的月供、出生没多久的女儿的奶粉钱、辞掉工作读研的夫人的开销等,每个月的花销高达7000元。
无奈之下,以文化人自居的他只能“厚着脸皮”瞒下领导,找到某媒体做兼职编辑,同时兼职写专栏,“差不多勉强覆盖掉生活成本”。
焦头烂额的日子很快迎来了转机,2003年11月,《新京报》正式创刊。年后潘采夫就投了简历,应聘文化副刊部的编辑,“我就觉得这份报纸前途无量,我也很喜欢这份报纸的文章。”潘采夫拔高了声调笑着说。
这一呆就是9年,他很喜欢这份工作,7500元的月薪也不算低。后来收入的逐步增长,让他在2008年时有了余钱。为了女儿上学方便,他在长椿街专门租了一套3500元/月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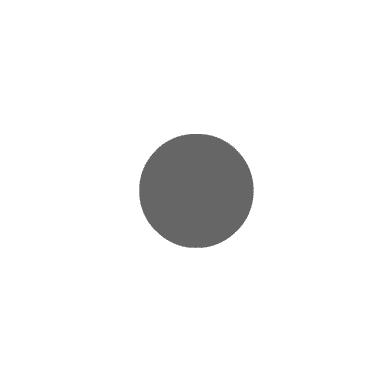
二
张本渝走出北京站就懵了——第一次来北京,他站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感觉有点晕,虽然已经和一个师兄约好在他家里借宿一段时间,但天性怕麻烦的他还是叫了一个在北京读研的朋友过来接他,而后蹭了一周的宿舍住。
在安徽某都市报工作的2年间,张本渝在合肥买了房,每个月2200元的月供压力,让他只能找租金便宜的地方住,不过他运气不错,找到一对年轻夫妇合住,20平米的屋子每月只要1300元的租金,在他的央求下还能够按月付。他回忆起来这件事不无得意,像是捡了大便宜。
“其实《新京报》的待遇在行业里是领先的,我属于比较能跑的记者,一般一个月能拿到1万多,但在那时候,发稿少的记者就会比较少。”张本渝说。
可张本渝没干太久,就跳槽去了《财经》,原因是遭遇了“职业瓶颈期”,由于在北京没有人脉,他很难拿到独家,写稿子也感觉“没有深度,感觉思维僵住了”。
《财经》的待遇更好一些,调查官员贪腐、公司问题,也让他更有成就感。但没想到的是,这段职业经历却让他一度罹患抑郁症。
“说白了就是看了太多社会阴暗面,想不通大家为什么都不按规则办事啊,明明就有规则的呀。”他不想解释太多。

2015年8月13日晚,前《南方周末》调查记者朝格图因抑郁症复发离世
本能告诉张本渝这样下去“很危险”,他天天晚上12点后跑出去找朋友喝咖啡、喝酒聊天,“我得把负能量全部倾诉出去,转移给别人我就解放了。”他哈哈大笑道。
可大家为什么不按规则办事的疑惑,他至今也没有想通。
到2017年,张本渝正好满30岁,比起这些困惑,他不得不考虑些更为现实的问题——他没有北京户口、买不起房。
2017年,北京房屋均价达到52000元,这还包括房山、密云等偏远城区。罗昌平买房时的均价4500元,如今也只能在广渠门租一套20平米不到房子一个月;即使是租房的均价,也从2003年的1400元上涨到了2016年底的4560元。
“我想稳定下来了。”张本渝叹着气说。
今年年初,张本渝在朋友的介绍下跳槽到杭州某基金会,从此和身在北京的女朋友开始了“京杭双城记”。
幸好他负责的是公关、传播方面的工作,经常要到北京出差,周末也经常回到北京。
“
都是成年人了,我们不再是刚毕业时的小年轻,懂得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张本渝说。
基金会的工作强度比传统媒体要高不少,不过待遇也相应的提高了。杭州的生活成本比北京小了不少。张本渝感慨,自己在余杭区租了一套精装修的2居室也只要3800元/月,这个价码在北京二环只能租到一间次卧。
如果把合肥的房产卖掉,在杭州买房的压力不算大,“你知道吗,我们这80%都是从北京过来的”。
他这次打算在基金会长呆下去,“很简单,你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了,做公益让你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很多人在做事”。
他不再沉浸在那些离他生活很遥远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能自拔,他现在更关心的是,杭州的阴雨天气太多让他“很不爽”;“工作日太忙了老盼着能不能快点到周末”;“太倒霉了,去年杭州颁布了要缴纳两年公积金才能买房的规定,我晚了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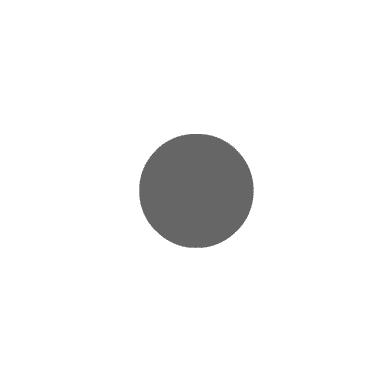
三
罗昌平虽然早就在北京买了房,但却一直没有北京户口。年轻时,他对北京户口嗤之以鼻,“觉得会限制自己的流动性”。
但今年,夫人怀孕后他的态度有了松动,“我有点后悔,如果有儿女,还是在北京有户口好些”。
2015年,罗昌平正式离开新闻业并创办了优恪网、成为投资人,投资了法网、丁丁律师等,这种转变源于他之前的新闻从业经验。
罗昌平对新的信息传播、影响社会结构的方式很感兴趣,2012年他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传统的信息发布方式过时了,当时人们普遍没意识到这一点,文章的发布要等杂志印刷出来才行?我现在发条微博就可以。”
为了证明自己的预判,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了刘铁男,做这件事的初衷并非源自“新闻理想”,“这件事的最大意义是告诉我的同行和政府官员,新的信息传播格局变化了,过去的方法论都失灵了”。
“
我从来没有什么新闻理想,记者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十年前的薪水也还不错,我不用迎合别人,能光明正大的赚钱,偶尔还能帮到一些人,这就是份不错的工作。
”罗昌平说。
他的《嘉禾拆迁事件》报道被当时的东家《新京报》写进内刊,夸他有“新闻理想”,他看到后就和别人解释说,“我没有新闻理想”。
他看到很多现在在北京北漂的年轻新闻人,最大的感触是十年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变化。
潘采夫对此也有同感,“现在对记者而言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为了收入入行,你一定会失望的。”

潘采夫
他认为新闻业的两大支柱是经济地位和调查性报道,缺一不可,如今因为传播格局的变化,两大支柱都岌岌可危,“这个行业自然就不太行了”。
潘采夫后来到《南都周刊》做主笔,采访小猪短租后觉得“现在做新闻不行了,那就做企业呗,共享经济也有改变社会的力量”,他转身加入了小猪短租。
转行后,潘采夫的收入一下翻了好几倍,这时女儿升了中学,他租了一栋8000元/月的房子。当时有不少媒体记者采访他,有人对他说“现在都说我们这行不行了,您又搞了这么一出,我们更焦虑了”。
有人采访他时向他咨询转行的建议,有人采访完直接投来了简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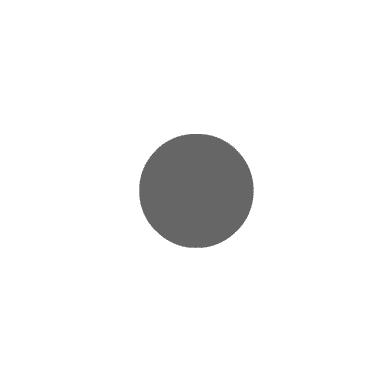
四
“人越长大,就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没有梦想,不如趁年轻满足自己的精神和价值观追求”,潘采夫说,
如果今天他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年轻人,他依然会选择做新闻。
“如果20多岁就为了户口、购房指标选择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人生很可能过得很灰败。”
北漂16年、做新闻15年的职业生涯里,潘采夫看到过年轻人各种各样的迷茫,也接受过不少人的“人生咨询”问题。
曾有喜欢新闻的年轻人为了户口到了某事业单位工作,他慢慢发现,这些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渐渐失去了锐气。
“他们年复一年的重复自己,做了小半辈子后丧失了跳出来的能力、丧失了在社会上谋生的能力,随着北京消费水平提高,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多人围城外面的人想象的那么好。”潘采夫感慨道。
买房、北京户口是困扰很多北漂最大的“心魔”,罗昌平现在的员工也有不少北漂一族,他很理解这种感受。
但他通常会分享自己的经历,2006年罗昌平离开《新京报》时有两个选择:《财经》杂志或腾讯网,职位分别是记者和新闻中心主编,他选择《财经》杂志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买的房子在南二环,而腾讯办公地点靠近北四环。
“我当时甚至都没想到可以在北四环那边租一个房子,就觉得我在这边住就应该去近的地方上班”,罗昌平说,
房子、户口都是重要的资产,它可能在人的潜意识里限制住人的思维模式,“但其实你都不知道”。
“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去腾讯,那人生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局面。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如果你现在真的买不起房,就放弃吧,给自己解绑,至少能让自己自由地选择。”罗昌平说。
潘采夫则觉得“你说你能失去什么呢?北漂本来就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年轻时要是有志于在新闻业干点什么就去做,不行就多换几份工作,反正肯定没我换得多,人还是得找准人生的坐标”。
潘采夫比较“现实”的建议是——“如果只考虑现实问题很容易出问题。”
他妻子最初在北京一家意大利公司工作,21世纪的头十年是外企在华最吃得开的时候,那时知名外企如宝洁,录取员工的比例都是数千人挑一。
所有人都觉得她这份工作很体面,这家公司的办公楼的对面是阿里巴巴,当时阿里巴巴的高层过去串门聊天,看中了他妻子的才干,想拉她入伙。
“她回家和我说,这什么公司名字太土了肯定活不长,就没去”,潘采夫笑着说,“就没想到以后是这样。”
“谁预料得到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不能,那不如就闯荡闯荡好了!”潘采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