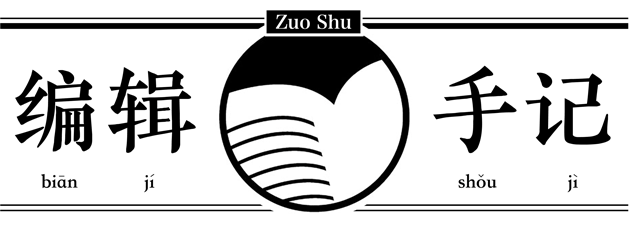
第一次在版代的信息中看到这本书,我就非常感兴趣。而在看到书的内容之后,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拿到这个选题。老实说,并不是所有选题都能让编辑有着卓绝的信念,必须把它拿下,做出来,做好它。很多时候,当编辑也有取舍,这本书也许利益相关,那本书可做可不做,但《风的女儿:二战德国女飞行员的交错人生》不是一本这样的书,对我而言,她是一本命中注定要相遇,并与我灵魂激荡的书,虽然这样讲感觉实在浮夸,但她配得上这样的形容(此后提到本书都会用“她”)。
做这样的历史选题一直是我的个人喜好,或者说是最热爱的选题取向。当编辑以来,我几乎无数次被问到,为什么你一个女编辑会喜欢历史题材,喜欢战争题材,喜欢这样看上去硬核的男性题材。我的回答总是,我一直都喜欢历史,喜欢言之有物的东西,虽然虚构的作品能带给人不同寻常的体验,但只有真实的事物才能永远带给我最震撼的感受。而且阅读爱好与男女无关,男性有权利喜爱自然、美术这些天真柔美的领域,女性也有权利喜爱历史、军事这些铁血激荡的风云。
定名与相知:我们并未知道那天所见花的名字,但我们能闻到香气
《风的女儿》的原名其实是“那些为希特勒而飞行的女人:女武神的真实故事”,在读版权代理提供的试读部分时,我一开始被她吸引的点其实也是因为她讲述战争的独特视角。纳粹德国掀起二战的腥风血雨,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欧洲人在战争中的立场始终被反复思索。平民受难,领袖抉择,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希特勒身上,在各国与之对抗的领袖身上。
但是,从士兵的角度出的书却很少,特别又是女性士兵,还是在男性占
据主导地位的航空飞行领域。
这个切入点非常新奇,又非常吸引我,想去看看到底她们有多了不起,能脱离时代的桎梏,走到台前。
这本书的两个主角,都身为纳粹麾下的女性飞行员,需要面对人性的抉择与军人爱国情怀之间的矛盾。
可以说既是军事类历史题材,又可以说是女性纪实题材。
我之前看过很多类似《天生幸存者》《纳粹子女回忆录》这种书,犹太人的母亲,纳粹德国人的女儿,她们在大时代的辗轧之下,绕指柔皆成百炼钢,所以我以为,《风的女儿》应该整体上也是这种风格,能够打动对历史的多角度展示感兴趣的读者。
不过,这本书在选题申报时遇到了一点儿困难。鉴于原名,选题申报的时候就用的是《希特勒的女武神》,简洁清楚,一目了然。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希特勒这个字眼一出来,女武神就没法跟随了,好像希特勒的后缀能配得上女神是一种不正确。其实女武神在这里出现,是一语双关。首先,女武神(Valkyrie)在北欧神话中,是天上的女战神,骑着能飞的仙马,在战场上收集死者的灵魂上天。
《风的女儿》书中,两位女主人公不是载过希特勒上天,就是给当时的德军设计过军机。两人本身虽然并未入空军,却也都是“身经百战”,大小表演,各种测验,都有她们一飞冲天的身影。若将她们比喻为翱翔在天的女武神,可以说是极为契合的。其次,《风的女儿》主人公之一,正是一个著名的刺杀希特勒计划——“女武神计划”的间接参与者。这里的女武神,是真正要杀死希特勒的刺客,而绝非这个残暴之人的拥趸。
这个书名拖沓了七个月有余,从等待她过审,到毫无音讯,再到得到一点模糊的信息,大概可以确定,不改名她就出不来的时候,我就拼命开始想,到底要改成什么名字,才能既体现她们的美丽和勇敢,又能表达她们对天空的向往。和朋友们聊了很多名字,有时候“飞起来了”,有时候又“差点儿意思”。最后,是在家里读安徒生童话,读到海的女儿,最终飞上了天空,在船帆和海洋之上,在太阳和云朵之间,天空的女儿正在等她,她们没有翅膀,却能飘在风中,因善良而获得永恒不灭的灵魂。
生活给启发,那就抓住它。于是我决定将这本书定名为《风的女儿》。两个勇敢美丽的女飞行员,在书中,依恋着风,飞向太阳。但天真的很高,她们有人飞升,有人陨落。
在20世纪初,德国迎来了它的“航空时代”,《风的女儿》中的梅利塔与汉娜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身世复杂的梅利塔·席勒胆大心细、低调谨慎,爱上了德国顶尖贵族家庭的亚历山大·冯·施陶芬贝格,潜心研究空气动力学,期许以知识报国;美艳热辣的汉娜·莱契则极其爱慕虚荣,反感父母对她成为贤良淑德家庭主妇的期许,纳粹的崛起,给了她可以承载个人梦想与魅力的表演舞台。两个人卓越的飞行水平,使她们大放异彩,不相伯仲,都获得了“女上尉”和铁十字勋章的殊荣。
但我在和朋友交谈时,很多人都听说过汉娜·莱契的亦正亦邪,却几乎无人知晓梅利塔·施陶芬贝格,后者仿佛隐入了历史的烟云之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她的家人才开始搜集她的故事。汉娜对此表示:“梅利塔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成就。”而梅利塔的妹妹则说,让我们“发现真相”。
我难以忘记汉娜金发碧眼的明艳,梅利塔鹰鼻星目的深沉。她们一个热闹就热闹到底,一个沉默就沉默至极。但喧嚣的不一定是真相,沉默的不一定被遗忘。
《风的女儿》全文来龙去脉很长,中间涉及一战后欧洲局势的错综复杂,纳粹的汹涌和崛起,刺杀希特勒的惊心动魄,臭名昭著的柏林奥运会,凄惨无比的犹太集中营,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希特勒地堡与狼穴……但是每读一遍,我、译者,甚至审读老师,还是会对梅利塔和汉娜本身产生深深的感慨。这两个女人,不是盛开在地上的温室花朵,而是在残酷到极致的战争环境中,驰骋于天河之中的女神。然而我们却见证了她们荣耀背后的强悍与悲伤。
作为编辑,我认为,这本书可以打动人的不止是女性可以冲破世俗,走上强势巅峰这一件事,还有一些关于人性的东西,在厚厚的云层背后,真相的声音如飞机冲破云霄,在风中呼啸作响。
在制作封面的过程中,封面设计师多次说我,太偏心,对梅利塔的偏心太明显。
一开始设计师有两版设计稿,但我都不太满意。第一版是Tiffany蓝,绿汪汪一波水潭似的,橘红色大飞机耀眼夺目,但是梅利塔的脸是个淡淡的印子。问了很多人都喜欢,但是感觉飞机是主角,倒把飞行员给忽略了。不成,这不成。
然后就是现在这个版本的雏形,深橙色,日光灼热和暴土狼烟的战争感觉都出来了,但我感觉不够冷静,有点过于风尘仆仆了。
在水绿色、深橙色、天蓝色版本做了几轮投票,又经过各种“辩论”之后,我一反平时的犹犹豫豫,果断选择了天蓝配银卡。事实证明,效果还是可以的。
有个朋友在第一次见到真书后惊呼:“这不就是机身映着蓝天的颜色吗!”
内封倒是毫无悬念,一稿过。设计师和我也有了点儿心有灵犀,稿出来就没二话的那种:云上的日子,霞光漫天。
在我纠结图案和底色的同时,设计师也在抠人像的问题,原书的封面没什么悬念,淡米色底,红色字,双人像,一看就知道是飞行员。但是我们考虑到还是要给当时德国飞行热这个时代大背景给一个呼应,所以封面上的飞机是不撤下去了,那么就只能上一个人了。
设计师说:你偏心,你就想放梅利塔。
我:你不偏心,你把汉娜给放上去看看。
设计师:放不下。
设计是相通的,封面跟房子似的,面积就这么大点地儿,放了你就没她。
然后她就把汉娜放封底了(我觉得她也偏心)。
放完了之后我觉得,怎么这个汉娜头这么大呢?是不是调小一点?这个图怎么那么奇怪呢?她在背后偷窥梅利塔呢?
设计师:你想一下,是不是有你就是看她不顺眼的问题?
我:……
最终调整的结果我和设计师都挺满意的,也算是尽了“洪荒之力”了。
尽管有人提出,你这不是双人传记吗?怎么就一个人在前脸儿?
我一般就很平淡地说,那不是背后还有一个吗。别的我也不讲了,在此统一答复一次:你要说我偏心就是你对。
是的,我得承认,我始终偏爱沉默坚韧的梅利塔。她不是坚忍,她没有在忍耐。她是强韧而不能被扯断的藤蔓,像童话中杰克的豆蔓一样,顶天立地,把所有她爱的人卷住,哪怕风雨来袭,她也能牢牢地抓住他们,让他们在凄风苦雨中活下去。
在出版《风的女儿》的过程中,与我协同作战的几位也都是女士。大家八卦的性子上来,有时候也会背地吐槽。译者好几次和我说,那个文艺青年亚历山大真配不上梅利塔。看他那摇摆的样儿我就来气。要我说呢,也还是觉得克劳斯好,长得帅,又硬气,那才是个真格的老爷们儿呢。审读老师评价:幼稚,外貌协会。不过我知道她们也偏心梅利塔。
谁能不偏心梅利塔呢?但施陶芬贝格家人确实都是好样的。拎着炸药包走向地堡的克劳斯就不必谈了,亚历山大就是个历史老师,为了他的“一开始就不支持”纳粹,他一个文弱书生先被发到兵营,后被关进集中营,再后来选择的也是同样一个有着强大心性的女人——她胆敢在纳粹的死亡威胁下,仍然保有昔日爱人抗争的证明而不畏惧。克劳斯的太太尼娜在集中营里接到家人死讯时还是个孕妇,仍然能把孩子健康生下来,并且祈盼来日方长。
在最后临出版前与发行讲书的会上,一位副总编问我,你觉得这本书可贵在哪儿?
我说,之前我觉得,女性崛起万般难得,但这本书还有一个更可贵的基调:就是人,要坚持做对的事情。












